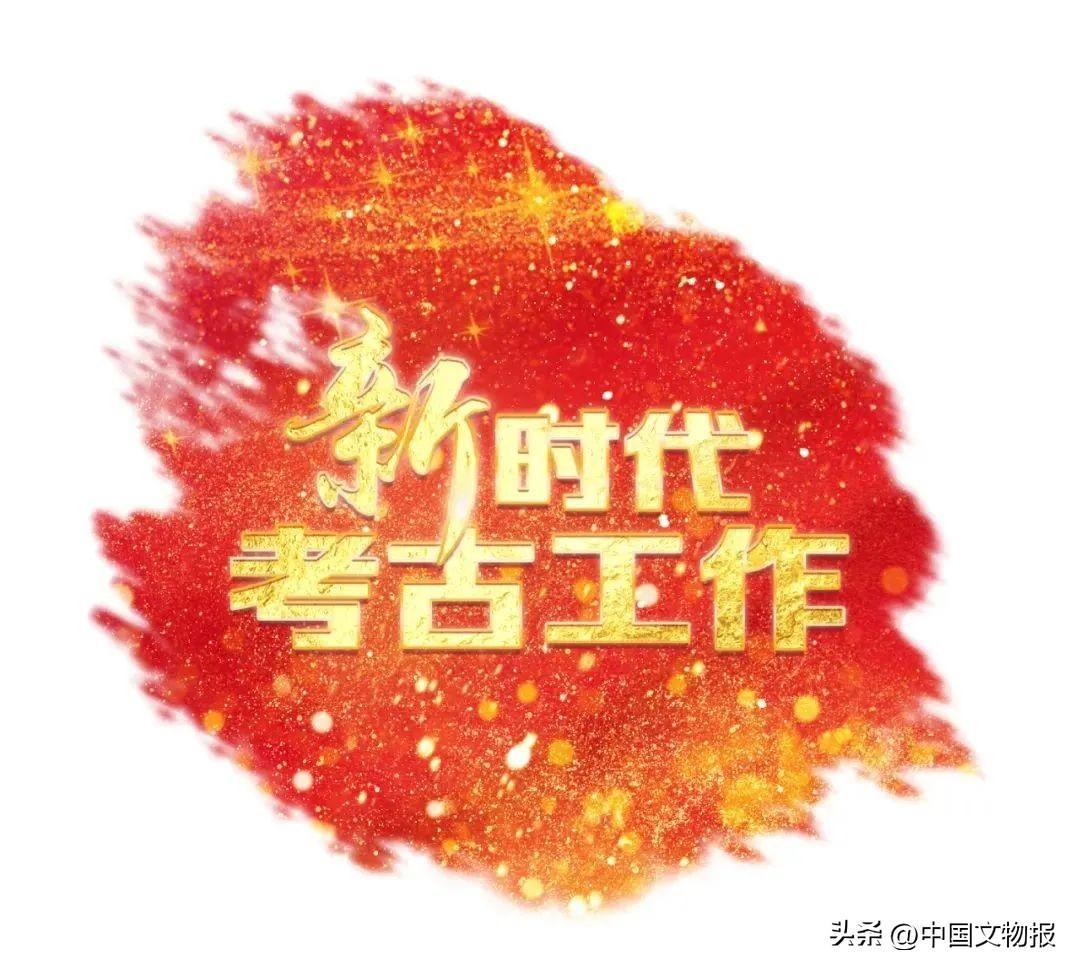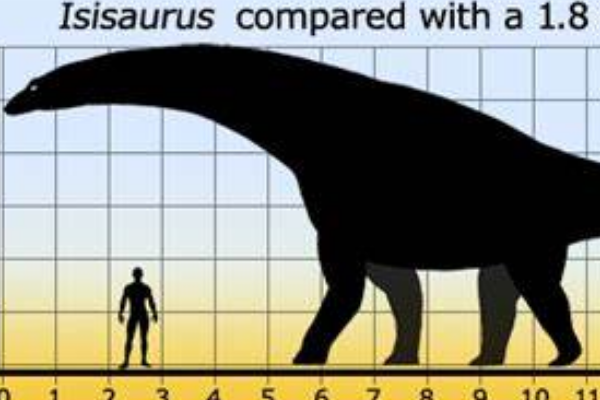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自序)
我对《老子》的兴趣,萌发比较早,持续比较长。回想一下,第一次接触《老子》,在什么时候?我记得,是在高中一年级。
初中三年,后两年,特别是最后一年,我的兴趣是背古诗,梦想学会写古诗,还有一手好文章。十五六岁,我犯了错误,在闭门思过,不是躲在家里,而是躲在心里,我和我——从前的我,简直判若两人。
上了高中,和我一起作诗的朋友不再和我来往。他读过斯诺写的毛主席的生平,雄心壮志不能已,他说,他要争取入团,不愿与我为伍,继续消极无为,堕落下去。
有一天,我的另一个朋友,非常淘气,其淘不让于我的张木生(现在是领导干部),多日不见,在路上撞见。我问他在干什么?他手执一卷书,居然说,他在读哲学,把我吓了一跳。
他挑衅地问,你懂哲学吗?诡秘的笑,挂在嘴角。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响了很久。
我不服。
从此,我开始偷偷寻找一切带“哲学”二字的书,希望拿出点证明给他看。哲学,当然特外国,但中国的东西也不能少。当时我更好古。
我在暗地里使劲儿,包括读《老子》。我是把它当哲学书。
那阵儿,我记得,围绕《老子》,关锋和任继愈在吵架,关同志的气好像更粗。
插队期间,有段时间,我也迷哲学,甚至发过愿,要学德语。
有年冬天,我的朋友肖漫子带我去看杨一之,我向杨先生请教,居然提出要求,我想跟他学德语。他答应了,定下日期。
可是,糟糕的是,我跟别人打篮球,打得昏头昏脑,居然把日子给忘了。想起来,实在不好意思。那时谁家都没电话。我连个道歉都没说,也不敢登门去说。
那阵儿,有个年轻人,陈嘉映,倒是在攻哲学,而且好像学了德语,很多年后,风入松开张,我们又见面。当年,我去过他家,希望与他亲近。
我记得,他们兄弟几个,敢在楼顶四边的短墙上走路。
后来,他成了哲学家,我和哲学无缘。
不过,《老子》还是留在了我的心中。插队的时候,我读过一点研究《老子》的书,印象最深有四本,其中三本还在我的书架上,一本是高亨的《老子正诂》,一本是马叙伦的《老子校诂》,一本是任继愈的《老子今译》,还有一本是王重民的《老子考》。最后一本,我是跟别人借的。
比如,“‘牝’是一切动物的母性生殖器官。‘玄牝’是象征着深远的、看不见的生产万物的生殖器官”,就是任先生所明示,我牢牢记在心里。此书有修订版,最新一版叫《老子绎读》,上面还有这段话。
朱熹的暗示,牝是有个窟窿就可以插棍的东西,比如门闩和门闩孔,钥匙和锁子眼,就是这种关系,我也是听任先生讲。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对我很重要。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比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小,比其他书大。
我没见过高亨,见过池曦朝。他们讨论《道经》、《德经》孰先孰后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还有,翟青的文章,《老子是一部兵书》,据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跟着这一发现才登出来。《老子》是不是兵书,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时的人并不傻,傻的是政治气氛,跟政治跑的气氛。
当时的学术骨干,现在也是学术骨干,而且是元老。
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高明老师是我的好老师。他的《帛书老子校注》,是替我们读书。读他的书,可以省去很多翻检之劳,留下工夫去思考。
1998年,郭店楚简《老子》发表,我参加过最初的讨论,包括达特茅斯会议、达园宾馆会议。我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就是参加讨论的结果,其中也包括《老子》。
我是学古文字的。文字考订,对我来说,是最基础的东西,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更关心的是思想内容。
我不同意,郭店楚简的儒书证明了宋明道统,它们都是子思学派的著作。
我也不同意,郭店楚简《老子》证明了儒、道原来是一家。
《老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书。我喜欢它睿智深刻,篇幅很短,意境很深,特别是其消极无为、飘然出世,被庄子发挥的一面。
老子和孔子不同,精神气质,更像《微子》篇中的隐士和逸民。隐士和逸民,有三大类型,死磕、逃跑和装疯卖傻。第一类最高洁,最难学,所以没人学。要学全是后两类。读《世说新语》,读《儒林外史》,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这种人文幻想。老子特能放下。放下的精神不属于儒家。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子》正好相反,它强调的是作“天下谷”、“天下溪”、“天下之牝”,甘居下流,不争上游(第28和第61章)。司马谈说,道家的特点是“去健羡,绌聪明”(《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六家要指》),什么贵柔贵弱好像水呀,什么要当女人、小孩呀,全是本着这种精神。
在这方面,它是天下第一。
《老子》给人神秘感。很多人迷的就是这种神秘感(包括西方读者),但我们不必把它神秘化。
《老子》的另一面是帝王术。它也提倡复古,它也崇拜圣人,它也主张愚民,念念不忘天下。愚民的伎俩更狡猾,也更高明。它的“道”,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韩非迷的是这只手。
大家别忘了。
2007年12月8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