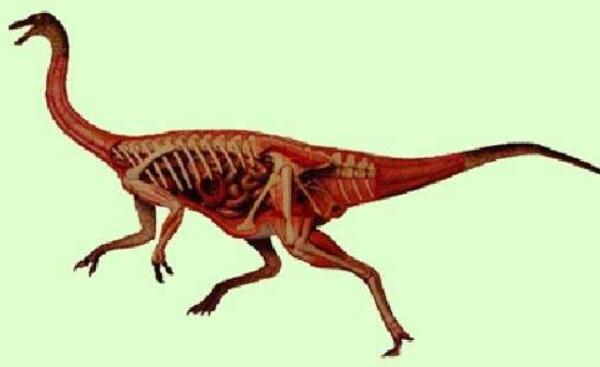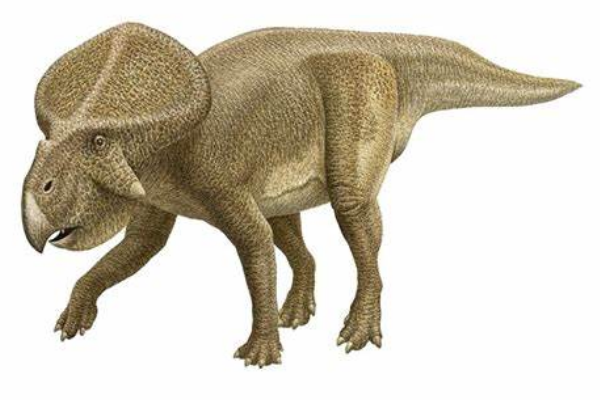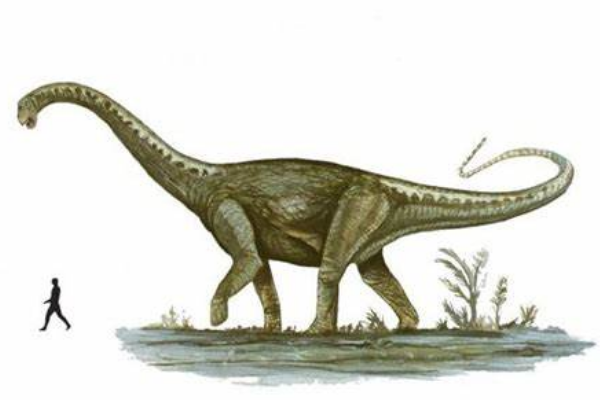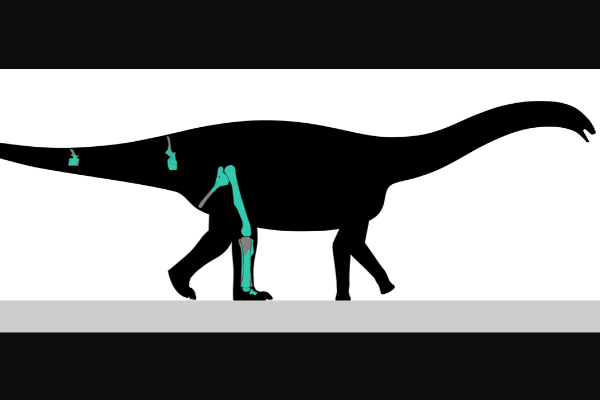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

【摘要】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有70年了。70年间尤其是近20年来,由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推动,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族属、地域和迁徙,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文明起源与形成,文化交流与传播,巴蜀文字和符号,宗教,艺术,科技等等。同时,在若干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内涵、主要成果与分歧予以了分析论述,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巴蜀文化;学术史;展望
从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从1933年四川广汉月亮湾的首次考古发掘算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达整整70年。70年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一切,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李学勤教授最近所总结的那样:“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仅从学术背景、文化内涵、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主要学术成果与分歧等方面对70年来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作一综合分析论述,并对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供各界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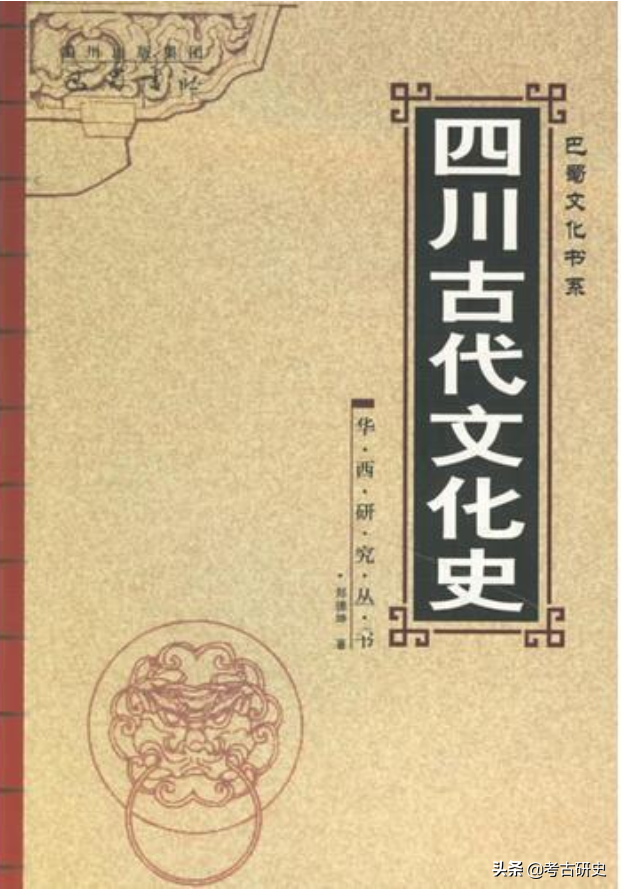
一、建国以前“广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提出与初步研究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建国以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发端,在两条线索上分别展开的。这就是广汉真武宫玉石器坑的发现与发掘、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1929年(一说1931年)春,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城西18里太平场附近真武宫南侧燕氏宅旁发现大批玉石器,其中不少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引起有关方面注意。1930年,英籍牧师董宜笃(A.H.Donnithone)函约成都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D.S.Dye)同往调查,获得一批玉器。戴氏据此撰《四川古代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Squares,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备记其事,并对器物用途等略加探讨,发表于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第4卷(1934)。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称从燕氏购得玉器4件,撰《古玉考》一文,发表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1935),文中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1933年(一说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教授及该馆助理馆员林名均应广汉县政府之邀,在燕宅旁开展正式田野考古发掘,颇有收获,由此揭开了日后三星堆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序幕。
1934年7月9日,时旅居日本并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广汉发掘所取成果的兴奋心情,并认为广汉出土玉器与华北、华中的发现相似,证明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他还进一步从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曾参与周人克商等史料出发,认为广汉遗址的时代大约在西周初期。
1936年,葛维汉将广汉发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林名均亦撰成《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两文均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至于年代,葛维汉认为其最晚年代为西周初年,约当公元前1100年;林名均则将广汉文化分为两期,认为文化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则为周代遗物。
1946年7月,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作为该馆专刊之一。在这部著作里,郑德坤把“广汉文化”作为一个专章(该书第4章)加以讨论研究,从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等五个方面详加分析,不同意葛维汉、林名均提出的墓葬之说,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之间。
广汉发掘尤其“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的学者对广汉遗物与中原文化有异有同的现象开始寄予了关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广汉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特别重视。
比较而言,“巴蜀文化”概念的命运却全然不同。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十分热烈的争论,直接导致了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的最终确立。
当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时候,还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与中原文化有别的青铜器文化来看待的。其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时有青铜器出土,以兵器为多,形制花纹与中原青铜器有异,流布各地以至海外,被人误为“夏器”。抗战爆发后,学者云集四川,遂对这些异形青铜器产生兴趣。卫聚贤搜集这批资料,写成考释论文,题为《巴蜀文化》,发表于《说文月刊》3卷4期(1941)和3卷7期“巴蜀文化专号”(1942)。他在文中将这批兵器分为直刺、横刺、勾击三类,并摹写出器体上的各种纹饰。他认为,春秋以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战国时仿中原文字。对于蜀国青铜器的年代,则断在商末至战国。
卫文刊布后,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知名学者力驳卫说,认为卫文所举青铜器,不是中原兵器,便是伪器。如像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考古学家郑德坤,都不同意卫聚贤的看法。在当时四川地区尚未大力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的情况下,人们大多从古人言,认为巴蜀蛮荒、落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由此怀疑巴蜀文化的存在,全盘否定巴蜀青铜器,却显然是“中原中心论”长期占据学术统治地位的结果。
在“巴蜀文化”命题提出的前后,学术界还从文献方面对巴蜀古史进行了研究,辑佚钩沉,试图重建巴蜀的古代史。发表的论著中,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旧题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以及先秦汉晋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这些新著论文,大多限于微观研究,视角不广,几乎没有提出成体系的观点。
1941年,古史辨大师顾颉刚在四川发表重要论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清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巴蜀的多数材料,彻底否定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说”,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氏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其实质在于,他实际上已洞见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和巴蜀文化区系的问题,而此类问题正式提上研究日程并为学术界所接受,却是40年以后的事情,足见其大师风范。
考古学方面,冯汉骥等人调查了成都平原的“大石文化”遗迹,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到周代,即秦灭巴蜀以前的遗迹,部分证实了文献有关记载的可靠性。吴金鼎、凌纯声、马长寿等著名学者也在四川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史前遗址屡有发现。郑德坤比较全面地搜集了当时可能看到的四川考古材料,详加排列整理,出版了《四川古代文化史》专著。尽管郑氏并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但这部著作对于研究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巴蜀文化的讨论激发了一大批学者的热情,人们纷纷著文参加讨论,各抒己见。董作宾著《殷代的羌与蜀》一文,发表在《说文月刊》3卷7期“巴蜀文化专号”上。他仔细搜求当时所见甲骨文,确认有“蜀”,并根据甲骨文中蜀与羌每在同一片上甚至同一辞中的情况,断言蜀国在陕南一带,并不在传统上所认为的成都。在董作宾之前,唐兰也曾考释了甲骨文中的“巴方”和“蜀”,认为在今四川。陈梦家也承认甲骨文中有“蜀”,指为西南之国。郭沫若亦从此论,但认为甲骨文中的蜀“乃殷西北之敌”。胡厚宣承认甲骨文中有蜀,不过他认为此蜀并不是四川的蜀国,而是山东的蜀,“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童书业则认为巴蜀原本都是汉水上游之国,春秋战国时才南迁入川。徐中舒在其享有盛誉的论文《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认为巴、蜀均南土之国,殷末周文王经营南国,巴蜀从此归附。
此外,在四川史前文化的调查方面也取得初步成果。1886年英人巴贝(C.F.Babei)在重庆附近购得磨制石器2枚,西蜀有石器文化遂闻于世。1913年美国哈佛大学叶长青(J.H.Edgar)在西康采集到打制石器材料。1925~1926年美国中亚考察队格兰杰(Walter Granger)在万县盐井沟发现1件与更新世动物化石群同时的穿孔石盘。1930年德国人阿诺尔德·海姆(Arnold Heim)在西康道孚发现2件刮削器。1931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包戈登(Gordon Bowles)在道孚附近发现史前遗址多处,采集石器数十件。1935年法国人德日进(Teilhard Decheadin)与中国生物学家杨钟健在万县西约10公里的长江第一阶地上采集到1件新石器时代以前的石器。还有一些学者对巴蜀的物质文化、古史传说、政治史,以及史前文化进行了探讨,对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
综观建国前的巴蜀文化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大多数是对古代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辨伪,初步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局部的发掘,并加以排列分类,这仍然主要是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但以考古材料包括殷墟甲骨文来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却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框架,开创了以近代方法论研究巴蜀文化的新风,为后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石。
第二,提出了巴蜀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课题,包括巴蜀的地理位置,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考古学上巴蜀遗物的真伪,以及巴蜀史料的纠谬释疑等等。从这些内容很容易看出,尽管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新方法,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很有水平的新观点,但就整个课题设计及方向上看,未能提出超越传统史学体系的新鲜内容。并且,论者往往仅从微观角度立论,缺乏把握全局的宏观眼光,因此常常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而广泛地进行研究。
第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从青铜器的角度同中原文化进行了初步比较,并提出了巴蜀有文字的初步看法。同时,从文献研究的角度透视了巴蜀古史,第一次把巴蜀作为无论其历史还是文化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国来加以看待。这些成果,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深入,但却涉及了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层面,而这几个层面正是今天学术界关于文化与文明史研究的基础所在。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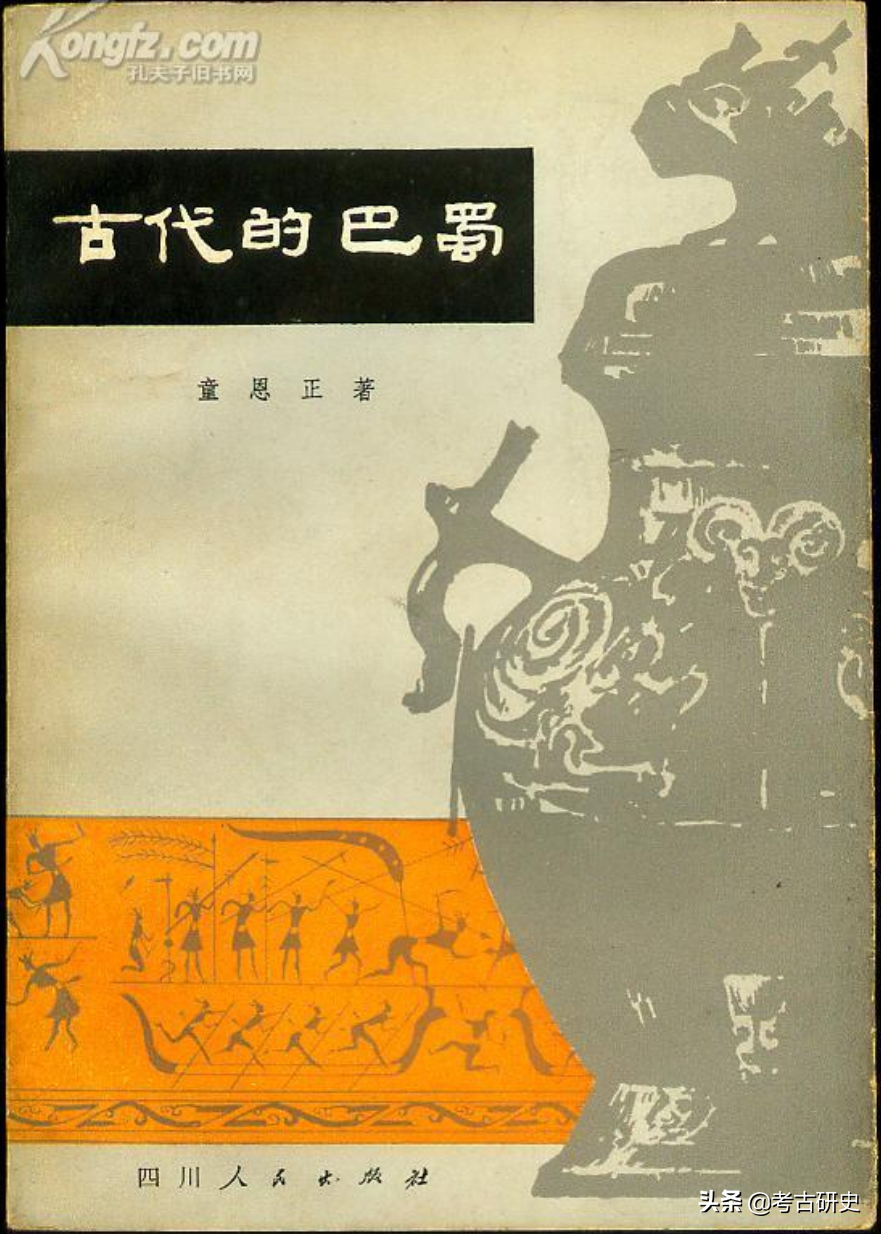
二、对巴蜀文化基本内涵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巴蜀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对巴蜀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也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徐中舒发表的《巴蜀文化初论》,是建国以后第一篇论述巴蜀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徐中舒从经济、政治、民族、地理以及文字等方面入手,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他指出,四川古代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文化区,但与中原有经济关系,文化上受中原较深的影响。蜀国在战国时代已进入国家,而巴国则一直盛行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姓统治。巴早在先秦已有初等文字,巴文是中原文字的不同分支。在这篇文章中,徐中舒还初步研究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区别和联系,不过没有明确指出这两支文化之间的关系。
蒙文通紧接着发表了《巴蜀史的问题》这篇重要论文。文章概述了他对巴蜀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巴蜀的地理位置大抵以《华阳国志》所记较确,并包括那些与巴蜀同俗的地域。蒙文通还认为,蜀国最初起源于岷山一带,后来才迁居成都平原。并认为,巴蜀的文化自古就很发达,巴蜀文化并非始于文翁兴学,巴蜀文化的内涵丰富多彩,其天文星象学自成一体(此本吕子方之说),词赋、黄老、历律、灾祥等是巴蜀固有的文化。蒙文通这篇论文的一些主要观点,为后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所逐步证实。
缪钺发表《巴蜀文化初论商榷》,针对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所提某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引起了徐中舒另一篇宏论《巴蜀文化续论》的发表。
在《巴蜀文化续论》中,徐中舒广征博引,从社会性质、民族学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他对巴蜀文化的再认识,并提出巴国非廪君,原居江汉平原,后受楚逼凌,被迫向西南进入大巴山地区,到战国才西迁到川东,与蜀邻敌,而川东古为蜀壤等观点。这篇论文,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首次从地域上说明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空间构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述几篇专论,不仅继承了建国以前巴蜀文化研究的成果,深化了巴蜀文化命题,而且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并使之走上科学研究的轨道,为学术界提供了新认识。
对巴蜀文化加以科学性规范化界定是在“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童恩正出版《古代的巴蜀》专著,对巴、蜀的涵义及其沿革做了考察,认为巴蜀文化是青铜时代的文化,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带有独特的地方风格。童恩正关于巴蜀文化内涵和性质的提法,基本上因袭了其先师冯汉骥的观点。冯汉骥的遗作《西南古奴隶王国》于1980年发表。这篇论文指出,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巴、蜀文化在大体上虽然相同,但从一些文化遗物上仍能加以区别。蜀人似乎没有文字,巴人的各种符号似乎是文字的雏形。蜀大约在殷周之际进入阶级社会,巴人的社会则较蜀人落后,直到秦灭巴时,巴尚处于奴隶制的初期阶级。并指出,巴蜀文化虽有明显的地方性,但仍属于中原汉文化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蜀文化近乎关中和黄河流域,巴文化则近乎楚。
20世纪8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更向纵深发展,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认识又有若干新的成果,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巴蜀文化时空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认为,考古学所说的巴蜀文化,不光是指巴国和蜀国的文化,而应包括巴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既包括商周杜宇族建立国家之前巴蜀民族文化形式的前期遗存,也包括公元前316年巴蜀被秦统一之后仍保持本民族习俗的巴蜀遗民的文化的遗存。据此,他把巴蜀文化的上限提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称为早期巴蜀文化;地域上,他认为巴蜀文化的分布地区与两国边境并不完全一致。李复华、王家祐在《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一文中,不同意把巴蜀文化的上限推前到新石器时代。他们认为,蜀的早期文化,广汉三星堆第二、三两期可能是其第一阶段,而三星堆第一期新石器文化则是蜀文化的前身。早期蜀文化是一种土著文化,但受中原影响较深,成为这阶段蜀文化的重要内涵。蜀文化的下限,从考古学上看可延续到西汉初期。至于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合流,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才有“巴蜀文化”。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许多学者在讨论巴蜀文化时,都提到了对其内涵的认识。一般说来,这种认识目前还主要限于考古学文化,即巴、蜀两族或两国的物质文化遗存。时序方面,多数论著把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视为先蜀文化,而把蜀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从夏代至春秋,晚期从春秋战国至汉初。空间位置方面,林向提出,殷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通,并提出“巴蜀文化区”的概念。段渝通过对三星堆文化与汉中、大渡河流域、川东鄂西相似遗存的考察,提出“古蜀文化区”的概念。这两个文化区的概念大体相通,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至于川东鄂西的古文化,一般依其发现地名称为“某文化”、“某类型”、“某遗存”,也有论著称其为“早期巴文化”,不过没有取得学术界的共识。段渝认为,巴文化有三个层次,或三种概念:一是战国以前位于汉水上游的巴国文化,一是长江三峡川东鄂西巴地的史前文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巴国进入长江流域与当地的巴地文化合流所形成的复合共生的地域文化,这个时候的巴文化才是可以用“巴”来涵盖并指称国、地、人、文化的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从而形成巴文化区。巴文化区大体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其文化内涵的基本特点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巫鬼文化非常发达,形成巫文化圈;乐舞发达;崇拜白虎与敬畏白虎信仰的共生和交织;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传统;民众质直好义,土风敦厚,等等。
先秦巴蜀文化事实上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而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总和。巴文化是指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蜀文化是指蜀族和蜀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将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古代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首先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即它们在古代是紧相毗邻,而在中、近古以迄于近现代又是省区与共的。其次导源于战国以来两者文字的相同,中古以来两者语言的一致,经济区的大体划一,以及其他诸多原因。这许多因素使两种文化逐渐融而为一,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
90年代初以后,对巴蜀文化时空内涵的认识又有了新发展。一批学者主张,巴蜀文化有“大巴蜀文化”和“小巴蜀文化”之分,即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和狭义上的巴蜀文化。所谓“大巴蜀文化”,是指从古到今的四川文化。这些学者以谭洛非、谭继和、袁庭栋等为代表。袁庭栋的《巴蜀文化》专著,综论了四川古代文化的主要方面。谭洛非发表了《关于开展巴蜀文化研究的建议》,建议全方位地研究四川从古到今的全部文化史。谭继和发表了《巴蜀文化研究综议》等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对巴蜀文化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认为从古至今的巴蜀文化可划分为七大阶段: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为巴蜀文化的萌芽和巴蜀文明的形成,商周包括春秋战国为巴蜀文化重心由江源和山地向平原和城市的转移,汉魏南北朝为巴蜀文化的第一次鼎盛和第一次转折,隋至元代为巴蜀文化的第二次鼎盛及第二次转折,明清为巴蜀文明历史地位的挫折及其向近代化转化的契机,1840~1949年为近代巴蜀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及其近代化发展的滞缓,建国后至今为现代巴蜀文化面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历程。
至此,巴蜀文化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三种概念:一种是先秦巴蜀文化,即原来意义上或狭义的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采用最为普遍,并得到中外学术界的肯定;一种是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主要运用考古理论与方法研究先秦巴蜀的物质文化,这一概念得到全国考古学界的肯定;另一种是广义巴蜀文化,研究从古至今巴蜀地区的文化,这一概念越来越取得各界的认同。

三、巴蜀考古的新发现
正如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的研究一样,巴蜀文化的研究是建立在以考古学和古文献为主要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由于文献不足征,考古学的新发现就愈益显示出其特殊地位和作用。1980年代以来巴蜀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都是充分运用考古新材料的结果。
建国以来,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给考古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发现层出不穷,其中重要的发现有:
1.四川广元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葬。1954年在昭化(今属广元市)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发现大批船棺葬,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和印章,其时代为秦灭巴蜀前后到汉初。这些器物,为学术界认识考古学上的巴文化提供了标准的衡量尺度,并使人们确信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巴蜀文化的存在。船棺葬式,最初认为是巴文化的重要特征,后来由于川西平原也发现了大量船棺葬,仅形制稍异,又使学术界认识到蜀文化同样也有船棺葬传统。
2.成都羊子山土台。1953年~1956年在成都北郊清理的这座大型土台,残高10米,台底103.6米见方,最上层31.6米见方,为三级四方形土台,这是现存先秦最大的土台。土台年代,原报告认为是西周到战国。后经林向研究,提出其始建年代可能为商代。土台性质,一般认为是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或古蜀国巫觋通天地的神坛,即大型礼仪中心。
3.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墓葬。1957年~1958年在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水观音发掘的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和青铜器。墓葬年代,早期墓为商代,晚期墓为西周到春秋。遗址年代为商末周初。这一发现,为商周与春秋战国巴蜀文化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序列依据。
4.四川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1959年和1980年分别在彭县竹瓦街发现窖藏铜器,有容器、兵器、工具,年代为殷周之际。其中2件青铜觯上有铭文,徐中舒考定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证实了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的记载。
5.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1965年清理的这座墓葬,出土不少青铜器,其中一件水陆攻战铜壶,壶面有习射、采桑、宴乐、弋射、水战等图案,十分精美,全国罕见,铸于蜀国,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这座墓葬为战国蜀人的铜兵器的研究提供了断代的标尺。
6.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1972年在川东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土坑墓,出土大批青铜器,墓主为巴国上层统治者。徐中舒研究了出土的虎纽钅享于,认为这种器物是中原文化的传入,后来成为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并认为,墓主可能是巴国众多部落中的小王之一。段渝认为,墓主可能为巴国王子。对于墓中所出14枚一组的错金编钟,邓少琴考证为古代小架所用。墓葬年代,徐中舒、唐嘉弘认为是秦昭王时期,王家祐认为是秦厉共公时期,于豪亮认为是秦始皇时期。这批墓葬的发现,为解决巴国历史地理上的一些问题以及巴与楚、秦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7.有铭青铜戈。1970年代在四川郫县发现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在新都出土一件有铭文的青铜戈,1973年在重庆万县发现一件有铭文青铜戈,1959年在湖南常德26号战国墓出土一件巴蜀铭文青铜戈,文字似汉字而非汉字,为确证巴蜀有文字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8.四川犍为巴蜀墓群。1977年发掘,年代为战国晚期,少数为汉初,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等。王有鹏认为,这批墓葬,为研究古文献记载的蜀人南迁提供了可靠的地下证据。
9.四川青川墓群。1979年~1980年在青川清理了82座土坑墓,出土陶器、铜器、漆器、竹木器、玉石器等400多件,并出土秦武王时在巴蜀推行田律的木牍。时代为战国中期和晚期。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划文字,既有汉字,又有巴蜀文字,为巴蜀符号确属文字提供了坚实依据。出土的漆器,表明巴蜀漆器与楚器有着相当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批墓葬中巴蜀与秦、楚文化因素并存,为深入研究其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10.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1980年发掘的这座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大型带斜坡墓道的土坑木椁墓,椁内分出棺室和8个边箱,棺具为独木棺,椁室出土青铜器188件,青铜器多5件成组,或2件成组,显示出特殊的礼制。青铜器中的鼎、敦等器,与楚文化有相似之处。沈仲常认为此墓是比较典型的楚文化墓葬,所出“邵之食人鼎”,“邵”为“昭”,即是楚昭王之意。徐中舒、唐嘉弘认为这种楚国昭氏器物,表明有可能楚之昭氏驻蜀地。李学勤认为,新都墓部分青铜器与楚器形制的相近,应是道一风同的缘故,即同一时代流行同样的艺术和风格,应是蜀器。段渝提出,此墓并不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的特征,确为蜀墓,至于青铜鼎上的“昭”字,应是古代的“昭祭”,而不是楚之昭氏。李复华、王家祐认为,该墓墓主应是蜀王开明九世到十一世当中的某一位,是为蜀王之墓。这座墓葬的发掘,为深入认识战国时期蜀文化的丰富内涵、蜀文化的特征、蜀国的礼制以及蜀、楚关系和蜀与中原的关系提供了新认识。
11.四川荥经巴蜀文化遗存。1981年在荥经烈太清理的墓葬内,出土印章等巴蜀文化遗物。1981年、1982年在荥经曾家沟发掘的战国墓群中,出土大量漆器,有的漆器上有铭文,尤其是“成”、“成市造”等铭刻的发现,为探讨巴蜀漆器的生产规模以至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资料。
12.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980年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墓葬4座,出土数万件陶、石、金、铜、玉石器物。文化堆积分为4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约距今4800~4000年;第二、三、四期为蜀文化,年代约从夏代到西周早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位于遗址中部的古城遗址,总面积3.6平方公里。1986年夏季在南城墙外发掘的两个器物坑内,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近千件,尤以大型青铜雕像和金杖、金面罩等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珍贵之物为奇特。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楚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而城墙的发掘,文物坑内所出与中原迥然有异的青铜器,以及文字符号的发现,为商代蜀文化业已进入文明时代,它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起源地等崭新观点的提出,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物证据。
13.成都十二桥遗址。1958年底、1986年至1987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商代地层内,发现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房顶、梁架、墙体、桩基、地梁等,基本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具有明显的共性和发展连续性。大型地梁式宫殿建筑与小型干栏式建筑浑然一体,错落有致,分布面积为15000平方米以上。在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南北延伸的数公里,还发现多处商周时期古遗址,文化面貌与十二桥相同,它似是成都这个总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商周之际的成都是古蜀文化的又一个中心,另一方面又以其文化发展演变的同步性展现出成都早期城市起源的历史进程。
14.四川绵阳边堆山遗址。1989年发掘的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石、骨器和房屋基址红烧土等标本数千件,年代距今5000~4500年上下。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四川盆地文明的起源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15.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1992~1993年、1994~1995年曾进行过数次小规模试掘,1997年进行大规模发掘,确定这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巴人遗址。1997年的发掘,出土的巴人遗存有40座墓葬、多座房屋基址、3座窑址和大量遗物,时代从商周到战国时期。其中商周时期的墓葬1座。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少量漆器、铁器、玉石器和琉璃器。此次发掘,对于深入认识巴文化尤其三峡地区的巴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6.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该遗址属于忠县洽甘井沟遗址群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根据1994年和1997年较大规模发掘的结果,哨棚嘴遗址可以分作三期,第一期的年代范围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之间;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左右至二里冈下层,文化面貌近似于三星堆文化早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文化面貌近似于成都抚琴小区第4层。哨棚嘴遗址的发掘,为探索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在川东地区的分布范围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7.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以及大邑盐店和高山等8座早期城址,经不同程度的勘探和发掘,证实这些城址是早于三星堆文化(不含三星堆遗址一期)的早期城址。这批城址的年代略有差异,总体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群,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绝对年代,初步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的发现,为分析文明起源时代古蜀地区政治组织的发展变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18.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发掘,确定是一处蜀王开明氏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墓坑长达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墓坑中现存船棺、独木棺葬具17具。船棺规模、形制宏大,最大的一具长达18.8米,为其他地区所未见。随葬品虽被盗过,仍出土陶器103件、铜器20件以及漆、木器153件等。遗迹显示,墓葬有布局规整的地面建筑。此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的发现,为探讨蜀王开明氏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至与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19.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2000年10~11月在茂县发掘的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82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约距今5500~5000年左右。出土灰坑26座、灰沟1条和地面或房屋基址3座,遗物包括陶器、玉器、骨器等。陶器以平底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器形多样,纹饰丰富,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彩陶器与西北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均有差异。文化面貌与绵阳边堆山、广元张家坡、邓家坪等遗址有一些相同之处,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为认识5000年以前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情况提供了新材料,并为深入探讨古蜀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有益的启示。
20.成都市金沙村商周遗址。2001年2月以来在成都市金沙村发现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分布范围约3平方公里,是一处十二桥文化的大型遗址。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一文化堆积区内有一定布局结构,出土大量青铜器、黄金制品和玉石制品,包括金器40余件、青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近300件、象牙40余件等计2000余件,还发现大批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青铜器、金器与三星堆有同有异。玉器种类尤其丰富,其中不少种类是首次出土。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去踪提供了重要线索,为进一步探明古蜀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以上重要考古发现外,四川和重庆境内大体均有古文化遗存出土。在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区划以外,也有不少巴蜀文化遗存发现,较重要的有陕南、鄂西、湘西和贵州等地区,为研究巴蜀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交流与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新材料。这些考古新发现,促进了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新认识,使人们对以前关于巴蜀为蛮荒之地的陈旧看法彻底改观,取得了古代巴蜀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的新共识。
四、巴蜀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与分歧
建国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研究内容为巴人和蜀人的族属、地域、迁徙、列国关系等,基本上是传统研究课题。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巴蜀的来源、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对传统研究有所突破。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研究巴蜀文化的来源,巴蜀古文明的起源、形成、内涵、内外关系等,无论在研究方向、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巴蜀文化研究出现了崭新气象,研究更加深化,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
巴蜀文化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大,内涵非常丰富,成果层出不穷。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的主要成果分成14个方面略加述评。
1.巴蜀的族属、地域和迁徙
建国后对巴蜀文化的第一阶段讨论中,族属、地域和迁徙问题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巴蜀文化研究中事关重大,所以至今仍有争论。
徐中舒首先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
蒙文通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灭的巴是姬姓之巴,楚灭的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即是枳巴。
缪钺提出,廪君之巴与板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
邓少琴、童恩正等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白皋之巴,应源出氐羌。董其祥《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宗贝、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
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4个巴国。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宗贝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宗贝族和獽蜒族。
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的巴人和狭义的巴人这个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宗贝、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关于蜀人,看法也不是一致的。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蜀人出自氐羌民族系统,一种认为蜀人出自百濮民族系统。这两种意见中,也有种种分歧,不一而足。一般认为,夏商时代的蜀人,即蚕丛、柏濩、鱼凫,与氐羌民族有关,杜宇、开明则与百濮民族有关。蒙默提出,古代没有一个统一的蜀族,历代蜀王都分属不同的族系。孙华则提出,蜀人既非西北氐羌,亦非江汉濮人,而来源于商代黄河中下游的一支氏族。张勋燎认为,鱼凫氏来源于川东巴人。徐中舒、唐嘉弘提出,蜀王开明氏为荆楚之人,童恩正认为是巴人,段渝认为应如史籍所述为原居贵州水的濮人,既非楚国人,亦非巴国人。
以上问题是逐步深化的,主要成果在于明确了古代巴、蜀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明确了巴、蜀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直接材料和相关材料的理解不一,同时在理论上也有分歧以至模糊不清之处,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若干差异。
2.巴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
这个主题在建国以前涉及很少,建国以后的第一、二阶段,也限于资料的贫乏,难以深入,第三阶段则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史料记载巴蜀蛮荒落后,无文字,无礼乐,俨如原始社会末叶的军事民主主义。建国后,徐中舒首先指出,蜀有高等农业,至迟在战国已具备了国家形式,巴则是部落组织,尚未形成国家。但认为从殷周到战国,巴蜀的经济和文化还落在中原后面。这种看法,长时期占居巴蜀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只是到1986年以后,由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学术界才开始改变了这种传统认识,一致认为商代蜀国已是比较成熟的国家。
关于巴蜀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目前在蜀人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巴人以粗耕农业兼营狩猎畜牧等方面,学术界基本拥有共识,但在蜀地农业的起源方面,则存在分歧。有的认为蜀人的农业发源于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有的认为蜀人的稻作农业来源云南,有的则认为蜀地稻作农业是土生土长的。由于文献不足征,考古材料尚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这些看法目前都还处在假说阶段。
商业的发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大要素。“文革”前少有论著对此进行过研究。张勋燎《古璧和春秋战国以前的权衡(砝码)》提出,古蜀国的大量石璧,应即用以“均物平轻重”的砝码,此本郑德坤之说。更多学者则认为,石璧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考古中,巴蜀墓葬内常出土一种形制如璜的“桥形币”,多数学者认为是巴蜀的一种货币。对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穿孔海贝,也认为是贝币。这样,考古发现便证明了古蜀国确有发达的商业。徐中舒还提出,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童恩正也认为,战国时代成都与中原各地以至中亚地区都存在商业贸易关系。段渝还根据多种资料进一步指出,早在商代,成都平原的广汉蜀王都和成都,就已初步形成为中国西南同南亚、西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关于巴蜀的社会形态,分歧也是较大的。传统的看法认为巴蜀是奴隶社会。唐嘉弘认为,古代巴国并非奴隶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从原始社会的家长奴隶制阶段向封建化过渡,并未形成一个发达或发展的奴隶王国。《四川通史》第1册认为,开明氏蜀王国不是奴隶制王国,而具有若干领主封建制特征,属于早期的封建社会。
对巴蜀社会形态的认识,随着学术思想和学术热点的变化与转移,已归入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内涵更加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中。
3.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其重要意义在于搞清楚人类与文化进化的关系,人类文化的成长、变迁,文化类型、结构和功能,政治组织的形态,以及文化进化的动力法则等等。文明形成主要有几大标志,物质文化标志有文字、城市、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社会形态标志是国家的形成,即公共权力的设立和按地区划分其国民。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两大背景。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首倡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框架的论断,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突破了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从中原起源)的传统看法。一是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等,与中原青铜文化迥异,迫使学术界重新思考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个重大课题。
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首先是关于两个“祭祀坑”的报道和发掘简报,披露了资料,进行了初步研究。李学勤、林向、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沈仲常、罗开玉、霍巍、段渝等,分别对三星堆青铜文化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研究,认识到古蜀青铜文化的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商代中期,比起传统的看法,早了近千年。
1980年代末,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试掘,确认了古城城墙,认识到三星堆是商代蜀国的都城。苏秉琦教授提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段渝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巴蜀早期城市,提出了巴蜀城市的起源模式、城市结构功能、城市体系等问题,并将巴蜀古代城市同中外早期城市进行了概略的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W·贝格勒认为三星堆是商代主要都市之一,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第三个中心。
巴蜀国家的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蒙默、段渝、胡昌钰和蔡革等,均有论述。但关于这个问题,多数论著限于考证三星堆文化如何与文献所记“三代蜀王”相衔接,没有更多地研究国家形式、政治结构等内容。段渝通过对三星堆文化的物资流动机制的研究,提出古蜀王权性质是神权政体,从分层社会的复杂结构、基本资源的占有模式、再分配系统的运作机制、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并讨论了王权的深度、广度和阶级结构、民族构成等问题。
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三星堆宏阔的古城、辉煌的青铜文化,是商代长江流域城市文明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从青铜文化而言,其青铜合金技术、铸造工艺和青铜制品种类均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李学勤因而提出,蜀文化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段渝也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当前,关于古蜀文明有其独立而悠久的始源,有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是一支高度发达的灿烂的古代文明等观点,在学术界已取得普遍共识。
文明起源的问题,是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学术界深切关注和热烈争论的重大学术理论课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证性极强的课题。中国学术界从1980年代初中期开始对这个重大课题形成研究热潮,并逐步形成在对各区系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进而全面深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格局。作为重要的区系文明之一,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由于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群的发现,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
在1990年代以前,由于学术界对文明时代与文明起源时代这两个紧密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范畴有相当的模糊以至混淆,不少学者在探讨文明起源的时候,事实上是把文明时代当作文明起源时代加以分析论述的,因而对巴蜀古代文明起源这个问题的研究多是无功而返。另一方面,由于文献难征,考古资料也还不足以提供比较清晰的线索,有些学者把巴蜀文明的起源直接与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相联系,多数学者则认为巴蜀文明的起源含有更多的土著文化因素,尤其与岷江上游古文化有关,而外来文化因素则是巴蜀文明得以最终形成的重要外部动力之一。不过,有关探讨多半属于文化来源或文化类型问题方面的讨论,还不能说接触到了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刻实质。
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文明诸要素的起源,以及文明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要素包括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和国家,其中最重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要素是国家。因此,除从物质文化要素方面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外,须从政治组织的演化角度进行分析,才可能从本质上充分透彻地阐明文明起源的问题。在关于文明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演化形式上,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由农耕聚落到大型聚落再到中心聚落是其演化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酋邦组织是文明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在对巴蜀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林向、段渝运用酋邦制理论来分析巴蜀文明的起源。段渝提出,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要素其实是政治组织变化过程中所先后产生的物质文化成果,从功能的观点看,这些物质文化成果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政治组织的变化及其需要所制约的。据此,他认为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完整的酋邦组织,由各座古城的共存所形成的古城群,则是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是文明的前夜,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来临。同时还分析了史册所载鄂西清江流域的巴氏廪君集团酋邦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途径。彭邦本根据酋邦理论,在早年蒙文通所说巴蜀不过是两个区域内联盟的盟主或霸君的基础上,认为从宝墩文化古城直到秦灭巴蜀,历代古蜀王朝均为共主政体。江章华、王毅、张擎则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角度,勾勒了古蜀文明起源尤其城市起源的进程。这些分析讨论,把巴蜀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推进了一步。
巴蜀古文明的研究,当前多数学者的兴趣还是集中在族属、文化来源、青铜器形制等方面,这些方面发表的论文最多。从考古学上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必须的,从历史学上看,又是不够的。正如苏秉琦所指出的,考古资料本身不等于历史,依照考古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从考古学到历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抽象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因此,要从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继续深入探索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演进,尚需今后进一步努力。
4.巴蜀文化与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关系
学术界大多认为:古蜀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从政治上看,古蜀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同中原夏商王朝不存在直接隶属的关系,但西周初年成为西周王朝的封国,与周王朝有较密切的关系。巴国为姬姓,是周王室分封到南方的一大诸侯国。文化上,受到了中原文化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还是当地土著文化。
古蜀文化与黄帝和夏文化的关系,过去认为是黄帝后代,完全就是中原文化的分支。上世纪40年代疑古派对此大加批驳,一概否定。1950年代,徐中舒认为,黄帝与巴蜀的关系是子虚乌有,除牵合几个人名、地名外,完全没有根据。蒙文通则认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由于没有新的证据,这个重大问题很快就被搁置起来。
19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史研究热潮的风行,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的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
谭洛非、段渝撰《论黄帝与巴蜀》、《再论黄帝与巴蜀》两文,段渝撰《论黄帝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从文献与考古综合分析的视角,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末商初由夏遗民与当地土著结合所创造的一支新型文化。为此,林向撰《蜀与夏》一文,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城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祁和晖、冯广宏等均持类似看法。谭继和撰《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进一步认为,禹治水始于岷山,扩及九州,提出夏文化初起于西蜀,而兴盛于河洛的看法,并概括为“夏禹文化西兴东渐”之说。段渝《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认为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实证的契机。
巴蜀与商文化的关系方面,1950年代王家祐等提出其间有较深的文化联系,后来冯汉骥认为巴蜀文化属于中原文化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文化。沈仲常、黄家祥1980年代提出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关系。林向认为古蜀是殷商的西土和外服方国。段渝认为古蜀不曾成为商王朝的外服方国,其青铜文化的主体和一些政治制度与商不同,古蜀由于控制了从中原通往南中的金锡之道,而与商王朝在资源贸易的基础上发生和战关系。
关于商代的巴,目前对殷卜辞中是否有“巴”还存在相当分歧,巴与商文化的关系亦少有专文研究。
巴蜀与周文化的关系方面,由于有少量文献可征,意见比较一致,近年的主要成果是根据考古所获大量资料,明确了蜀人参与伐纣,受西周王室分封的史实。
巴蜀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过去学术界曾长期持巴文化近楚、蜀文化近秦的观点,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若干重要突破。李学勤提出,秦文化中的鍪釜甑,是从蜀文化当中吸取的,而后又流布其他地区。林春认为,夏商时代江汉平原的若干文化因素,来源于成都平原蜀文化。段渝认为,长江三峡地区、陕南汉中地区夏商时代的古蜀文化因素与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扩张有关,尹盛平、赵丛苍等则认为陕南古文化与巴文化有关。江章华认为由于二里头文化从鄂西沿长江西进,成都平原于是诞生三星堆文明,川东鄂西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李学勤认为,商周时的蜀文化较多影响了楚文化。徐中舒、唐嘉弘、沈仲常认为战国时楚之昭氏后代驻蜀,战国蜀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十分深刻。李学勤认为,蜀、楚文化的某些风格相近是道一风同的缘故。段渝认为新都蜀墓所出“昭之/鼎”,“昭”为“昭祭”,不足以说明是楚国昭氏之后,蜀、楚文化在若干重要方面有明显区别,春秋时代巴与楚曾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后来联盟破裂,巴被迫弃土南迁;江汉地区“信巫鬼,重淫祀”之风,与巴人的巫鬼文化有关,其根源在巴。澳大利亚N.巴纳认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其风格是受楚文化影响。段渝则认为这种文化影响的方向正好与巴纳所说相反。王有鹏认为,川滇之间出现的若干巴蜀考古遗存,证明了战国后期蜀人南迁的史实。段渝认为古蜀在商中叶后已控制南中,川滇之间的考古遗存不能完全视为安阳王南迁所遗。林向提出商代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和华南地区均有深刻影响,中华牙璋的起源和传播可以证明这个史实。
巴文化的问题更为复杂。1950至19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弄清楚了巴国的建国和迁徙,即巴国原建国于陕南鄂西与川北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才南下至长江流域,进入川东。但是对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怎样看待?三峡地区的巴文化与陕南鄂西川北之间的巴国是什么关系?由于资料不足,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为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学者提出巴为地区名而非国名、族名的看法,蒙默便力主此论。但这仍未很合理地解决文化类型问题。于是,有学者于1990年代初得出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的新认识,认为二者起源、地域、内涵均不同,直到巴国南下长江后,才整合起来,这时才有名实相符的巴文化。
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与古蜀文化即顺江东下的三星堆文化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三峡地区文化较早影响了成都平原古文化。对此,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
5.巴蜀文化与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关系
千百年来,四川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总被认为是僻处西南内陆,文化落后,与外界联系甚少,更谈不上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1980年代以前,学术界虽然注意到巴蜀与越南北部历史文化的一些关系以及巴蜀地区对于向南传播中原文化所发生的作用,但由于资料所限,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认识。
1983年童恩正发表《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除了提到巴蜀向越南等东南亚大陆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外,还研究了巴蜀文化本身在北越地区的传播,这主要是指青铜文化。同年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安阳王杂考》一章提出,战国末秦代之际,蜀人向越南的大规模南迁,对越南民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对三星堆文化因素的深入认识,段渝、霍巍及湖北张正明、云南张增祺、湖北万全文、美国许倬云、香港饶宗颐等,分别指出了殷商时期古蜀文化与西亚文明具有某种联系。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古蜀文化的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青铜神树以及海贝、象牙等文化因素集结,不仅与中国文化异趣,而且在古代巴蜀也无其来源的蛛丝马迹,而这些文化因素却能在西亚近东文化中找到渊源。段渝还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文化交流关系,提出了文化采借的看法。并从“支那”名称的由来以及西传的角度,讨论了先秦巴蜀与古印度的文化交流,认为公元前4世纪印度文献中说的“支那”,不论从史实还是音读考证,当为“成都”之称。对于中西交流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进一步实证,从而深化对古代巴蜀的开放与交流的认识。何/从文字源流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与中国商代文字的异同,认为三星堆刻符与印度河文字有紧密联系,在中国原始文字符号传播到印度河地带时起了桥梁作用。
6.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中西交通。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进抵罗马帝国的惟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不久以前,中外学术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丝绸之路的外延得到了大大扩展。
早在古代,《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但这些史料千百年来未受到认真对待。1960年代和70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国内已出版多部专著,日本出版专著1部(中国重庆学者著),论文集多部,论文达200余篇,电视系列片1部(川、滇两省合拍),大型画册2部,由四川的凉山州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和云南的曲靖文管所、瑞丽文管所等14个单位举办的大型文博展览10余次,召开“南方丝绸之路研讨会”2届。这些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南丝路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
7.巴蜀文字、巴蜀符号、巴蜀图语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这就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契机。
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巴蜀图语”等概念,王家祐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
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祐、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图语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
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
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
8.宗教和巫术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术界为古蜀文化恢宏的宗教场面所震惊,无不感到古老的蜀文化中宗教力量的巨大作用。这个问题在发掘简报中提了出来,认为古蜀宗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认为,古蜀盛行萨满文化,巫师以酒精性饮料处于麻醉状态,与天神相交接,据此主宰民意。范小平认为,古蜀人奉行原始巫教,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像就是为原始巫教的祭祀活动服务的。巴家云则否定图腾在古蜀文化中的地位,认为蜀文化早已超越图腾信仰阶段,奉行的是崇拜鬼神思想。段渝认为,古蜀的宗教是一个有中心、分层次的体系,其主体是宗教神权,而不是图腾崇拜,而神权又是与王权紧密结合、合为一体的。古蜀神权政体通过控制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工具,使政治权力宗教化,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从而实现其统治。刘弘认为,古蜀国统治下的诸民族信奉的是一种统一的宗教,至少各族的统治者在形式上皈依了这种宗教。赵殿增对巴蜀“原始宗教”作了多方面研究。看来,在研究巴蜀宗教与巫术这个问题上,有些理论问题还得首先解决,才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宗教、巫术及其社会功能提供正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论。
9.巴蜀的哲学与学术
蒙文通在《巴蜀史的问题》中,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巴蜀的词赋和哲学,认为战国时代蜀人的哲学受道家影响较大,蜀人臣君子远在韩非子以前已有著述,传于汉代,书在道家,可能是严君平学术的来源。并认为史籍所载秦相商鞅之师尸佼在蜀作《尸子》是可信的,尸佼的著作也是通过蜀人流传下来的。段渝认为,古蜀的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贯穿于诸方面,与儒家、法家均格格不入,与“神道设教”的墨家亦无共同之处,古蜀源远流长的方术神仙家传统使它成为道教土壤,最终发展成为汉末道教的重要起源地。
古蜀的史学,过去不曾有人提出研究。蒙文通曾讲到《山海经》中的《大荒经》作于蜀,认为“蜀王有其家史”,惜无详实论证。段渝提出古蜀的“史学之源”问题,认为古蜀人崇尚历史的传统可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山海经》中的一些篇章就是根据古蜀王的历史写成的,并对古蜀史材料在古蜀和中原地区的流传情况作了分析讨论。
由于书阙有间,要对古代巴蜀的哲学与学术进行深入研讨,确实困难重重。如果将来考古能够发现巴蜀文献,当可以充分研究这个问题。
10.艺术
巴蜀艺术多种多样,丰富而又充满神秘气息,很早就吸引着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的注意。80年代以前,学术界主要关心的是巴蜀青铜艺术,包括兵器、礼(容)器形制和花纹、图案,以及各种巴蜀图语。1986年三星堆发掘后,人们发现,古蜀艺术中的大型青铜雕像自成体系,与中原有别,普遍感到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的一大空白。而黄金面具、金虎、金杖等,其造型艺术和制作工艺,在同时代的中国都处在领先地位,堪称商代中国黄金制品南方系统的杰出代表。
11.科学技术
巴蜀科学丰富多彩,但大多数仅以实物形式被发现,几乎没有通过历史文献流传下来。学术界从青铜器制造技术、冶金术、建筑术、纺织术、制陶术、制玉术、酿造术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也从天文学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巴蜀科学评价甚高,尤其青铜合金、建筑、天文历算等几项,普遍认为水平很高,完全不亚于中原文化。
例如青铜合金,古蜀很有特色,并且在使用某些元素如磷等方面,十分具有科学性,铜焊技术也早于中原数百年。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的地梁,也优于中原建筑。天文学方面,古蜀的天文星象术代表着中国天文学的南方系统,具有很高水平,还影响了汉代天文学。但比较而言,对巴蜀科学技术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
12.巴人与土家族
潘光旦于1955年著文指出,巴人是今天湘西北土家族的先民。此论一出,各种反映蜂起,赞成者有之,怀疑者有之,补充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学问题大讨论。到目前为止,从主要学术观点看,多数人支持土家族出自古代巴人的论点,这样的论点在当代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生了重要作用。
13.氐羌民族研究
氐羌民族原居中国西部高原黄河上源地区,主要分布在甘青和川西北。1960年代中期,冯汉骥、林向、童恩正等认识到岷江上游文化与氐羌民族的南迁有关。多数学者还认为,氐羌人是蜀人的先民之一,夏商时代南下成都平原。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合著的《羌族史》,是研究并总结氐羌历史的一部力著,这部著作于1984年出版,学界评价很高。杨铭的《氐族史》是又一部详细研究西北民族的力著,对川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罗开玉《中国西南民族墓葬研究》一文,从考古学上研究了氐羌入蜀的年代和历史。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从多种角度探讨了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民族文化与历史,颇具学术价值。
14.濮越民族与夷系研究
四川古代除氐羌民族外,濮越民族是又一个大的民族系统。李绍明、蒙默、童恩正等对这个民族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般认为,川东地区以濮人为主,川西南地区的濮越人群团也纷繁复杂。对于濮人问题,蒙默撰《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独树一帜,认为属于古代西南的“夷系”。但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五、三星堆文化研究的主要争论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三星堆文化热”和由它所引发的系列反应正方兴未艾。也正是由于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才使巴蜀文化这个几十年来未曾得到学术界更多关注的研究领域最终登上了中外学术界的大雅之堂。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这里仅就笔者阅读与研究所及,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主要分歧从10个方面略加述评。
1.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及概念的演变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后,直到建国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此次发掘报告刊布于《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根据这次发掘以及历年所获资料,发掘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分为三期(后据资料分为四期),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等条件,发掘者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尽管当时还没有预料到三星堆文化会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以致会由此改写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但作为一个科学命名,“三星堆文化”这个名称,从此便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行列之中,并日益取得中外学术界的公认。
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其中最具震憾力的发现是1986年夏相继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掘并确认的三星堆古城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大批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引起了“三星堆文化”概念的发展演变。
从分期上看,先是把三星堆遗址第一至第四期文化通称为三星堆文化。90年代初,学术界注意到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与后三期文化在内涵和时代上的区别,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后三期为青铜时代的文化,从而提出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后三期为三星堆文化,而第一期为新石器文化。这一分期法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采纳。90年代中期,学术界又注意到三星堆文化第三期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共性,考虑到十二桥文化的兴起与分布情况,提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应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这一分期 序列逐步得到学术界较多学者的采纳。当前在三 星堆遗址文化分期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可 以表述为:

另有一些学者则坚持三星堆遗址第一至四期文化有着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它们同属于完整的三星堆文化的观点。
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2.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1995年宝墩文化发现后,在对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的文化属性问题上,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江章华、王毅、颜劲松、李明斌、张擎等撰文提出,从遗址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宝墩文化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宝墩文化在时代上既早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二期以后,下同),在文化内涵上又有不少因素被三星堆文化继承,因而宝墩文化应是三星堆文化的上源,即三星堆文化是直接从宝墩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而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应当归入宝墩文化范畴。陈显丹、刘家胜则不同意这种观点,撰文提出,不论从宝墩文化各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还是从宝墩文化房址、城垣构造和方向、墓葬特点看,宝墩文化与三星堆遗址的特点和文化内涵都是基本一致的,应属同一种文化,但宝墩文化并非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也不能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它只能归属于三星堆文化范畴之内,可以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宝墩类型”。
以上两种意见均认为三星堆一期与宝墩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范畴,分歧主要在这支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归属)问题和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从碳测年代看,三星堆遗址一期的最早年代数据是4740±150B.P.,宝墩遗址最早的年代数据是4500±150B.P.,在两个遗址内均未找到其最早上源。从文化因素看,尽管两者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但也并非不存在某些差异。看来要论定谁涵盖谁,还必须寻找新的材料来作结论。近年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遗址距今5000年前的宝墩文化遗存的发现,为解决宝墩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判明宝墩文化本身与三星堆一期的关系,还须更多的材料作为依据。
3.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来源和族属
有关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来源,绝大多数论著认为有相当的土著文化因素,也认为有某些外来文化因素。对于外来文化因素所占比重,未见发表统计资料予以说明,一般从文化形态上进行比较研究,定性研究占绝大多数,定量研究非常缺乏。
王仁湘、叶茂林认为,三星堆体小扁薄的磨制斧、锛、凿、锄等石器,和夹砂灰褐陶、平底器、绳纹等,其来源与四川盆地北缘的绵阳边堆山文化有关。徐学书认为,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南迁有关。张勋燎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柄勺与川东鄂西的史前文化有关,来源于溯江西上的一支古代巴地的文化。俞伟超、范勇认为三星堆文化与江汉地区西迁的三苗有关。孙华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某些因素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主体部分应来源于山东。罗开玉等认为,三星堆文化面貌显示出古代西南民族的文化特征,因此以土著成分为,外来因素为次。林向、段渝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经历过突破与变异,第一期以土著因素为主,第二期由于文化内涵的巨大变异而出现突破,但外来文化并不是整个地取代了原有文化,而是对原有文化有所承袭,有所融合。
至于族属,则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越人说、东夷说等不同看法。
4.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与年代
这个问题分歧较大,争议颇多。
陈德安、陈显丹首先提出,一、二号坑均为“祭祀坑”,是古蜀人在一次性大型祭祀活动后所遗留下来的,坑中瘗埋的器物均为祭器。林向认为,一、二号坑应为厌胜埋藏,是古代萨满式文化的产物。张明华认为,一、二号坑绝非祭祀坑,而是墓葬。孙华认为,一、二号坑既非祭祀坑和厌胜埋藏,更非墓葬,应为两位死去的古蜀国统治者生前所用器物的埋藏坑。徐朝龙认为,一、二号坑所埋器物的制器者、使用者,与埋藏者不同,应为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而将前朝用品加以毁坏掩埋的结果。李安民认为,一、二号坑为祭祀坑,但不是同一民族所为。郑光认为,一、二号坑反映了中原中央王朝或地方政府对当地巫风的打击和遏制。此外,尚有陪葬坑、窖藏以及其他一些意见,不再一一赘述。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问题,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一、二号坑分别约当殷墟一期和三、四期,宋治民认为应在西周,徐学书则认为应在春秋。
可以看出,对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在于方法和视角的不同,目前要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还有一定距离。至于性质,目前所见诸说虽然都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差不多是各执一端,诸说均不能圆满解释一、二号坑的各种遗迹现象。看来要取得共识,必须首先针对各种遗迹现象作出细致分析,在此前提下再来分析其性质,以便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并且这种分析应该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和有价值的启示。
5.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文化意蕴
这个问题分歧较大,异论纷出,莫衷一是。
发掘者认为,青铜人头雕像胸部以下成倒三角形,应为杀殉奴隶替代品或象征。多数观点认为,“杀殉论”不能成立。青铜为古代贵重金属,是富于战略意义的物资,何以能用来代替杀殉奴隶作其“替身”?徐学书认为,青铜人面像为古蜀人祖先形象的塑造,具有祖先崇拜的意义。其中的大面像即双眼突出眼眶10多厘米的“纵目人”像,或认为是蜀先王蚕丛氏的偶像,龙晦认为是蜀王杜宇的偶像,陈德安认为大面像不是人面像而是“兽面具”。对于与真人大小近似的人头像,或认为是贡奉者形象,或认为是受祭者形象。
陈德安认为,青铜人面像不是古蜀人祖先崇拜的产物,而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其中的小型青铜人面具,即是图腾舞蹈用具。范小平认为,青铜“纵目人”大面像,突出双眼,其作法和含义与中原甲骨文中的“蜀”字突出双眼(“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的图腾崇拜。
关于青铜大立人雕像,也有不同看法。
沈仲常认为,青铜大立人是古蜀人的一代蜀王的形象,由于古代社会的政治君王同时又是宗教上的群巫之长,所以是蜀王兼巫师的形象。段渝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的形象。陈德安认为,青铜大立人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尸”字的字形,故应为“立尸”,称为立人像则不妥。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大立人绝非是中原文献中的“立尸”或“坐尸”,两者内涵截然不同,《礼记》等文献可以证实此点。整个青铜人物雕像群,反映了以古蜀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具有民族结构的象征意义和有中心、分层次的君统与神统的表现功能。
凡此种种,尚有其他看法,不一而足。
6.三星堆金杖、金面罩的文化意蕴
关于金杖,争议不是很多,但差异甚大。
一般认为,金杖是蜀王权杖。段渝进一步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政权)、神权(宗教特权)、财富垄断之权(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垄断权力)为一体的权力标志,象征着古蜀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杖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关于金面罩,对其文化意蕴较少争论,多认为与古蜀人的宗教习俗有关。陈显丹认为是古文献中“黄金四目”的方相氏,但有争议。
7.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文化意蕴
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但将青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分歧之中的一致。
陈显丹认为,三棵神树应分别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若木”和“扶桑”,是古蜀人在举行祭祀仪式时用于人、神上下天地的“交通工具”或祭祀器。
胡昌钰、蔡革否定青铜神树为建木。认为其构造形态极似《山海经》中的“若木”。另一种观点认为,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文献中的“桑林”一致,应为“社树”。
与此不同的观点则认为,神树并非“社树”,其文化内涵与中原的“桑林”不同,中原无以神树为天梯的文化传统,《山海经》中以神树为“通天之梯”者仅一见,即位于“都广之野”的“建木”。三星堆神树当为“建木”,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其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樊一认为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日本林巳奈夫则认为神树起源于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若木(即扶桑、若木)。
8.三星堆金杖、雕像的文化来源
金杖、雕像是三星堆出土金属制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是众所公认的。但对其文化因素的来源,却众说纷纭,差异甚大。
宋新潮认为,青铜雕像文化形式来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老牛坡、湖南出土的青铜面像或青铜礼器上的浮雕有一定关系。罗开玉认为,雕像、神树等与古代的西南民族传统有关,但青铜器的出现则与中原文化的传播有关。李绍明认为,金杖、雕像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从青铜人物的冠式、体质面部特征看,可分为二种,一种为华南濮越民族系,一种为西北氐羌系,扁宽鼻型来源于华南,直高鼻型来源于西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雕像无论在中原、长江流域还是古蜀地本身都没有发现其文化来源,应与对外来文化的采借有关。纵观世界古文明,西亚、近东是青铜雕像和权杖的渊薮,并有向南连续分布的历史。再联系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海洋生物青铜造像和象牙等文化遗物,判定金杖、雕像文化因素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采借的产物,反映了古蜀人的文化开放和走向世界意识。这种意见中,又有南来论、北来论的区别。
9.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体系
屈小强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了古蜀人的竹崇拜,表明了古蜀人以竹为图腾的情况。陈显丹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反映了古蜀人的自然崇拜,表明古蜀人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宗教形态。
范小平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表现了对“蜀”的图腾崇拜,即是作为祭祀客体的艺术形象图腾的崇拜,而不是祭祀客体本质本身的崇拜。巴家云认为,三星堆文化决不仅仅表现自然崇拜,更不是图腾崇拜,而主要反映了祖先崇拜,也有自然崇拜。段渝认为,三星堆宗教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自然崇拜,又有祖先崇拜,还有至上神信仰等多种崇拜形式,表现出一个神权政治中心的多层次结构和网络体系,是一个神秘王国。黄剑华认为,三星堆文物揭示了古蜀昌盛的太阳崇拜。谭继和认为三星堆的性质是神礻某文化,是祭先祖与先妣共存的文化,祭祀坑出土的神像应为在神之祭。
10.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有多种层次的讨论,或从单项文化因素,或从多项文化因素,或从整体内涵上去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比较的对象也不尽一致,有新石器文化,有夏文化、商文化,也有东夷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云南青铜文化等等。
就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而言,过去的认识由于建立在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多认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近年由于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学术界多在这种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古文化和古文明,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但具体观点,各派则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方面,以及在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夏、商文化有较大差别,有其自身的生长点。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这种观点,在学界和社会各界中愈益占有多数。
李学勤认为,史籍记载了黄帝与蜀山氏的关系,这在三星堆文化中有所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形制和玉器形制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有关,证明蜀国君主确与古史传说中的颛顼有关。李炳海认为,古蜀文化的发展早于中原,夏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古蜀文化。温少峰通过对史籍所记古史传说的研究,发现中原所传的黄帝,实与古蜀文化的“西山文化”有深刻联系。郑光认为三星堆文化应是中原为代表的华夏文化系统的一支或一个组成部分。
在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交往的途径问题上,学术界也有不尽一致的认识。李学勤认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地区的。林向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的碰撞地在陕南,与夏文化的碰撞地在川东鄂西长江沿岸。段渝认为汉中和长江三峡川东鄂西均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边际交流地带,汉中地区是三星堆文化的北部军事屏障和扩张前锋,川东鄂西则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和平交流的舞台。李民提出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以上十大论争外,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还涉及到更多的层面和方面,其中一枝独秀者不在少数,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予以列出。至于本文未列出的其他内容,则属挂一漏万,尚希雅谅。
仅就上面论列的十大问题来看,三星堆研究已是高潮迭出、新见迭出、争论迭出,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这无疑是由三星堆文明本身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就三星堆文明的影响、争论范围、研究者队伍、学科构成、学者层次来看,都远远超出了巴蜀本身,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全局意义将会日益突出。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六、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几大方向和课题
巴蜀文化博大精深,内涵宏富,目前所揭示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部分尚待发掘和探索,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总结当前的各项成果,展望未来,我们以为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在以下四大方向和若干课题上可望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文字、城市、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
城市的性质,固然不是由是否有围墙来决定,但三星堆城墙以内的范围达36平方公里,无论比中国北方农村围有围墙的村庄,还是比史前时代围有围墙的近东耶利哥村落,规模都绝然不同。量的变化反映了质的变化,何况三星堆古城中还体现了史前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王权运作机制,因此必为城市无疑。三星堆城市研究,不但是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对于确定古蜀文明的社会性质、政府组织、权力结构、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动力等等,都具有头等意义和重大价值。它的另一个前景,在于通过考古发现,确定各类遗迹的所在和相互关系,比如宫殿群、居室群等,确定其城市布局、规划,从而探知其完整面貌和文化形态。
目前已知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代,宝墩文化古城群的衰落和三星堆古蜀城市文明的兴起是什么关系,其转化过程和机制是什么,都必须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新发掘与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探明。因此,探索三星堆城市文明的起源,关键在于探讨它与宝墩文化之间的兴替。
青铜文化方面,除了进一步研究古蜀青铜文化的起源、演变,进一步考察各类青铜制品文化因素的渊源而外,在科技史、冶金史方面,在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布局、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及其社会机制等方面,都有待深入开拓。
具体而言,对于青铜雕像、金杖、金面罩的文化渊源问题,对于蜀式三角形援无胡青铜戈的起源问题,对于柳叶形青铜短剑的起源、分布和传播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深入解决,并与中原等地考古资料作细致的比较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冶金术、科技史方面,通过自然科学实验,将进一步摸清三星堆青铜技术的特点、合金特点,以及青铜矿产资源来源问题。综合研究则将解决古蜀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程度,生产组织管理所反映的社会机制和王权集中程度等问题,以及对资源的控制或贸易等获取方式问题,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对古蜀文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所发现的刻划文字问题,目前因资料不集中,也因数量较少,故研究成果不多,今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会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为巴蜀文字的起源和巴蜀文明的形成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应大力加强,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以上诸方面研究的综合成果,必将对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文化结构、文化模式与类型,以及文化功能体系等,取得新的认识,获得重大突破,必将对中国文明研究做出新贡献。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做出贡献。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关系的研究,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当前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基础上,已初步建立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相应网络。然而这个序列和网络,与中原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实质怎样,均须进一步探索。与中国古史传说相联系,当前已从过去的疑古转变为探索古蜀文化与炎黄文化的关系阶段,今后必须深化认识,首先从考古学上建立可靠的认识基础,然后具体分析来龙去脉和发展演变诸关系,从而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增添新的内容,做出新的发展。
古蜀文明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重在长江三峡鄂西地区、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古代文化。当前学术界已在多方面开展了工作,还须通过对考古资料的仔细梳理,探明其间文化交流传播的基本轨迹,并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阐明古蜀文明在西南地区深刻而持久的历史影响。
古蜀文明与中原和周边文明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互动、双向以至多向的文化接触和交流问题,其中既有文化中心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有边际文化交流、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由边际向中心逐步渗透、延伸等交流形式,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其速率或快或慢,其程度或深或浅,其影响或大或小,其作用或显或隐,既具发展不平衡性,又具连续性、间断性,其过程、途径、方式极其错综复杂,绝不是单向、单纯或单一的,需要细致地进行艰苦的工作才能明察。
这项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入认识文化传播、文化变迁与文化演进及其动力法则的深层关系,至为重要。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必将对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并提供具体实例和理论模式。而且,从另一个宏观角度看,还将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得出意想不到的新成果,在此方面填补空白,开风气之先。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
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阐明了巴蜀文化对东南亚大陆文化的持久深刻影响。当前初步取得的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开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领域,而且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重大的研究价值。
由此展开的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不但将对巴蜀文化与中国西南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提供崭新认识,而且将对古代亚洲的国际文化交流纽带的研究做出新论断,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认识中国与世界,以至人类文化的交流、发展和人类文化的空间传播能力,和文化交流、传播方式、途径的复杂性,并认识人类文化传播与政体、国界、民族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关系和实质,从而对中国、亚洲以至世界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古代亚洲国际文化纽带中,巴蜀起到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充分研究,将揭示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联系途径和方式,巴蜀文化面对南、北两种文化所取态度和发生作用等问题,还预示着南、北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及交通诸问题提出新的课题和认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均属填补空白而富于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4.封闭与开放
三星堆文明研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系列研究成果足以揭示,身居内陆盆地的三星堆文明绝非封闭型文明,它不但与中原的文明和中国其他区域文明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且还发展了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的关系,证明它是一支勇于迎接世界文化浪潮冲击的开放型的文明。
三星堆文明开放性的揭示和继续深入研究,将给今天的四川内陆盆地和中国其他类似区域的改革开放提供古鉴,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思,有许多事情可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进展。比如,巴蜀人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实现同外域文化的远程交流的。又如,三星堆文明尽管吸收采借了若干外来文化因素,却并未改变其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又为什么?值得深思。
以上论列的各点,仅仅是就未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中的荦荦大者而言,绝不是全面列举,也不可能全面列举。全面的研究,需要学术理论界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此外,在相当多的具体问题上,巴蜀文化也值得进一步细致研究,有些问题还必须反复研究,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解剖分析。我们相信,未来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必将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 0001
- 0000
- 0000
- 0000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