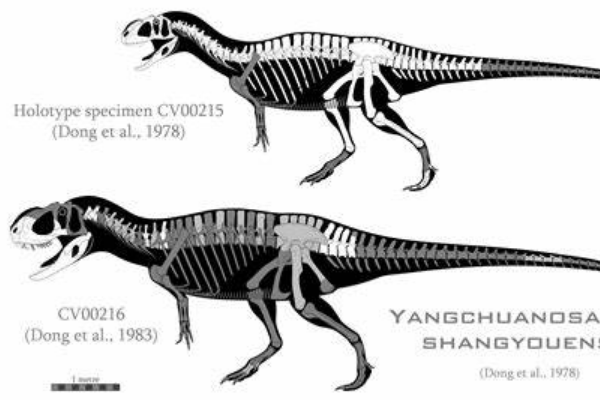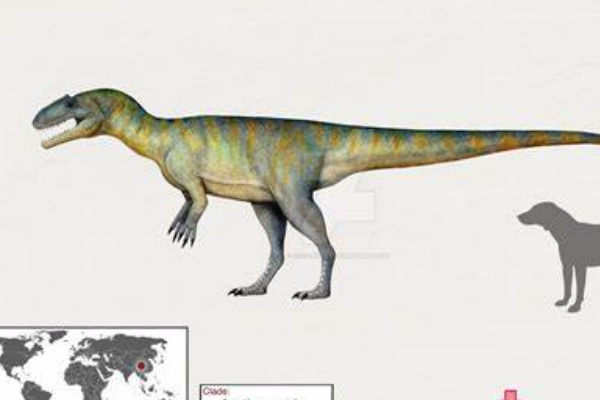施劲松: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
一 前言
成都平原西起都江堰市以西的邛崃山,东到金堂附近的龙泉山,北抵茂县的九顶山,南至新津县的熊坡山。这一面积不大的区域从史前至今一直是四川盆地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先秦时期,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文化自成系统,宝墩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城址群、三星堆和金沙等青铜时代的中心遗址、东周时期的大型墓葬等都集中于此。
本文以成都平原及邻近地区的先秦时期墓葬为考察对象,即因为该区域的先秦墓葬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尤其是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存主要即为墓葬,各时期的墓葬反映了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文化和社会的特征。时代限于先秦,是因为从距今约4000多年到秦统一,这个区域的墓葬地域特色鲜明,公元前316年蜀虽为秦所灭,但成都平原的葬俗未立即改变,区域性的文化和社会经过渐变,于秦汉王朝建立后才基本融入到统一的王朝中。
学术界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或是专论重要墓葬,或是就墓葬的时代、分期、类型、文化面貌等进行综合研究。也有研究由一个时段或特定的墓葬去探讨文化与社会。本文的重点有所不同,即试图由墓葬对先秦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特征、演进与变革进行长时段考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于讨论墓葬时代、类型等仅限于墓葬本身的问题,由墓葬探讨文化和社会,相关认识显然更容易受新发现的冲击。因此,本文的认识只是立足于现有材料从而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需由今后的新材料来检验、补充和修正。
二 宝墩文化墓葬
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约5100~4100年的什邡桂圆桥,发掘了2座墓葬,但未具体报道。
按成都平原的文化发展序列,桂圆桥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距今4600~4000年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墓葬首先出自宝墩文化的城址中。
发现墓葬最多的是大邑高山古城,2014~2016年发掘95座墓,被认为是成都平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墓地。据悉3座墓有随葬品,可见拔牙习俗。具体报道的6座墓均为竖穴土坑墓,1座墓为屈肢葬,时代或略早于宝墩文化。在新津宝墩城,1996年在城内Ⅲ区发掘5座,2013年在田角林地点发掘9座,其他地点也零散分布墓葬。1997~1998年在郫县古城发掘1座墓。1999年在温江鱼凫古城发掘4座,应为墓地的一部分。以上墓葬均无葬具和随葬品。
除上述城址外,成都是墓葬出土较多的区域。成规模的墓地见于1998年发掘的南郊十街坊遗址,19座墓中有17座由北向南呈三排分布,人骨仰身直肢,头向西北。有的墓随葬骨镯、管、片状饰品、圆形器、锥形器等,一座墓随葬1~2件,最多者14件。1999年在西郊化成村遗址发掘16座墓,有的墓带二层台,所知墓例中人骨头向西南,仰身直肢或屈肢,仅1座墓随葬1件石凿。2002年在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10座墓,多为东南向,葬式明确者均为仰身直肢葬,只在填土中出土2件玉石锛。在高新西区,2003年在“格威药业一期”地点发掘3座,在“航空港古遗址”发掘3座,2007~2008年又发现5座墓。这些墓葬式明确者均为仰身直肢,仅有1墓出土1件陶尊。
这一时期的墓葬还见于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新都斑竹园镇忠义、褚家村、陈家碾,郫县三观村、曹家祠等。一地少则1墓、多则5墓,墓向不一,均无随葬品。
宝墩文化时期的墓葬不多,以高山古城墓地规模最大,其他墓葬分布零散。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墓向不一,无葬具,多为仰身直肢葬,有少数屈肢葬。成都十街坊墓地随葬较多的小件骨器,可能是饰品,不体现财富或墓主人地位。其他绝大多数墓葬无随葬品,只极个别墓随葬1件石器或陶器。宝墩文化墓葬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无等级区别,表明尚未出现阶层分化,或者没有厚葬习俗。
成都平原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还有城址,已发现的新津宝墩城、大邑高山城与盐店城、都江堰芒城、崇州紫竹城与双河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均修筑在平原冲击扇河流间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城墙顺应河流与台地走向。城址面积多为10~30万平方米,宝墩城为60万平方米。靠近平原边缘近山地带的芒城、紫竹城和双河城有两重城墙。城墙正中不见明显的城门缺口,保存较为完整的郫县古城只在东南墙的北部有一个缺口。墙垣堆筑,经水平和斜面拍打,内外均有坡度。城内文化层堆积较薄,除郫县古城和宝墩城有大型建筑外,其他城遗存较少。城址的年代跨度不长,宝墩、鱼凫等城址废弃后直到汉代才又有人活动。虽然城址的规模较大,筑城也需要组织管理与大量劳力等,但从城址中看不到战争或社会分化的迹象,因此它们不应是暴力冲突或社会复杂化的产物。根据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及上述城址的特点,很多学者认为筑城的目的可能是防洪,外城墙甚至可能是挡水或居住遗迹而非城墙。在成都平原还有同时期的不带城垣的遗址,并有比较丰富的内涵,如新近发掘的青白江三星村遗址。很可能人们只在需要或利于筑墙的聚居点修筑城墙作为防洪设施,城垣并不反映聚落的等级。
由墓葬结合城址材料,可以认为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较为一致,阶层分化不明显,社会结构简单、松散。
三 三星堆文化墓葬
宝墩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化,时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殷墟第二期,新的研究推定为距今4000~3100年。已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的墓葬非常有限。1963年在月亮湾发掘6座,较早的3座为少年和未成年人墓,无葬具与随葬品;较晚的3座随葬陶觚形器和圈足豆。1980~1981年在三星堆城址内发掘4座墓,均无葬具和随葬品。
在三星堆城址以西550米的仁胜村,过去曾发现玉石器和象牙。1998年在此发掘墓葬29座,除8座被破坏外,21座中有2座被遗址第一期的地层叠压,其他为近现代层叠压并打破生土。从地层关系以及墓葬的排列和出土遗物看,或为同一时期的墓葬。墓葬最特别之处在于墓坑和墓底经夯砸和拍打,填土夯实,无葬具,墓底有人骨朽痕和腐殖质痕迹,推测人骨经砸击。部分墓随葬陶豆、豆形器、尊形器、器盖,玉蜗旋状器、泡形器、璧形器、锥形器、凿、矛、斧、斧形器,以及黑曜石珠和石弹丸。这批墓葬出土了相对丰富的玉石器和陶器,显然不同于宝墩文化墓葬。但玉石器又与三星堆两个祭祀器物坑的出土物不同。数量较多的玉蜗旋状器,形状略似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斗笠状白陶器。玉锥形器顶端的小榫见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玉凿上,象牙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大量发现。仁胜村墓葬的时代或许为宝墩文化末期至三星堆文化早期。墓葬的奇特葬俗、不同于宝墩和三星堆文化的随葬品,似乎表明墓主人具有特殊的身份。
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三星堆城内的两个祭祀器物坑和城内西北青关山台地上的大型建筑,都显示出青铜文明在当时达到的高度。但目前发现或确认的三星堆文化墓葬却极有限,除了发现的墓葬确实较少,也不排除有些被划为十二桥文化的墓葬年代可能相当于这一时期。比如,2010年在新都朱王村发掘的4座墓,仰身直肢葬,无随葬品。该遗址全然不见十二桥文化的陶尖底器,小平底罐、敛口罐与十二桥文化的同类陶器也有差异,此类遗存在成都地区还存在多处。2008年在郫县广福村发掘5座墓,有1座墓出1件磨石。该遗址出土了较多三星堆文化陶器,但尖底器很少。又如成都金沙遗址的一些墓葬,年代推断到了距今3400年,这在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范围之内。
确定的三星堆文化墓葬虽然有限,但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当时的文化与社会。目前所见的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主要出自三星堆城内的两个器物坑。此外,城址内还发现过一些玉石器窖藏,在青关山大型建筑中也有玉石器和象牙。但青铜制品、金器和很多类别的玉器几乎不见于三星堆文化的其他遗址和墓葬。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遗物,主体是表现祭祀对象和祭祀场景,也有祭祀用器,它们在被毁坏和埋藏前可能置于宗庙与神庙,体现了王权与神权并存。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青铜器等贵重物品的特定功能,表明社会上层控制了资源、技术和产品,社会财富用于维护宗教信仰与王权,以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显然,两个器物坑中形体巨大、造型独特的青铜人像、面具、眼形器、神树、太阳形器和“神坛”等并非实用器,也不代表财富和个人等级,因而不会出现在墓葬中。这些器物表达的是权力和宗教信仰,而非等级观念和丧葬习俗;社会主要财富的占有者可能是统治集团集体而非个人,财富用于祭祀而非丧葬。因此,尽管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发现有限,但可以推断,在这个特别的文化和社会中不一定有如同其他文化或王朝的规模宏大的墓葬。即使今后发现此时期的大墓,至少可以断定其埋藏物也会有所不同。
虽然目前没有发现高等级墓葬,但其他考古材料表明成都平原此时已形成了复杂社会乃至早期国家。除了器物坑,三星堆城址的结构已更为复杂:四周有城墙,城内还有月亮湾城墙和仓包包城墙;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有现存面积16000平方米、高3米的人工夯筑的二级台地,台地上有2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发掘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在三星堆遗址西北的鸭子河南北两岸还发现17处呈线形分布的中小型聚落遗址,绝大多数与城址同时。
墓葬材料未能显示三星堆文化时期多层级的社会,但其他考古材料表明当时存在一个具有凝聚力、控制力并充满宗教色彩的统治集团。虽然缺失其他文明中常见的大型墓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成都平原已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一点也表明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
四 十二桥文化墓葬
十二桥文化承袭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墟第三期至春秋前期,或被推定为距今3100~2600年。十二桥文化内涵与三星堆文化相同,或许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阶段。此时成都平原的文化和政治中心迁移到了成都金沙。金沙发现了大量十二桥文化的墓葬,一些墓地规模很大,主要由南向北分布于祭祀区以西。
2001年在金沙最南部的“兰苑”地点发掘100余座墓,墓葬排列有序,少有叠压和打破关系。以西北-东南向为主,个别有生土二层台,以仰身直肢葬居多,有少量二次葬。未见葬具,大多数墓无随葬品,所见随葬品以陶器居多,有少量铜器、玉器和石器,简报提到个别墓随葬金器。铜钺、戈、斧、斤均为小型器物,制作粗糙,锈蚀严重;玉锛、凿、璋形体较小但磨制精细。简报认为随葬品表明墓主人多为贫民,墓主人之间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层。
向北的“蜀风花园城二期”地点可能为墓地,2001年发掘了15座墓。葬式明确者均为仰身直肢葬,墓向均为西北-东南向,二次葬似较为流行。有4座墓出土陶器和石器。
2004年在“国际花园”地点发掘62座墓,其中48座叠压于该遗址的第5A层下,推断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有1座船棺墓,其他葬具不明。仅9座墓有陶器和石器。
2002~2003年在“万博”地点发掘60座墓,所举墓例多为东北-西南向,有一次葬和二次葬,3座墓底有木痕。仅少数墓出土陶器,一墓多为1~2件,多者5件。
2002~2003年在“春雨花间”地点发掘17座墓,多为西北-东南向,少数为南北向。均为一次葬,除了2座俯身直肢葬,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5座有随葬品,每墓出1件陶纺轮,只有1座另出1件小平底陶罐。
2003~2004年在西部最北的金沙“阳光地带二期” 地点发掘约290座墓,其中约有21座船棺墓。墓葬多为西北-东南向。土坑墓多为仰身直肢葬,有少量屈肢葬和二次葬,只1座墓出土小件青铜器,其他墓有陶器和石器。船棺墓有6座为双棺或三棺合葬,仅1座墓随葬陶器,疑似船棺墓多随葬磨石。该地点的大多数墓葬无随葬品。
在金沙遗址的东北部,2008年在“星河路”地点发掘48座墓,其中24座叠压在遗址第5层下而属于这个时期。18座为西北-东南向,6座为东北-西南向。均无葬具,仰身直肢葬,3座墓出土1~2件陶器。
在金沙东部的黄忠村遗址,1999年发掘13座墓。无葬具,有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成人墓内多出兽骨,仅1座墓出铜柳叶形剑。2001~2002年在黄忠村四组又发现1座墓。
成都市区其他区域发现墓葬不多,见于岷江小区,无随葬品。2004~2005年在金沙西北的金牛区禾家村发掘6座墓,仰身直肢葬,仅个别墓随葬陶器、玉石条和卵石。
成都市区以外以郫县发现墓葬较多,如清江村、天台村、三观村、青杠村等。彭州天彭周家院子,新都区正因小区、褚家村,温江等也有发现。这些墓中仅个别墓出土1件或少量陶器、石子等。2007年在郫县三道堰镇宋家河坝、2011年在新都同盟村发现的1座合葬墓有多件陶器和玉石条。2009年在郫县波罗村发掘26座墓,其中1座也随葬多件玉石条和1件陶纺轮。新繁水观音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5座早期墓出土少许陶器,或属此时期。
十二桥文化时期多成片墓地,墓地内墓葬分布较为整齐。墓坑方向多为西北-东南向,或东北-西南向,同一方向的墓头向又不一致。有少量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个别墓地出现了船棺墓和合葬。船棺墓的特点在于很少随葬陶器而多随葬磨石,其他方面与土坑墓无明显区别。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但出土随葬品的墓葬增多。随葬品并不丰富,每墓通常只一两件,陶器有高领罐、小平底罐、圈足罐、尖底罐、尖底盏、尖底杯、壶、器盖、纺轮,极少数墓有小件铜器和玉器,随葬玉石条、磨石、纺轮的现象非常突出。三星堆仁胜村墓葬、三星堆器物坑多见玉锥、凿等条状器,金沙祭祀区还有磨石、卵石等,十二桥文化墓葬随葬玉石条和磨石不知在观念上与此有无关联。
十二桥文化的墓葬总体上延续了此前的传统,最鲜明的特点是仍然没有大型墓葬。墓葬随葬品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遗物完全不同,后者保持了与三星堆器物坑相同的器类。贵重物品仍是祭祀器物,在特定的场所用于具体的祭祀活动,并不作为随葬品埋葬。可见,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社会依然是王权与神权并在,早期国家的结构和统治方式一如三星堆文化时期。虽然存在社会等级,但在墓葬中没有明显体现。个别墓葬出土的小型铜器与金沙铜器普遍小型化、轻薄化的特点一致,或与当时铜料匮乏有关,或是保持了不以贵重物品随葬的传统。但墓葬中有少量青铜器,玉石璋、戈等也见于金沙遗址祭祀区,或许统治阶层对社会财富的控制较三星堆文化时期有所放松。
十二桥文化墓葬的主要变化是在金沙形成了大规模的墓地。尽管墓葬发现的绝对数量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在金沙一个遗址发现多个墓地,一处墓地内又有成片墓葬,这与此前的墓葬明显不同。相关的是,十二桥文化的遗址数量也超过前两个时期。由此可认为,成都平原这个时期的人口显著增加,人口密度也以金沙一带最高。此时的社会和平、稳定,墓葬中没有与战争或其他暴力行为相关的迹象,也几乎不见实用兵器。对金沙雍锦湾墓地380余座墓所出的363个人骨标本进行鉴定的结果显示,男女死亡的高峰期都在中老年期,进入老年期的个体较多,表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男性死亡高峰未集中在青壮年期,推测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有关。尽管这只是对一个墓地的鉴定分析,但结论与由墓葬特点得出的认识一致。
五 春秋时期墓葬
十二桥文化以及金沙遗址的下限大致为西周末期或春秋前期。此后,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传统似乎中断了,主要表现为中心遗址的废弃,王权与神权象征物的消失,文化出现了新面貌。成都平原春秋时期的遗存主要是墓葬,它们具有十二桥文化墓葬的主要特点,但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中断后、战国时期文化和社会变革前的“过渡期”面貌。
春秋时期的墓葬大多仍然位于金沙遗址祭祀区以西。2002年在南部的“黄河” 地点发掘了170座墓,其中墓地东北部的16座墓有7座为船棺墓,9座葬具不明。墓葬大多为东北-西南向,仰身直肢。均有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20余件,有陶器,铜兵器、工具、饰件,玉坠、卵石、石条等。
2002年在“人防”地点发掘14座墓。除1墓为东西向外,其余均为东北-西南向,有三组合葬墓。1座墓底部内凹并有朱红色漆痕,或为船棺,出土1件绿松石和1块兽骨。其余墓无葬具,6座墓出青铜柳叶形剑、矛、明器兵器,陶罐和兽骨。
2004年在“国际花园”地点发掘的62座墓葬中有14座墓叠压于遗址第4层下而属于这个时期。墓葬多填青膏泥,葬具均为船棺,以一次葬为主,有少量二次葬,除了1座墓为俯身葬外均为仰身直肢葬,7座墓为双棺合葬。均为西北-东南向。13座墓出土随葬品,包括陶器、石器,铜戈、剑、兵器形饰件等。绝大多数墓出土磨石。
2008年在“星河路”地点发现24座墓叠压于第4层下,简报认为这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家族墓地。船棺墓和土坑墓共存,排列有序,17座墓为东北-西南向,7座为西北-东南向,仰身直肢葬。船棺墓4座,2座为合葬。船棺墓均随葬陶器、铜兵器、磨石和鹿骨。其中M2725中男女两人全身施朱砂,仅男性就随葬铜剑、戈、矛共46件,剑、戈的数量均为5的倍数。M2722也随葬铜剑、戈、矛各5件。土坑墓中有二次葬,11座墓出陶器,铜兵器、工具、牌饰、璧形饰,其中6座墓仅有1件陶器或1件磨石或美石。
可能属于这个时期的还有1981年在成都枣子巷发现的1座墓,残存人骨和朱砂,出土35件实用铜兵器和小型兵器。2008年在天府广场西侧发掘2座墓葬,推断为春秋早中期。2011年在新都同盟村发掘的M6出土19件小型铜饰件,具有这个时期墓葬的特点。水观音遗址的3座晚期墓出土陶罐、瓮和椭圆形石器,铜器既有戈、矛、钺、斧、削,又有戈形、长条形、三棱形等小型饰件。
这个阶段的墓葬明显延续了旧传统。墓葬仍多集中分布,以东北-西南向者为多,但仍有不少为西北-东南向。船棺墓增多,墓葬填青白膏泥。“国际花园”地点即为船棺墓地。墓葬等级不分明,船棺墓和土坑墓随葬品的多寡和器类仍无明显差别,即使是仅随葬磨石的独特现象,在不同的墓地也分别见于两类墓中。陶器以罐、尖底盏、瓮、釜、缸、盆、器盖和纺轮为主,石器仍然多磨石、卵石、石条,并有绿松石。小型铜器增多,包括比实用兵器约小一半的兵器、兵器形状的小件铜器,以及圆形、枝形、条形等的饰件。小型铜器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随葬品,有学者认为它们或是祭祀礼仪用器,或是随葬明器,反映了在宗教祭祀和丧葬活动中使用替代品的行为习惯和信仰观念。这一时期的墓葬仍然不见铜容器。
新的因素也很明显。墓葬大多有随葬品,“国际花园”和“黄河” 地点几乎每墓都有,且有的墓随葬品较多。出现了新型陶器,如“黄河”地点的陶三足盏,应是仿自春秋中晚期中原和楚文化区的铜盏。出现了成套的实用铜兵器和工具,它们替代了此前的玉石器,并具备了战国时期流行的主要器类和特征。以“黄河”地点的铜器为例,有剑、矛、戈、钺、斤、凿、刻刀等;剑有单剑和带鞘双剑,矛有长骹弓形耳和短骹半环形耳两类,戈有三角援戈和带胡戈;剑上多见镀痕,鞘上开始出现精美的卷云纹和云雷纹;兵器上兽面纹与“巴蜀符号”并存。在“星河路”地点,墓中铜兵器数量大增。
尽管墓葬出现了新特点,但总体看,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社会与十二桥时期相比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最具意义的变化出现在2000年发掘的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这座时代可能为春秋晚期的墓葬出土了17具独木葬具,推测原有葬具可能超过32具。棺木形制、大小不一,或葬人,或专门放置随葬品。墓坑周围的木质遗存显示出墓上可能还有祭祀类建筑。墓葬有较多随葬品,包括陶瓮、罐、釜、豆、尖底盏和器盖,铜矛、戈、钺、斤、削刀、印章、带钩和饰件,漆木家具、生活用器、乐器和兵器附件。尽管墓地曾遭破坏,但推测大墓中并未随葬青铜容器,因为至少有6具棺保存相对完好,葬人的8号棺和放置随葬品的9号棺未被盗扰。这座墓具有“过渡期”的特点,如合葬,船棺,无铜容器,兵器多为明器。但新因素也很鲜明,一是合葬规模和船棺的形体远大于此前的船棺墓;二是随葬品丰富,有大量漆器,30多件大型陶瓮中有粮食、果核和动物骨骸;三是外来文化因素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突然出现的大量漆器,漆器模仿了春秋至战国早期楚国、三晋、燕国、中山等地青铜器的纹饰。
商业街船棺墓的规模表明墓主人应为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家族。至此,成都平原始有大型墓葬。虽然与其他区域的墓葬相比,成都平原的大墓仍然不见大型的青铜器,却出现了大批漆器甚至大量食物。对动物骨骼的研究还揭示出船棺墓中有较多鹿肉,从最小个体数看至少有18个个体;鹿肉在成都平原的墓葬中并不常见,随葬鹿肉表明墓葬的等级很高。因此,墓葬等级的标识可能是上述随葬品和巨大葬具。墓上建筑则表明,早期针对王权和神权的祭祀活动已不见,或至少不再是全社会的重要行为,祭祀已针对死者从而变成丧葬活动的一部分。这表明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从墓葬中的外来因素看,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的中断、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剧变。
近年来在成都青白江双元村等地发现了大批船棺墓,有的墓时代可能相当于春秋时期,一些墓规格较高并有外来铜器。因此,新材料将进一步说明成都平原墓葬变化的时间节点与特点,十二桥文化之后的“过渡期”也可能会缩短或不再鲜明。
六 战国时期墓葬
成都平原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多、分布广、情况复杂,与此前的墓葬截然不同,反映出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首先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单座的大墓,或是规模大,或是葬具复杂,或是随葬品丰富,墓中出现铜容器,并有大量具域外风格的青铜器。这类突出于其他墓葬的大墓在商业街船棺墓之前尚不存在。1965年发掘的战国早期成都百花潭10号墓墓坑虽仅长3米,但有独木棺,出土的48件遗物除1件陶尖底盏外均为铜器,有鼎、壶、甑、鍪、尖底盒、勺,以及兵器和工具。铜壶镶嵌采桑、习射、宴饮、乐舞、狩猎和水陆攻战等图案,以戈、矛为主的兵器多达20余件,上有多种“巴蜀符号”。1976年在绵竹清道发现的独木棺墓出土铜容器、兵器和工具150余件。壶、罍等形体高大,盖豆、方壶镶嵌写实的动物纹,鼎、敦、圆壶有蟠虺纹、窃曲纹,尖底盒上有线刻纹,兵器多达七、八十件。1980年发现的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有斜坡墓道,墓坑长10.45、宽9.2米,木枋叠砌的巨大椁室分隔为三部分,再分为棺室和八个边箱,正中棺室内有独木棺,椁外填青膏泥。墓葬虽被破坏,头箱和边箱仍出土铜兵器、工具、印章等杂器,以及陶器、漆器、兽骨等。椁室中部腰坑内出铜容器、乐器、兵器188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前所末见,每类器物为2件、5件或5的倍数,极有特色。1955年发掘的成都羊子山172号墓早不过战国晚期,有木棺和椁,也出土很多铜容器、兵器、车马器、杂器和铁器。
其次,发现多处大规模的墓地。1988~2002年发掘的什邡城关墓地有船棺墓、土坑墓、木板墓和木椁墓,船棺墓中又有合葬墓,时代从春秋末期到西汉。2011~2012年在德阳罗江周家坝发掘了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的墓葬83座,其中船棺墓70座,多为两棺、三棺或多棺并列,棺木或形体巨大而形似木船,或较小而仅有船棺形制。出土遗物以陶器、青铜器为主。2015~2016年在成都青羊区清江东路张家墩发掘了战国秦汉墓195座,葬具有船棺、木棺、木椁,出土遗物多为陶器,也有青铜容器、兵器和饰件。
战国时期的墓葬有船棺或独木棺墓、土坑墓、木椁墓、木板墓。从什邡城关墓地看,船棺墓和狭长形、长方形土坑墓在整个战国时期都存在,随葬品无明显差别。同一墓地中不同的墓葬类型似乎不反映时代和贫富差别,这与早期墓葬相同。但在船棺墓中,形体巨大的船棺比制作简单、轻薄的船棺出土更多数量和种类的青铜器。
再换个角度看,成都平原的高规格墓葬都是船棺或独木棺,如商业街墓、百花潭10号墓、绵竹清道墓和新都大墓。但也有不少船棺墓出土遗物甚少,如20世纪80年代在大邑五龙发现的1坑3棺的船棺墓等。2014年在三星堆青关山发现了3座战国中期的船棺墓,除了3件铜兵器和工具,只出土了少量陶器。船棺显然并不体现墓葬等级。成都平原最早的船棺墓,如金沙“阳光地带”船棺墓,并无外来文化因素。商业街墓和新都大墓等也被认为是当地统治阶层的墓葬,如此,船棺葬可能是当地族群的葬俗。船棺葬与土坑墓的墓主可能族属不同,不同的族群应在成都平原长期共存。至于新都大墓的木椁,以及什邡城关墓地等战国晚期的木椁墓,应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出现的。船棺葬标识的可能是族属而非社会等级,墓葬等级由随葬品来体现。成都平原战国墓中的陶器多为釜、罐、豆,差别不大,青铜器却明显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釜、甑、鍪等容器,戈、矛、钺、剑等兵器,斧、刀、凿等工具,印章等杂器。容器形制简单,大多没有纹饰,兵器和印章上多有“巴蜀符号”。这类铜器很普遍,出青铜器的墓葬基本上都有,也见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四川其他地区,但多数器物在四川之外少有发现,因而应是四川当地的器物。
第二类为鼎、甗、敦、豆、壶、簠、缶、罍、鉴、钟等。形制复杂,纹饰多样,有的甚为精美。这类铜器的器形、纹饰,包括镶嵌和线刻工艺等,显然来源于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
据已发表资料,这类域外风格的铜器较早集中出现于2003年发掘的成都文庙西街M1。该墓出土壶、簠、敦、盘、釜、勺、匕等17件铜器,除釜和尖底盒外都具春秋战国时期楚式铜器的风格,蟠螭纹壶和簠、勾云纹器座也不见于成都平原的其他墓葬。与M1相距12米的M2出土48件陶器和10件铜釜、鍪、甑、兵器和工具,两墓完全不同。M1的墓主人或是外来移民,M1集中出土高规格的域外风格铜器而无船棺,也说明船棺葬是本土葬俗。
域外风格的铜器多出自高等级墓葬,如百花潭10号墓、绵竹船棺墓、新都大墓。还有很多同时出土两类铜器的墓葬,其等级可能也高于仅出当地铜器的墓葬。如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和金沙巷墓葬出土了多件鼎、罍、敦、豆等,饰涡纹、云雷纹、蟠虺纹、窃曲纹、蝉纹、夔凤纹等。白果林小区船棺墓出土的1件铜壶有内容丰富的狩猎纹、凤鸟纹等。凉水井街、西郊石人小区与水利设计院、中医学院、青羊宫等地的墓葬一般仅有1件域外风格的铜器,且多为素面。成都南郊和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出土的铜器也应出自墓葬。以上墓葬出土的铜器中鼎、敦、壶较多,也有罍、盆、盘、豆、勺、匕、磬。个别墓可见葬具痕,并保留了用朱砂的传统。2006年在郫县飞龙村发掘的3座船棺墓、1座土坑墓和1座木板墓呈东北-西南向排列,随葬两类铜器、铜钱和铁器,推断其时代为战国末期至秦。
另一部分墓葬只出少量的当地铜器,除前文提及的文庙西街M2、大邑五龙和三星堆青关山墓葬外,还见于成都金鱼村、罗家碾、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成都西南郊、京川饭店、蒲江、彭县等,时代以战国中期和晚期为多。一些墓葬也有船棺,有双棺或三棺合葬,还有的墓残存木板。陶器多罐、豆,铜容器很少或不见,更多的是铜兵器和工具。战国晚期的这类墓葬,如成都金牛区、光荣小区、天迴山、青龙乡、龙泉驿、郫县、蒲江等地的墓葬,开始出现木棺椁,随葬陶釜形鼎、铜钱和铁器,部分墓的时代应是秦灭蜀之后。
随葬陶器也出现了等级差别。1995年在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1座墓,随葬品除了两类铜器17件,还有陶器73件,其中高、矮圈足的两种豆64件。文庙西街M2出土的陶尖底盏、圈足豆等均有10余件,形制基本无差别。随葬多件(套)形制相同的陶器,应具标示等级的意义。
总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现了巨大变化。各时段都存在高规格的墓葬,等级差异明显;大型墓地发现多且内涵丰富;墓内出现了包括青铜容器的丰富的随葬品;青铜器按文化面貌分为两大类,不同的类别、器形和数量体现出不同的墓葬等级。仅此而言,这种迥异于此前的、新的墓葬和等级制度,已与中原文化趋同。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开始,青铜容器成为个人拥有、标识墓主人地位的物品。成都平原青铜时代铜器的功能至此彻底改变。墓葬中青铜兵器大量涌现,表明战争和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环境已不再似早期那样和平安定。有学者指出此时军权代替了早期的神权。
七 墓葬、文化与社会的变迁
据现有资料,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就其自身特点而言可以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与十二桥文化、春秋、战国四个阶段。
宝墩文化墓葬的突出特点是大规模的墓地不多,墓葬很少有随葬品。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墓葬仍少随葬品,似无厚葬习俗,少见葬具,在墓向、葬式等方面没有形成明确的葬制。未发现大墓,青铜器、金器、象牙等社会财富不用于随葬。但十二桥文化时期形成了大规模的墓地,船棺出现后逐渐增多,随即有了一坑多棺的合葬。墓葬中有少量成组的玉石工具和铜器,随葬玉石条、磨石、卵石和陶纺轮的特点非常鲜明。
作为过渡期的春秋时期,土坑墓和船棺墓共存,墓葬普遍有随葬品,但数量不多,保持了随葬磨石、纺轮的特点,小型铜器独具特色,但也出现了后来在战国墓中流行的成套的铜兵器和工具。
至迟在春秋晚期墓葬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从规模和随葬品两方面衡量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墓葬的大墓,多船棺葬和合葬墓,葬具形体巨大,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丰富,铜容器成为随葬品,兵器盛行,墓葬中涌现出大量域外文化因素。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还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区域同时期墓葬的特点,如墓葬类别较多,船棺墓、土坑墓和木椁墓并存,有单人葬和合葬,个别墓葬有墓道。随葬铜器有本地铜器和域外风格铜器两类,每类都只有常用的器形而无明确、固定的组合。在大规模的墓地中通常不见大墓,已发现的大墓似乎都单独分布而不属于某个墓地。以上种种,表明墓主的族属、文化背景等较为复杂;墓葬虽有等级差别,但又未形成严格、规范的等级制。
成都平原的墓葬可以反映各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探讨当时的文化与社会,亦可帮助我们反观各时期墓葬的特点。
宝墩文化时期的墓葬和城址等显示出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一致,社会形态简单,似乎尚未出现阶层分化,人们面临的威胁更可能是洪水一类的自然灾害。
三星堆文化时期,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青铜文明的出现,应与域外文化的影响有关。当时出现了社会统治集团,并可能形成了早期国家。但如此巨变并未体现在墓葬中。在三星堆遗址,墓葬与祭祀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差异并不在于数量上的强烈反差,而在于器物坑中的遗物不会用于丧葬。据此推断神权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相比之下,个人财富、地位的标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丧葬活动就较为次要。只不过,这种情形并不见于与成都平原存在联系的其他文化。
十二桥文化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承袭了上一时期而无实质性变化。当时的社会发展平稳,人口大幅增长,聚落数量增加。成都金沙一带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与此同时,神权可能开始逐渐削弱,相比于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祭祀区的祭祀遗存规模小而且分散,与祭祀器物相同的少量玉器和石器出现在个别墓葬中。
进入春秋时期后,政治和宗教中心区的衰落很可能意味着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自三星堆文化以来的神权和王权的衰落,可能导致成都平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文化势力的“真空” 阶段,此时正值楚文化大肆扩张。或许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由长江中游西进,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又一次变革。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楚式和中原式的青铜器,战国晚期还有秦式器物。域外风格的铜器有的可能由当地仿制,但一些工艺或装饰母题特殊的器物,如镶嵌水陆攻战纹的壶、蟠螭纹簠,以及青白江双元村新出的线刻纹匜和可能使用了失蜡法的盏等,应当直接从域外传入。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以及东周时期的楚蜀关系,学界早有讨论,相关认识也不断为成都平原的考古新发现充实。1999年以来发掘的川东宣汉罗家坝墓地所出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楚式青铜器与成都平原的青铜器相同,即为长江中游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节点。
传入成都平原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并不限于器物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观念。新的观念强化了墓葬及随葬品对于体现个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性,墓葬因此分级,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由祭祀用品转变为丧葬用品。而这些最终反映出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表现形式的变化。可以说,观念的传播和影响对此发挥了关键作用。器物、技术的传播需由人来完成,观念的传播更离不开人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成都平原就有移民墓,它们可能从战国早期到秦灭蜀后都存在。除前文提及的成都文庙西街M1外,有学者还辨别了四川地区存在的楚和秦移民的墓葬。
原有社会秩序的改变、外部势力的入侵、多民族的杂处,都会导致频繁的武力冲突。这个时期的墓葬中普遍出土兵器,规模较大的墓中兵器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出个人的实际需要。自春秋晚期以来的大墓各不相同,多种类型的墓葬并存,墓葬间虽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但并未形成规范的等级制,这些似乎暗示了当时的政权并非那样强大和统一,社会形态与其他东周列国存在差异。春秋晚期至秦汉的大型墓地是家族墓地还是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也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秦灭蜀后,秦文化对成都平原的影响超过了楚文化。秦汉王朝的建立将成都平原纳入帝国的范围,此后成都平原的墓葬虽保留区域特色,比如多崖墓,随葬独特的青铜钱树等,但文化和社会在总体上已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统一文化之中。
原文载《考古》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 0003
- 0000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