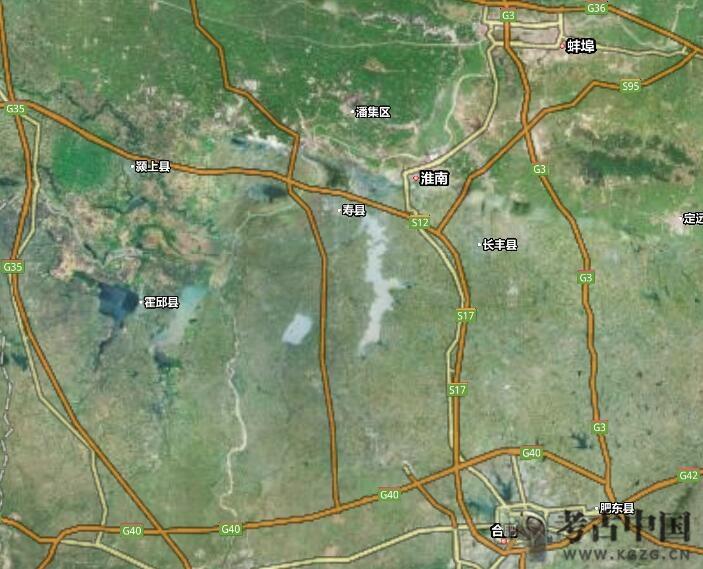柳扬:秦国文物的艺术异质媒介间的互动与革新
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乃是艺术中的某些强势的形式和风格,会超越具体的艺术种类,成为渗透于不同艺术媒介的普遍存在。有些尤其突出的形式和风格,甚至成为一种艺术精神,蔓延于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各种类型的艺术之中。秦人早期的艺术,为我们观察这种现象,提供了绝好的标本。
 柳扬 博士 亚洲艺术部主任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柳扬 博士 亚洲艺术部主任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异质媒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融,发生在秦人的青铜器、金银器、玉器及陶器等主要艺术门类之间。它们可以是器物造型的互相模仿、母题和纹饰运用上的趋同,以及整体的艺术风格上的向心力。有时我们还能见到,秦地流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能跨越地域,和其它方国以及不同文化和族群的艺术之间发生的更为复杂的相互交流、影响、融合、和革新。
一
讨论秦艺术异质媒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融的第一步,当然是寻找秦艺术异质媒介间,在较为接近的时间和空间里不同的艺术品之间的“事实联系”,通过事实联系再进而讨论它们之间在历史的和地域的交往中相互影响以及各自发展的轨迹或路径。
近年来出土的秦文物显示,秦艺术不同媒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融存在于同时期的艺术品中。同样的造型,流行于相近的地域和相同的时间,会被不同媒介的艺术品争相模仿。举例来说,春秋晚期在秦地流行的某种鸭首状带扣,会同时出现在金、铜和玉这几种不同介质的艺术品中。这类造型的带扣于金器中所见最多。1992年考古工作者于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晚期墓出土了两件金带扣,一件鸳鸯形(BYM2:24)(图1),另一件呈鸭形(BYM2:25)(图2)。
两件带扣都是末端开口,腹部中空,底部的凹槽内铸一圆柱用于固定皮带。最典型的是回首状,喙部扁长宽大,中部起脊,前端两侧成锐角凸出,最前部如三角状。秦人这种类型的金带扣,还可以举近年来流失海外、进入公私收藏的一些例子,比如瑞士人皮埃尔·乌尔泽(Pierre Uldry)收藏的一件鸳鸯形金带扣(高2.2 厘米,宽 1.9 厘米,厚 1.7 厘米,重 20 克)就非常接近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标本BYM2:24。笔者曾于另文讨论这件带扣与秦人的关系并推测它也出自秦人之手。
 图1
图1
 图2
图2
鸭首形金带扣,除益门村二号墓所出之外,位于凤翔的秦景公(前576 – 前537)墓(“秦公一号大墓”)也出土了两件(现分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考古研究院),标本000001,长 2.2 厘米; 宽 1.5 厘米(图3)。
 图3
图3
尽管头上无宝石装饰,但鸭喙上脊棱左右对称的S形阴线纹却与益门村二号墓所出一脉相承。凤翔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出土的一件鸭首形金带扣(长 2厘米,宽 2厘米),鸭首较为写实,身体却只是一长方体(图4)。尽管整体无任何装饰,但回首鸭形也与上述作品一致,而长方体无饰的主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简化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带扣鸭喙上脊棱左右也有对称的S形阴线纹。
 图4
图4
这种呈回首状的鸳鸯或鸭形金带扣,或者装饰繁复、或者素面无饰,在春秋晚期秦地是流行的样式。工匠们不仅以此作原型,制作出变化多样的金带扣,而且还将其造型运用到其它媒介的饰物上。
比如益门村二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玉带扣(M2:130,现藏宝鸡市考古所),长 2.8 厘米,宽2-2.2厘米,高1.25厘米(图5), 尽管通体被雕刻出浅浮雕勾云纹及变形兽面纹并间以小颗粒纹,以此呼应流行的玉器装饰风格(益门村二号春秋晚期墓所出玉器都带这种纹饰),而且扣首亦简化,缺少写实的头部,但是,从其回首的姿势以及扁平长方形的主体依然可以看出,其创意源自上述鸭首形和鸳鸯形金带扣。而另一件1977年出土于凤翔高庄春秋晚期十号秦墓的蟠虺纹鸭首形玉带钩(长3厘米、宽1.8厘米、高1.4厘米),雕出较为写实的头部,包括鸭喙上左右对称的S形阴线纹,就更接近它的金带扣原型了(图6)。
 图5
图5
 图6
图6
益门村二号春秋晚期墓还出土了7件金鸭首环形带扣(通高0.9厘米,长1.9厘米,环径1.3-1.5厘米, 宝鸡市考古所藏)(图7)。
 图7
图7
尽管它们的主体部分呈椭圆环形,但是都有鸭形首以及头两侧圆圈形双目,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扁长形喙上脊棱左右也有对称的阴线S纹,这种纹饰是秦人制作的鸭形和鸳鸯形金带扣上的标志性的设计。同墓出土的还有7件铜鸭首环形带扣,形制与上述金质带扣完全一致(图8)。
 图8
图8
出土于此墓的玉器中,有一件形制相近的鸭首形带扣(M2:129,长6厘米,高1.6厘米,环径2.6-3.5厘米))(图9),同样有扁长形喙,上有脊棱,前端两侧成锐角凸出,最前部如三角状,唯一不同处是圆环后部有一个圆管型附加物。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环玉带扣,鸟头朝向环心,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同一类的作品。
 图9
图9
近年来在秦人活动区域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同一种造型,在金器和铜器之间的通用最为常见。1984年考古工作者于凤翔马家庄雍城遗址出土了数件春秋晚期至战国的兽面金泡,标本000915,高2.5厘米、宽1.5厘米,厚0.32厘米(图10),兽面有突出的双眼,双角呈弧形,角尖凸起,鼻翼两侧有C形、尖部翘起的獠牙,下颚舌状突出,通体铸出装饰性的细珍珠纹。
相同造型的兽面金泡在秦地多处出土,比如考古工作者在凤翔西村战国早期的秦车马坑(S2)就出土了5件,标本80M162:04,高、宽2.7厘米,重8.2克。
 图10
图10
这种造型的兽面纹金饰,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流行甚广,有时作为单个作品出现,有的则变成更为复杂的一个造型的组成部分,比如1979年凤翔兰付村出土的两件春秋晚期金带扣(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凤翔县博物馆),标本0373, 长4.1 厘米,宽 3.4 厘米,重 77 克(图11),主体部分为长方体,其上饰缠绕蟠虺纹,底下的槽用以连接皮带,长方体一端接出一个兽面,它有卷角和颚下舌状突出,形制与上述雍城遗址所出一致。
瑞士藏家乌尔泽的藏品中有一件金铜圆环形络饰(图12),高 1.9 厘米,宽 4.2 厘米,环直径 3.2 厘米,重 62 克,造型是于几何纹错金铜圆环上,安置三个兽面纹金泡饰,兽面的造型非常接近上述马家庄与凤翔西村秦车马坑(S2)所出的金兽面泡。
 图11、图12
图11、图12
乌尔泽的这件金铜圆环形络饰,不仅兽面和上述金泡饰相似,而且圆环和三个兽面组合而成的整体的造型及作用也与凤翔西村战国早期车马坑(S1)所出的环形络饰相当。S1的那4件圆环形络饰出土于1979和1980年间,均是于圆环上铸三个向外伸出的兽首,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是青铜所铸。标本80M118:38,外径 3.9 厘米,内径 1.9 厘米(图13)。
由于它们全都出自马头两侧,所以我们得知它们是马络饰。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一件嵌铁圆环形嵌铜鎏金饰件,直径5.1厘米(图14),它曾被称作“龟形嵌铁鎏金饰件”, 但是将其与上述金铜圆环形络饰比较,显然它们都是造型和功能相同的马络饰,环上三个饰物并非龟形而是兽面。尽管这件络饰出自北方游牧民族青铜文化地域,但显然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很有可能出自秦人工匠之手。
 图13、图14
图13、图14
在另一件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S1)出土的龙形铜带扣(长5.8 厘米; 宽 4.8 厘米,陕西考古博物院藏)上,同样造型的兽面,也被结合进一个复杂的造型中,使其成为一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件带扣的主体部分是两条缠绕翻腾的龙,造型复杂,带扣圆环的另一端所附的兽面扣首的造型,却分明与上述金质泡饰相同(图15)。
 图15
图15
二
任何一个文化中的艺术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 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 必然与其先行的艺术传统以及同时期相关形形色色的艺术形式、风格和流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发展史显示,强有力的艺术风格和形式,会有持久的传统力量,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有时即便在历史发展阶段中有断裂,早前的传统也能重新流行。在秦人的艺术中,特定的艺术造型,有时能跨越时间和地域,在不同媒介的艺术创作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出土的秦人文物显示,常常早期的造型和风格,会在数百年后的异质媒介艺术品中,找到回响。
1991年考古工作者于陕西宝鸡陈仓魏家崖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金虎,长 4.5 厘米,高 2.2 厘米,厚 1.5 厘米(现藏陈仓区文管所)(图16)。
 图16
图16
金虎的背面凹陷无饰有一横梁,供皮条穿系之用。从正面看,虎呈卧姿,四肢成直角蜷曲,爪部握成拳头状,整个虎身以侧面展示,但虎头却转向正面视人,大耳上竖,双目圆睁,张嘴露出獠牙。西安市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据传是凤翔出土的金虎(图17),长4.8 厘米、高 2.3 厘米。
 图17
图17
这件金虎看起来象是上述魏家崖出土金虎的一个镜像:一个朝左,一个向右。除了尾巴上的纹饰有所区别,其余部分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认为西安市博物院这件金虎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在商周艺术中,虎是一种常见的形象,在青铜艺术中尤其如是。但是要断定某种文化中的虎的造型是上述两件金虎的原型,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除了相近的造型和纹饰,这种表现方式还须是当时流行的样式。可以肯定的是,金虎的形式源自秦人自己早期的青铜传统。秦人青铜器艺术是在模仿西周的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从春秋中期以来,秦人逐渐摆脱西周的常规,在造型和纹饰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1998年甘肃礼县圆顶山春秋中晚期秦贵族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显示,秦人热衷于在礼器上附设造型生动的动物装饰,而虎的形象即为其一。
 图18
图18
例如,M1出土了两件鸟纹方壶,标本98LDM1,高48.8厘米,壶盖颈上饰蟠虺纹,腹上却是蟠虺和凤纹的结合,壶身上下附设了许多个凸出的兽头,圈足前后侧各附两虎为支足。虎身侧卧,虎头却转向正面。
虎身上饰}}纹,四肢呈直角形,虎爪握成拳头状,尾下垂而末端上卷,柿叶状的大耳上竖,其中有与耳之外廓对应的轮廓线装饰,圆睁双眼,咧嘴露一排牙齿以及两侧弯曲的獠牙(图18)。 将铜壶上的虎和上述两件金虎的造型相比较,我们只能由衷地赞叹,几百年前铜铸的虎形象在金器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图19
图19
圆顶山出土的秦人早期铜器中,能见到许多类似造型的虎形象,因此让人相信,这种形式是当时流行的样式。比如它出现在M2出土了一件蟠虺纹方壶(图19)和一件蟠虺纹盨(图20)上,同样是作为铜礼器的支足,唯一不同的是这几只虎缺乏向两侧斜出的獠牙。
在蟠虺纹盨和蟠虺纹方壶上,还能见到另一种造型的“虎”,它们出现在蟠虺纹方壶的壶盖和壶颈上,蟠虺纹盨盖的斜坡处、盖沿和腹部。和上述作为铜器支脚的卧虎相比,这些动物都作行走状,身形修长,头呈长方形,阔嘴,两耳平行竖起前倾,四肢在胸腹的部分以漩涡纹表示,长尾下垂至末端卷起,整条尾巴的正中有一条装饰性的细线(图21)。
 图21
图21
在考古报告中,这些动物被称作是虎,但是很可能它们并非是虎而是狗,因为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狗(高1.9厘米、通长3.0厘米、宽1.1厘米)在形制上和它们几乎完全一致(图22)。 可以想见,当秦景公时期的宫廷匠人制作这些金狗形饰时,秦先人制作的铜礼器上的同类动物造型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粉本。
 图22
图22
三
和造型一样,秦人艺术中某些强势的纹饰,也会超越时间和地域,成为渗透于不同艺术媒介的普遍存在,被后来者模仿。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秦人塑造虎的形象时使用的一种 “{{ ” 或是“}}”和 “ ” 的纹饰。最早的例子来自两件据传是出自礼县大堡子山秦贵族墓地的金虎身上。
它们各自通长 41 厘米,高 16 厘米,身躯硕长,回首竖耳瞪眼,双腿卷曲做蹲踞状,全身以朱砂描绘出“}}”形平行纹表示虎毛(图23)。
 图23
图23
这两件金虎与一批金箔于90年代流落海外,经法国古董商之手,散入公私藏家,韩伟先生将其制作年代定为西周晚期,为秦仲(约前845年-约前822年)或庄公(约前821年-约前778年)棺上装饰之物。基于对大堡子山秦贵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进一步研究,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该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早期的秦襄公(约前777年-约766年)和文公(约前765年-约前716年)时期。 同样的纹饰,也被运用在上述出自圆顶山春秋中晚期M1和M2、作为青铜容器支足的虎身上。

 图24
图24
其它一些秦式青铜器上的虎形饰,也能见到这种纹饰。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蟠虺纹盖鼎(图24),平盖上围绕倒U形捉手,刻画了四圈蟠虺纹饰,近边缘处设对称分布的三个L形装饰物,每一个中都镂空作一回首张口的行虎,虎身上也同样用“{{”纹表现虎毛。此鼎的形制和鼎身纹饰接近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的春秋中晚期蟠虺纹盖鼎,它和台北故宫收藏的一件春秋中晚期蟠虺纹盖鼎(O3T-104)几乎没有二致,而那件鼎早已被学者认定出自春秋中晚期(约6世纪)的秦人之手。 由此可以推断,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这一件蟠虺纹盖鼎,也是秦人所制作,鼎盖L形装饰物中的虎身上表现虎毛的“{{ ”纹,与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所出金、铜器上纹饰的艺术传统一脉相承。
秦人自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受封为诸侯始立国,此后逐渐东扩,到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徙都于雍,直至灵公二年迁都泾阳,在雍城营建都城达255年之久。从6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雍城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建筑遗物,其中有一枚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瓦当,以浮雕刻画一位猎人手执长矛刺向老虎的情形(图25)。
 图25
图25
虎回首张口,躯体修长呈S形,身上以“ ”形纹表现虎毛,与上述金虎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这件瓦当上的纹饰并非孤例,同样是雍城遗址出土的所谓“虎袭雁纹瓦当” (现藏陕西考古博物院 000929)(图26)和“虎袭鹿纹半瓦当模” (现藏陕西考古博物院 T1102:190),虎的脖子上也刻画出表现虎毛的“ ” 纹。其它如雍城遗出土的陶如意上,也能见到这种纹饰。
 图26
图26
回到前面提到的宝鸡陈仓魏家崖出土的和西安市博物院收藏的两件战国时期的金虎,同样的纹饰,再次出现在虎身上。相隔数百年、不同媒介的艺术品展现秦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执著的偏爱,我们不得不惊叹传统的延续力量。
当然,在秦人的艺术中,特定的纹饰,在流传和不断被使用的过程中,其造型也并非一成不变。常常这些持久流行的设计方式和形式出现新的内容,特定的纹饰在不同媒介的艺术中被反复借用的过程也是再创作的过程。
举例来说,考古工作者1982年于凤翔马家庄秦人宗庙遗址出土了两件春秋晚期圆泡形金节约,标本K17:2,直径 2.2 厘米,宽 0.35 厘米,重10.8 克(图27),在繁复的流云纹中,蟠虺似隐似现。
 图27
图27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乃至秦代,圆泡形金节约在秦人的艺术里一直流行,凤翔县博物馆收藏有5件1985年于千河出土的战国蟠虺流云纹圆金泡(直径 5.1 厘米)(图28)。
 图28
图28
将它们与上述马家庄出土的春秋晚期圆泡形金节约相比,早期的蟠虺流云纹显得比较拘谨,而后出者就比较流畅、蟠虺之形也更具象。瑞士乌尔泽的藏品里也有一对夔龙流云纹圆泡形金节约(通高 2.7 厘米、直径 4.9 厘米)(图29),笔者曾于另文讨论着两件金节约并且认为它们也是战国时期秦人的作品。
 图29
图29
到了秦代,秦人这种圆泡形金节约上的蟠龙形象脱离了线性的表现方式,因而具有更强的浮雕和具象效果,显得更为灵动,最有代表性的实物是出自秦始皇陵铜车马上的几件金、银节约(通高 1.58 厘米、直径 2.44 厘米)(图30)。 秦人圆泡形金节约这样一个发展的序列或许可以显示,工匠们在继承和利用传统时,常常是带着再创作的态度,因而能推陈出新。
 图30
图30
四
异质媒介间的互动、影响,起主导作用的是哪一种媒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须将秦艺术置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去打量它。
春秋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的文化艺术的生成和发展,并不是纯粹地与地域传统有关系,而是融合了族群地域性(具有垂直的历史性的特性)与跨越诸侯国界(具有水平共时的特性)的元素,所有自成一体的艺术形态都情愿或不情愿地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以及早前传统的制约。
在种种重要因素中,周文化是持久的强势话语,影响着各个诸侯国艺术话语和艺术形态。当时不同族群和地区的艺术流行思潮所发生的关系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在周文化形形色色的组成部分中,青铜艺术扮演了一个极其璀璨的角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时期,中国青铜文化已经达到它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它综合了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于一体,不但被用来制作礼器,还被大量地用以生产兵器、工具,以及乐器和车马器。
 图31
图31
更重要的是,青铜器的发达是与古代社会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息息相关的,“藏礼于器”的观念使得那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让它们成为礼制的体现,甚至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毫无疑问,青铜器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门类,它所创造的强势形式和风格,会跨越形形色色的艺术门类, 成为渗透于不同艺术媒介的普遍存在。
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秦人的玉器作品。1976-1986年发掘的凤翔南指挥乡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两件春秋晚期玉龙纹宫灯形镂空佩(现分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考古研究院),标本002889直径4.9、厚0.3厘米,玉佩外形酷肖宫灯,两侧有镂刻成方向相反的条形,在其左右和下方有“山”、“ 八”和“L”字形的镂空,圆心的空洞处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对“L”形互相对应的齿(图31)。这种宫灯形的龙纹镂空佩的造型前所未见,绝无仅有,被公认是秦人在春秋晚期制作的最有特色的玉作品之一。
但是这个造型的原型,显然来自青铜器,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晚期。2003-2004年间,考古工作者于陕西扶风周原的庄李发掘了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铸铜陶范,所铸铜器包括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也有双龙形镂空环陶范 (图32) 。
 图32
图32
作坊使用启自西周早期, 沿用至晚期, 双龙形镂空环陶范的发现证明,这种形制的铜饰,最迟到西周晚期已在使用了。类似的双龙形镂空环似乎也流行于西周晚期中原其它地域,在虢国,数量较多的双龙形镂空环的出土说明,这种形制的铜饰在那里的使用尤其盛行。1990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西周晚期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出土了6件双龙纹铜环,发掘时它们被置放于内棺上,故被考古工作者认作是棺饰。标本M2001:541-1,直径6.1厘米,正面呈连体双龙相对盘曲,长舌相接,二龙有丫形角,各有一对獠牙向下向内弯曲(图33)。 上村岭其它西周晚期虢国墓也出土双龙纹铜环,比如M1715。 除外,还有4件收缴的、同样是从上村岭西周晚期虢国墓地所出双龙纹铜环,形制完全一致。
 图33
图33
在原西周的王畿及邻近区域,这种双龙纹铜环的使用,春秋时期仍颇为流行。考古工作者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贵族墓葬遗址属于春秋早期的M19出土了10件铜双龙镂空环,它们均贴附于外棺四周,因此也是棺饰无疑。在同样属于春秋早期的M27,这种环饰的作用显示得更清楚:10件铜双龙镂空环被贴附在外棺四周,两两对称,两侧各四件,两端各1件。 此外,同期的M586也出有多件,还有15件出土于M502,标本M502:75 ,长直径5.2厘米、短直径4厘米、厚0.15厘米(图34),它所展示的细长对称的双獠牙更贴近宫灯形镂空佩的造型。
 图34
图34
韩城梁带村芮国贵族墓葬遗址所出的另一类铜双龙镂空环,圆心空洞处出现的是单齿,它们显得较为规整而不张扬(如M26所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铜双龙镂空环的造型已经开始向其它媒介的领域扩张,双龙头尾相接成圈形并张扬露齿的形式已经成为金饰物模仿的对象。梁带村芮国贵族墓葬遗址同属于春秋早期的M27出土了13件金双龙形镂空环,由于它们皆发现于墓主人腰部,所以不可能是棺饰。发掘者根据其形制和纹饰将它们分为三型,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造型都是连体龙头尾相向成环形,单个獠牙在环中心伸出形成对称的布局(图35)。
如同它们的铜单齿双龙镂空环,这些金双龙形镂空环,有的单齿紧贴内环壁颇为收敛,有的虽然悬空伸出,但相比而言都较为短促,显示出独特的地域风格。


 图35
图35
以上的举证或许可以说明,秦人工匠制作这种宫灯形的镂空佩时的灵感来自当时仍占主导地位的青铜艺术。不过在这个很显然的例子上,继承过程中的改编也显而易见:为迎合玉佩这种作为私人饰物的材质的需要,工匠们将玉佩环的部分加大,以便让其承载当时强势流行的蟠虺纹饰。
西周青铜器传统影响秦人其它材质艺术品造型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流行于春秋晚期的兽面纹金泡。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秦地贵族流行车具上的金装饰件,金泡饰或金节约就是其中一种。
如前所举,圆泡饰通常为圆形弧起,作半球状, 有的素面,有的通体饰变形蟠虺纹或流云纹;方形泡饰则通常作兽面,两者背面附有横梁或鼻环。凤翔马家庄1号建筑址出土金制品29件,包括9枚圆泡、8枚方泡 (有的泡面饰有兽面纹);凤翔春秋晚期的秦公大墓也有兽面金泡出土。陕西宝鸡益门村属于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M2出圆泡56枚,方泡7枚。方泡皆为兽面,但有的嵌有料珠,有的则为素面。标本BYM2:29(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藏),长 3.9 厘米; 宽3.2 厘米; 厚 0.6 厘米(图36)。
 图36
图36
带绳纹眉毛的双目颇为写实,但整体却以几何线条刻画,鼻翼下两侧的獠牙也显得规整,颚下有蛇首状凸出。通体对称镶嵌八颗料珠,背后有一横梁以便将其固定于皮带之类的物体。
 图37
图37
检视流散海外的秦风格兽面纹金泡,可以提到瑞士乌尔泽所藏的一对例子(图37),它们高约3.9厘米, 宽4 厘米, 厚1 厘米, 重42克。已故苏黎世大学布林科教授和现在纽约巴德学院任教的路易教授曾将其年代定为西周,但是显然它们是秦人春秋中晚期的制品。尽管它们和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兽面金泡并不完全一致,但却与秦人同时期制作的兽面铜泡相同。
陇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批80-90年代陇县边家庄出土的春秋早中期的青铜兽面饰(图38),同样背后有横梁,兽角的造型可分成三类:直立,朝外弯成直角状,或以横梁连接双角。另外,它们有的下端有蛇头状凸出,有的则没有。
 图38
图38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显示,陇县一带是秦人东迁最早的落脚地之一。尽管这里是否就是《史记》说的襄公所徙之汧仍有待更多考古资料证明,但此地曾是秦人春秋早期的一个都邑却是事实。
边家庄墓葬的年代从春秋早期延续到春秋中期,但明显盛于早期。礼县大堡子山属于春秋早期的秦贵族墓地未见出土同类泡饰,圆顶山秦贵族墓地曾出土数件铜兽面泡饰,如标本98LDK1, 高3.7 厘米, 宽 3.4 厘米,角上有横梁连接,额下有蛇头状凸出物, 造型与边家庄所出同类兽面饰相似,不过该墓地属于春秋中晚期,年代比边家庄要晚或同时。这说明这类泡饰是秦人迁入原西周文化的地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
 图39、图40
图39、图40
形制相似的铜兽面饰至少在西周晚期即开始流行,1990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南三门峡市西周晚期虢国墓地M2001出土了39件兽面纹铜带饰,其中34件体形稍大,有的兽首双角间有横梁(标本M2001:289,长4.6厘米,中间宽4厘米,厚1.3厘米)(图39),有的则无(标本M2001:397,长4.7厘米,中间宽4.1厘米,厚1.5厘米)(图40)。
兽面都是正中有两个丫字形设计,上面的作为双角主体,下面的则形成鼻梁与双眉,两者中间左右各有一个作为角之一部分的C形,下部左右有獠牙。5件稍小的(长宽均为2厘米),除其中3件无獠牙而稍有特殊外,其余的造型类似尺寸较大的兽面带饰。 考古工作者还于西周晚期的M2011出土了9件兽面纹铜带饰,其中5件非常接近M2001所出(高约3.5,宽约3.2厘米)。
在被盗的同属西周晚期的M2118也发现了3件类似的兽面纹铜带饰。除外,还有收缴的零星的、同样是从三门峡市西周晚期虢国墓地所出兽面纹铜带饰。
 图41
图41
考古工作者还于M2001墓主人腰间出土了一组12件金腰带饰,包括3件兽面纹金带饰,形制与上述铜带饰相同(图41)。在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主腰间,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组15件金腰带饰,其中也有一件兽面饰,但形制与流行于虢国的稍稍有异。 不过这两个例子说明,铜兽面泡饰的造型已经开始被移植到更珍贵的媒介黄金上来了。
就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芮国是个极其流行使用兽面带饰的区域。2007年考古工作者于梁带村芮国墓地北区属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18件铜兽面带饰,其中9件有连接双角尖的横梁(标本M508:2,宽4.1、厚1.4、高4.6厘米),另外9件则无(标本M508:3,宽4.2、厚1.3、高4.5厘米)。
进入春秋时期,这种形制的兽面饰在芮国盛行不衰。梁带村属于春秋早期的芮公大墓M27出土91件铜兽面带饰,由于是与众多的衔镳、铃、节约、络饰等一起出土,所以它们作为马络带饰的用途无异议。 同是春秋早期的M28也出土了近70件兽面带饰,由于面貌多变,发掘者将其分成兽面和龙首两种。在梁带村芮国墓地所出数量众多的兽面带饰中,四件出自M27的金兽面饰因此弥足珍贵(图42)。
 图42
图42
长宽约2.2厘米,它们均出自墓主人胸腹之间,是与别的牌饰一道作为带饰成套使用。在总体轮廓上它们和同时期的铜兽面带饰相同,凸起的鼻翼与一件出自M586的铜兽面饰尤其接近(M586:67)(图43),唯一与铜兽面饰不同的新变是金兽面颚下出现了舌形凸出。
 图43
图43
从近年来出土的兽面饰来看,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青铜兽面饰在数量上的压倒性是西周青铜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有力证明。青铜兽面饰给予同样类型的金饰的影响,还可以从兽面饰这种器物本身在造型的进化和发展来说明。西周时期流行的铜兽面饰,颚下都没有蛇头形(或舌形)的凸出部分,在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和梁带村芮国墓地北区出土的铜兽面纹带饰中,只有少数下颚微突(如M2001:142/292/278及M508:3)。
春秋前期,秦地制作的兽面饰也常见下端无蛇头状凸出的,比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春秋前期秦墓出土的4件兽面饰。 进入春秋中晚期,这类兽面饰在秦地仍有制作,如边家庄出土所见,但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带蛇头状凸出的造型乃是更为流行的样式。
秦工匠显然对西周流行的样式进行了加工和革新,注入了新的元素,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兽面纹金饰(见图36),以及一些同时或稍晚的金、铜带扣,如凤翔兰付村出土的两件春秋晚期金带扣(见图11),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S1)出土的龙形铜带扣(见图15),以及凤翔马家庄雍城遗址及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S2)出土的战国兽面金泡(见图10),全都是这种造型。梁带村M27出土的4件金兽面饰下端有舌状凸出,异于所有已见诸报道的众多芮国铜兽面带饰。很可能,这种新的形式源自秦人的传统。
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是一个由多种考古学文化相互渗透、冲撞和融合的多文化的交汇区。在这个多文化交汇区里,各种文化因素的融合和发展往往会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新的文化区块,互相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文化正是这样一个由多种文化因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当时文化的多元以及强势文化的放送使得孤立发展的本土艺术和文化形态成为不可能,所有自成一体的艺术形态都情愿或不情愿地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而这不同地域、民族、国家、文化背景的艺术之间也常常发生极为复杂的相互交流、影响、融合、革新。有时我们还能见到,秦地流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跨越地域,和其它方国和民族的艺术发生更为复杂的相动和融合。
近年来学界讨论青铜器时,注意到所谓融合型,即某一器物的器形和纹饰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因素特征。这类青铜器是由特定的族群将自身的文化因素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融合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器物。在秦人制作的在器型、纹饰和风格等方面互相影响的铜器金银器中,我们也能观察到这种融合型作品。因此在讨论秦艺术异质媒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融时,我们还须注意到某类结合了中原文化、秦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艺术品。
 图44
图44
1982年从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K17)出土的春秋晚期金器中,有三件造型奇特的金异兽。 标本006909,长3.7、高2.5厘米(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一有蹄类动物,它扬蹄卷尾,首作大卷角兽面(图44)。
值得注意的是,金异兽的三肢作正常姿势,但前肢之一却向上扬起,作180度旋转。这种将下肢不自然扭转的动物造型,不但在秦艺术,而且在中原文化中也是全新的元素。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亚草原的艺术传统。
在西伯利亚斯基泰游牧民族创造的美术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动物造型,包括那些表现在黄金和青铜制品上的,甚至人体上的纹身,后者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出土于阿尔泰山北麓的帕兹雷克(Pazyryk)公元前5世纪二号古冢墓主人身上刻划的纹饰(图45)。
 图45
图45
表现在金牌饰上的例子很多,比如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伊赛克(Issyk)古冢(公元前4-3世纪)出土的两件(图46)。
以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K17)出土的金异兽来看,欧亚草原的这类表现方式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已传入秦地,而与秦接壤的北方游牧民族,则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图46
图46
一个重要的例证来自西安北郊的一座秦墓。1999-2000年间,考古工作者于这座编号为M34的墓葬中,出土了25件作为随葬品的铸铜陶模具,其中有5件为牌模:一件上的图案是少数民族人物,另四件则是形形色色的动物形象。
标本M34:13(高7、宽9.4、厚2.5厘米),以浮雕表现一个有蹄类动物,前肢呈奔跑状,后肢却180度向上翻转。异兽的头部有鹿角似的平行延伸物,五个分叉以鸟头结尾(图47)。
 图47
图47
拿这个异兽和帕兹雷克(Pazyryk)古冢的墓主人纹身上相应的造型作比较,显然它们一脉相承,不过陶模具的设计者将来自欧亚草原艺术的原型稍作变动以适应长方形构图的需要。
这种综合了多种动物和禽鸟元素而组合成的异兽是欧亚草原艺术中最典型的一个形象,它有着马的身躯和四蹄、鹰类禽鸟的头以及鹿的角,角的枝杈和尾巴又总是以鸟头结束。由于此怪兽的带喙的头及鹿角枝杈的鸟头都各自有耳朵,所以无疑它们都是格里芬(Griffin),源自西方神话传说中的狮身鹰首有翅膀之异兽,它法力无边,让人敬畏,象征勇气、勇敢,以及智慧。关于格里芬的传说及形象传播到了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区域,变得极其流行。
1957年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异兽(格里芬)证明(高11.5厘米,长11厘米)(图48),这种源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艺术的造型已传到了秦国的北方边地。
 图48
图48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宁夏和内蒙(尤其是鄂尔多斯)一带发现了许多金、铜牌饰,其造型显然源自欧亚草原传统,但往往经过改良。
鄂尔多斯青铜博物馆收藏的格里芬与狼或虎豹搏斗纹铜牌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图49),在这个设计中,格里芬的鹿角和鸟头被设计成置放于左上角,看起来如同伞盖一般的树丛,鸟头也变得图案化和不易辨识。
 图49
图49
纳林高兔村匈奴墓出土的金异兽具备了上述欧亚草原马鹿鸟混合异兽的典型特征,可是身上的纹饰却又接近中原青铜艺术中常见的云纹,让人想象它或许是汉人工匠的作品。尽管这种推测还需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但西安北郊M34所出铸铜陶模具上的马鹿鸟混合异兽(格里芬),却分明是秦人所制作。
M34是典型的秦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随葬品中有一枚铜印,上镌一阴文篆书“苍”,估计是墓主人的名字。随葬的陶器摆放在壁龛内,铜印、铜环、铜座漆器、铁刻刀等放在棺内墓主人的头前,而铸铜陶模具等器物则被置放于墓主人身体两侧及脚下。
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是一个铸铜工匠,后人在下葬时将代表他生前事业的铸铜陶模具等器物紧挨着他置放。而那些牌饰模上的浮雕设计证明,经这些陶模所铸出的金、铜牌饰,很有可能是为跟秦国紧邻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的。鄂尔多斯发现的一对鎏金青铜牌饰为这种推测提供了证明。这对牌饰长9.9厘米、宽7.3厘米,⁶⁸ 除了格里芬鹿角枝杈以及其上的鸟头稍多之外,它们和西安北郊M34所出陶牌模上的设计几乎完全一致(图50)。
 图50
图50
鎏金青铜牌饰上的图像可以让我们补充M34所出陶牌模上漫漶不清之处:尾巴末端分叉结束处是两个鸟头,而异兽头前方还有一个长喙的鸟头。
回到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K17)出土的金异兽上来,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秦艺术异质媒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融有时呈现复杂的情况。欧亚草原金、铜器饰的艺术造型和风格传播至与秦接壤的北方草原游牧人文化圈,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秦人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又让来自更遥远的北方的艺术形式找到了新的土壤,让这些表现形式在金、铜和陶等不同介质的艺术品的互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秦人工匠无论以何种取舍标准对其本身的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形制和纹饰的重新组合, 或者借鉴与融合来自其它媒介的表现形式,都体现了他们重新设计、构思器物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观。比如金异兽借用了下肢转体上扬的设计方式,兽首仍作当时在秦地及中原流行大卷角兽面,形制上非常接近上文讨论的下颚无蛇头或舌状突出的兽面造型。
象这一类的例子说明,由于特定文化传统某些本质的因素如同基因一样渗透于该文化的血液之中, 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只能在一定层面上发生, 而在某些范围内外来的影响却无法穿透, 这种情况给秦艺术异质媒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融带来了复杂性,也给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本文发表于《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03-523页。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