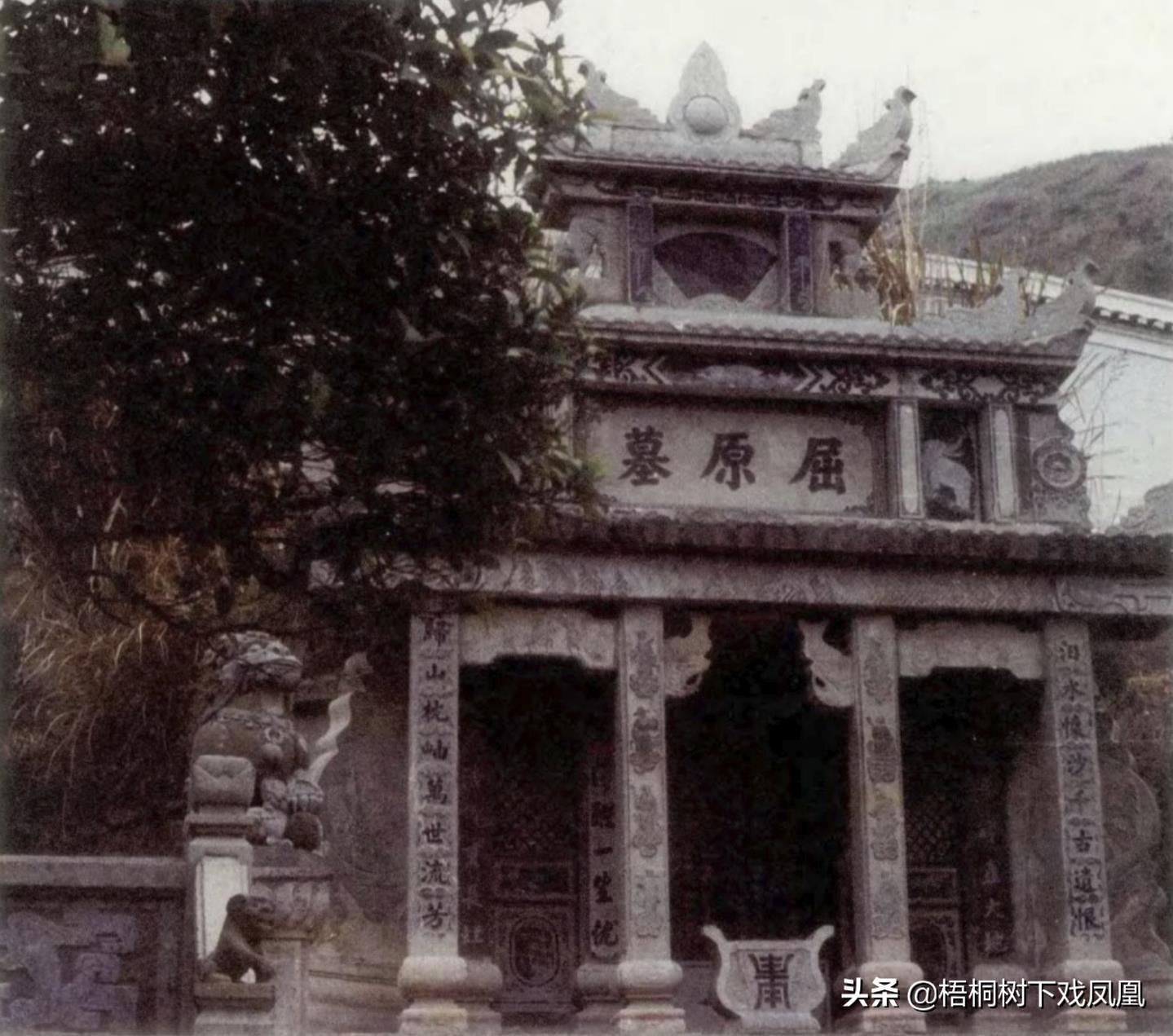韩茂莉:“中国”的含义及其空间变化
中国,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土主权国家的称呼,它所包括的政治理念与空间界域十分清楚,但这一称呼所具有的含义并非从来如此,而是经历过从标定地域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变化。
于省吾在题为《释中国》的文章中提到,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1963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为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铭文中出现“中国”一词,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字记载。<但这时“中国”并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所领有的空间,仅表明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唐兰释何尊铭文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迁都成周,并按照武王的礼,进行福祭。祭祀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戌周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向天下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呜呼,你们或者还是小子,没有知识,要看公氏的样子,有功劳于天,完成使命。’”


唐兰之外,张政烺、马成源等对何尊铭文“中国”之释,大体相同。当代学者释“中国”并非出于自己的创意,于省吾指出“中国”一词由“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命,故“中”的含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中”与“国”合为一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先秦文献中含有“中国”的记载,均表明了这番意思,只不过那时视为中央区域的,或为殷商乃至于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诗经·大雅·荡》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中“中国”指商都或商的基本控制区。《尚书·梓材》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的“中国”指文王、武王伐商及商属国所在的地区。武王克殷,以周代商,周人所在核心区域则被视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注疏》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处“中国”,指周人国都丰镐及毗邻地区。商人居东,周人居西,由西周进入东周,周人的政治中心也由位于丰镐的宗周移向位于洛邑的成周,伴随这一迁移,“中国”再次回到殷商时期的位置,即黄河中下游地带。入周以后,有关“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偏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即后世所称的中原地区,《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这些文献提到的“中国”均指中原地区。不仅如此,何尊铭文所及“中国”也应指中原,《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位于洛邑的成周是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营建的,故唐兰等均认为“余其宅兹中国”为中央之地即中原地区。
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凡被视作“中国”的区域有着与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范,正像唐人孔颖达所说的那样,“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礼仪、服章强调的都是文化,显然“中国”所在区域盛行华夏所代表的文化;反之,没有这样文化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前述《左传》鲁成公七年吴伐郯事件之后,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就是这样的事例,吴国先祖本为太伯、仲雍,不但不是外人,而且与周天子同为姬姓,但远在长江下游,全失华夏风范,竟被鲁人视作蛮夷。西周时期,人口不多,开发程度也不高,地区之间不仅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而且华夏之风也没有可能为普天下效仿,于是不仅吴、楚不在“中国”之列,位于今四川的蜀也是如此,故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称“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叟”是那个时代对蜀地民族的称呼,限于地理条件,叟人至春秋之时与中原地区仍来往不多。文化风范与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同处于农耕生活背景下的吴、楚、蜀尚不被视为“中国”,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带的非农耕民族更无法纳入到“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被称为戎狄、蛮夷。
上古时期“中国”一词具有的内涵,对后世影响很大,故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如《新唐书》载:“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赋其盐布毡罽以利中土。”《宋史》载:“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嵠峒及以铜钱出中国。”《三朝北盟会编》载:“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载:“华阴,河行华山之北故曰华阴,河自北狄入中国皆南行,至此而极。”《乾道临安志》载:“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以上所列,涉及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中国”的含义却很相似,其所指均不是政权空间,而是文化区域。其中《新唐书》所书姚州,东汉时已经归永昌郡统辖,与中原内地有着完全相同的管辖方式,但在唐朝人理念中仍不在“中国”或“中土”之列。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政权对峙,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但中原诸国与都于杭州的吴越国之间,宋人仍认为位于黄河流域的政权为“中国”。唐五代时期,早已打破了上古时代文化地域隔绝现象,吴越所在之地不仅拥有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礼仪风范,而且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不凡的水平,尽管如此,上古时期形成的“中国”空间理念并未消退,仍然使人们将设在中原的政权统称为“中国”。
可以肯定,在华夏文化已经传布到各地后,文化诞生地被视作“中国”的理念仍然沿承下来,无论涉及政治、经济还是自然山川,凡言及“中国”,其地理方位均不离商周时期“中国”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或指建立在中原的地方政权,或指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至于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否自认为“中国”,仍在于政权的政治核心是否在中原。《辽史·张砺传》载:“(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张砺本为磁州人(今河北磁县),入辽后上奏辽太宗的奏文中以“大辽”与“中国”相对,因辽王朝的政治核心在塞外西辽河流域,而辽南京所辖地区在后晋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之内,属于传统“中国”的范畴,故有上述言辞。与《辽史》记载的情况不同,《金史·食货志》载: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金章宗泰和年间已是金人迁都南京(今北京)50年之后了,由于政治中心位居中原一带,金人以“中国”自居,反过来对位于江南的南宋政权却以宋人相称。《辽史》《金史》的记载说明,古人理念中是否认为是“中国”,并不在于政权建立者的民族归属,政权政治核心的位置与文化风范可能更为重要,故虽为女真人,只要拥有了中原之地,仍然不妨碍成为“中国”的代表。
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以下所引为《尼布楚条约》有关疆域的内容:
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9.7)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议条款如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
自“中国”一词出现后,《尼布楚条约》第一次赋予了它代表主权国家的含义。当然,清人签署国际条约中使用“中国”一词,明显含有西洋为化外之邦之意,尽管如此,此后“中国”一词逐渐摆脱了标定文化区的初始含义,而成为国家全部领土、全部主权、全体人民的代表。
“中国”一词词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汇自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故梁启超《少年中国》称:“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绵长久远,但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仅数百年,以数百年之短比万年之长,真可谓少年中国。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