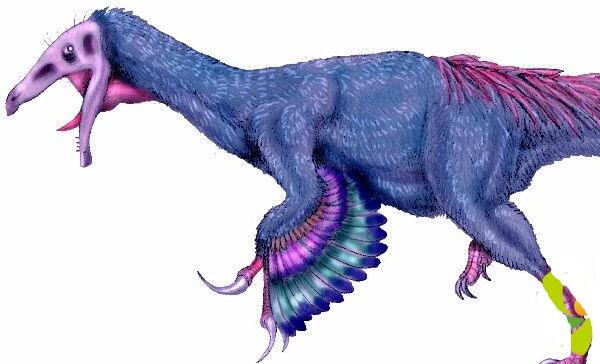侯仁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
一九四四年,侯仁之在天津工商学院为行将毕业的学生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常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所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定。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侯仁之写给行将毕业的“诸君”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出自在燕京大学多年生活中对于青年励志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自己的人生体悟。事业,成为“读书人”的士节与献身的核心,这是侯仁之自我摸索的结论,标志着学者之人生观的成熟确立。
侯仁之在三十岁之前确立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志,而侯仁之选择的这种历史地理研究,的确可以体现士节——矢志不渝,可以值得献身——终生不悔,可以令国家和社会蒙受他的利益——经世致用。
不过,在求学的初期,侯仁之却未曾想到过历史或地理,那时,“历史地理”还不是青年侯仁之准备献身的“坚定的事业”。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忧患意识与时俱进,在人生理想中,虽有奋发的愿望,但还未曾想过任何具体的专业,即使想过,也未曾轮到历史或地理。少年侯仁之,在对母亲的感念中,仅有过从事教师职业的笼统意向。
直到在中学理科班毕业,侯仁之在父亲的叮嘱下,有了做医生的具体想法。不过,在填写报考大学专业的那一刻,医学却只作为第二选择,而排在首位的是:历史学。这是侯仁之青年时代思想的重要转折,转得好像有点急。
侯仁之何以选择历史?坦率地说,侯仁之并不像许多报考历史专业的人那样对历史本身有多少兴趣,也不是像某些文史学者那样,四岁背古书,六岁写对联,有着传统的知学惯性。
历史学在侯仁之心头忽然跃出,首先是因为顾颉刚。一九三二年,侯仁之在因日本侵华而产生的苦闷中,读到顾颉刚的《贡献给今日青年》一文(载《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受到“不要空谈救国”号召的激励。侯仁之进而找来顾颉刚的《古史辨》阅读。然而,对于《古史辨》中曾引发学界震动的古史研究新法,却不是侯仁之的兴奋所在。倒是“长达百余页的‘自序’,犹如一篇自传,详细讲述了作者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却使我深有感受”(《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32页)。顾颉刚的人生品格吸引了侯仁之。很简单,因为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侯仁之便有了投考“顾颉刚的历史系”的想法。
不过,说侯仁之对于历史研究缺乏思想基础也不对,也不符合那一代人的学识特点。青年侯仁之对历史研究曾有真切体会,那是在中学行将毕业的时候。在同一期《中学生》杂志上,侯仁之读到一篇《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北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页)。历史研究可以解答今日的问题,这正是侯仁之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的缘故。这也成为一个特征,一直保持在侯仁之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它是认识侯仁之学术特色的一个关键。侯仁之从来是关注现实的,在侯仁之的理解中,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死线。其实,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本身是一类重要的学术问题,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研究与现实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实用”史学。
对青年侯仁之报考历史专业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他的弟弟侯硕之的一番话。侯硕之“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说他们本来都是学医的,却都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兼事历史研究,对社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2页)。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于历史学都抱有如此殷切的现实性期待。
一九三二年,侯仁之作为潞河中学的保送生参加了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并获得奖学金,进入燕大历史系。
燕大有三位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顾颉刚、邓之诚。以三位导师的盛名、学养和师风,历史系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极佳的求学环境,史学要义、治史之法均不在话下。学习是从基本训练开始的。侯仁之在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史学研究的正途。在洪业所授“史学方法”课中,侯仁之完成习作《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获得“佳甚”的评语。邓之诚曾出示相传为万斯同的《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嘱咐侯仁之详加校阅。经过研究,侯仁之断定这六本传记残稿乃是初刻《明史》列传稿的过渡稿本,所有删改字迹均出自王鸿绪的手笔,因而写成《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此文后刊载于《燕京学报》。当时,顾颉刚正准备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遂交给侯仁之为《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的工作。
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与研究,培养出侯仁之在史学考证上的方法与能力。他对严谨的考证方法也的确产生了兴趣,因频繁检阅古代文献,“稔识昔贤用力精勤,史法谨严,不禁爱之好之”(《明史列传稿斠录》,侯仁之著,载《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八年)。
不过,侯仁之的胸臆之中另有一种天然植下的爱好,它是生活以至学业路途中的另一种驱动力。侯仁之后来进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正是受了这一驱动力的推动。
侯仁之说:“我爱旅行。”大地,以及面对大地时的快意与追问的欲望,对侯仁之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幼年时代,家乡——华北大平原——的平坦与辽阔,便在侯仁之心中引发感受:天空“在四周的地平线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浑圆的圆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想我的家乡就是世界的中心了”(《步芳集》,96页)。刚入小学不久,侯仁之便随高年级同学远足数公里之外,登上一座最高的沙丘,“第一次在高处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蜿蜒的道路”。侯仁之还注意到,在沙丘上,“一些高大的果树被埋没得只剩了一些树尖尖”(《步芳集》,96页)。
可能谁都有过类似的快意,但在侯仁之这里,它们不但被牢固地记忆,并且持续地滋长、成熟、壮大。到了大学,侯仁之的旅行更增强了力度,也更富于主动性、计划性。在二年级的暑假,侯仁之选择了东西横贯华北大平原腹地的一条路线,约三百公里,中间包括三处特别吸引侯仁之的地方,一处是古代湖泊的故址,一处是九百年前湮没于黄河泛滥泥沙的古城,一处是位于平原中央的古战场。
在这次只身跋涉中,侯仁之的情绪格外高昂。“在我旅途中的第四天,我遇到了一阵阵连续不断的暴雨,但这并没有阻止住我前进的决心……骤急的雨点打在遍地嘉禾上,发出了有如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我就趁着这天然的乐曲,引吭高歌,好像为鼓舞自己的前进而奏起了军乐一样。”(《步芳集》,99页)
我们注意到,侯仁之如此热烈地走上这个旅途,并不是老师们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计划。这次出游,有两项要素,一项是侯仁之从来喜爱的大地旅行,另一项是侯仁之生活中新近出现的内容:历史探索。就在老师们以正规的方式指导他苦读历史文献(他也确实为之努力)的时候,侯仁之自己却又迈开了一个方向:走向大地。当然,他并没有抛弃历史,而是将历史与大地、旅行结合到了一起。侯仁之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有一门学问叫“历史地理学”。这次作为一个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实际上的历史地理考察,显现了侯仁之旨趣的个性。
当然,侯仁之的学术个性并非没有遇到启示性的机缘。正是在燕大,侯仁之遇到了这样的机缘,而令自己的学术个性一步步显现,并走向深入,走向成熟。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侯仁之接触到洪业的《勺园图录考》、《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这都是关于燕大校园历史的研究,它们虽然不属于正式的学业课程,但因为研究的就是眼下的实地、身边的环境,便十分投合侯仁之的兴趣。侯仁之的关注遂从燕园史迹开始,进而扩大到海淀周边,再扩大到整个北京地区。关注,便意味着实地考察,这是侯仁之的逻辑与风格。在北京西郊的古代园林沟渠遗迹之间,到处留下青年侯仁之的足迹。

顾颉刚、谭其骧领导的禹贡学会的成立,使历史地理研究变得名正言顺。不过侯仁之自有个人的特色,现实关注与实地考察依然是他的风格,这一点与学会的不少人都有区别。侯仁之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几篇“正宗”的史地文章(如《燕云十六州考》)而外,还有《记本年湘鄂赣四省水灾》、《萨县新农试验场及其新村》、《河北新村访问记》等。这几篇东西仿佛算不上史地类别,但侯仁之显然对它们抱有热情,在他的理解中,这几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与历史并非无缘。水灾,自古以来便是社会大患。新农村,是要从历史之中走出来,“目前之西北命运,亦再难容于以往之半荒废状态”(《河北新村访问记》)。
大约与此同时,侯仁之开始自觉地阅读地理书籍。这也是历史系的正规课程里面没有的。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侯仁之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发表了《读“房龙世界地理”》一文,这是所知侯仁之最早的一篇直接谈论地理学的文章。他在文中讲了如下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就理论上讲,地理与历史是分不开的。历史为地理所解释,地理为历史所诠注。但是,真要并成一块来写,可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书中他织入了许多重要史实,把平面的地理,造成了立体的叙述。把人类的活动放在全书第一位,把地理这科的传统性质企图改造起来。……这比专门去读一部普通的地文地理对一般读者有益多了。……
一些孤立的常识被这条“地理”的线索穿贯起来;好些单独的事件,就都成了一个舞台上的角色。这样,地理、神话、历史、传说的穿插交织,就是房龙之所以能征服一般读者的第一件武器。
把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是《房龙世界地理》吸引侯仁之并受到他赞赏的原因。侯仁之在这里,表面上看,是向“传统性质”的地理学家建言,但其实也是向传统性质的历史学家(包括自己)呼吁,“历史可以为地理所解释”。
此时,地理对于青年侯仁之来讲,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明确的可以认同的学科。一次,当老师偶然问到他的学术爱好时,侯仁之“贸然以地理对”。
一九三六年,侯仁之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靳辅治河始末》,已经很有历史地理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侯仁之被推举执笔所写的《一九三六级班史》中,有“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一语,再联系一年前四省水灾的严酷事实,可以想见侯仁之内心关怀的全景是什么。
一九三七年,侯仁之作为助教,协助顾颉刚的“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的教学,主要负责事先的资料准备和参与调查。这个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工作正是侯仁之的长项,他曾负责组队到开封与洛阳实习,参加的不只是燕大的同学,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闻一多、陈梦家、叶功超。
在文献准备与实地踏查的过程中,侯仁之颇有心得:
来到现场对比实迹实物的时候,也会发现我所根据的资料不尽可靠,也有时是调查对象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些情况,大家往往不甚注意,我却不得不格外留心。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5页)
关于古迹古物考察的部分内容,由邓之诚定名为《故都胜迹辑略》,印刷成册,这是侯仁之的第一本著作。
我们不曾知道最初侯仁之是怎样一步步具体研究北京的,但到了一九三八年,侯仁之关于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察,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一次,一个由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妇女组成的类似沙龙的组织请洪业去做英语讲座,题目是Historical Peking(历史上的北京)。洪业推荐侯仁之代替自己去讲,并特意将题目修改为Geographical Peking(地理上的北京)。此事可说明两点,第一,侯仁之已经具有系统讲解北京史地的水平;第二,侯仁之的研究已经具有鲜明的地理学特色。
以上所述大约是侯仁之在燕大历史系“倒向”地理学的几个关键折点。很幸运,侯仁之遇到了一位十分知己的老师:洪业。洪业支持侯仁之的选择,一九三八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洪业把侯仁之叫到燕南园五十四号家中,明确地对侯仁之讲“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侯仁之燕园问学集》,16页)
洪业看出侯仁之研究中越来越明显的地理学特征,理解并支持他的学术志向,同时也感到侯仁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正规的地理学的深造,所以主动向侯仁之提出这个建议。洪业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值得去西方学习历史地理的人。
在那个阶段,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地理学理论方法的融入,关于这一点,禹贡学会也已经意识到,但因“七七”事变,顾颉刚出走,禹贡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断。这可能也是洪业建议侯仁之出国学习的一个原因。
侯仁之在本科学习的时候便已脱离了“正宗”的治史方向,“我惭愧的是未能继承我师的主要学业”(《侯仁之燕园问学集》,17页),但是,侯仁之一直感念洪业对他选择地理学方向的鼓励与支持,常常说:“是煨莲师引导我走上历史地理研究道路的。”不过,准确地说,侯仁之朝向历史地理学方向的发展,并不是洪业的有意引导,洪业的作用是慧识与支持。产生引导作用的其实是侯仁之自己内心的追求。
从青年侯仁之转向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的实例中,我们观察到地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直接面对大地的基本精神;二、古今一体的完整关怀。
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发现问题——解析问题——问题结论,一般都是直接从地面开始。地理学存在的前提当然是地面事物的丰富性。在青年侯仁之的时代,地上的当代要素早已被学者关注,而历史要素,相对来说,尚缺乏专门的关注。在中国这样一块历史积淀深厚的大地上,一个巨大的地理学发展空间是对地面历史要素的重视与研究。对地面历史要素,需要系统的梳理,开启深入的问题意识,采纳科学的分析程序,得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结论。
像历史文献中存在混乱一样,大地上的历史要素也存在混乱,如何在大地上将它们理出一个套路,这在资料与逻辑的运用上与文献研究具有共同之处。学者们在探索的兴趣与智力的表达上,可以获得同样的乐趣。
青年侯仁之走向大地,从历史学转向地理学的意义,正在于朝向这个学术领域的积极推进。侯仁之进入历史地理学,是用脚踏进去的。
大地本来是古老的,或者说是古今一体的。地理学一般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的地理环境,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结果,这是一批地理学家向历史时期探索的最初动力。这种研究本身就反映了一体化的内质。有评论说,法国地理学家普遍具有历史探索的风气,所以法国地理学家都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却没有多少纯粹的历史地理学者(只研究历史不研究当代的专职学者)。不放当代,而去研究古代,常常是地理学家的特点,或者说,是从地理学发展出来的历史地理学家的特点。美国历史地理学者大多是从地理学发展出来的,就有这个特点。
与一般地理学者不同,历史学者可以放下当代,单纯研究古代问题,至少在主观上或看起来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史学意识越强,向古代走得越远。美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布朗,原来是地理学家,后来涉及历史时期,史学意识逐步增强,越走越远,遂发出这样的感慨:There are two pasts!他感到有两类“过去”,一类是与今天有联系的过去,另一类是与今天失去联系的更遥远的过去。布朗把地理学研究带入“更遥远的过去”,扩展了时代视野,对于美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一个贡献。
中国的情形相反,早年历史地理学者主要是从历史学出来的,没有重视当代问题的习惯。那么,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建立古今一体化的意识,肯为当代地理环境负责,便成为学术发展、完善的一项任务。侯仁之虽然也是历史系出身,但他不放弃对当代的关怀,这与地理学的基本点是吻合的。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大力推进古今一体化的意识,是侯仁之的贡献。
侯仁之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的计划因欧战爆发而受阻,直待一九四六年战争结束后才得以成行。一九四九年,侯仁之学成回国。一九五二年,侯仁之转入北京大学地理学系工作,直至百岁高龄。
选自唐晓峰:《踏入历史地理学之路——再论青年侯仁之》(载《读书》2013年第7期 )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