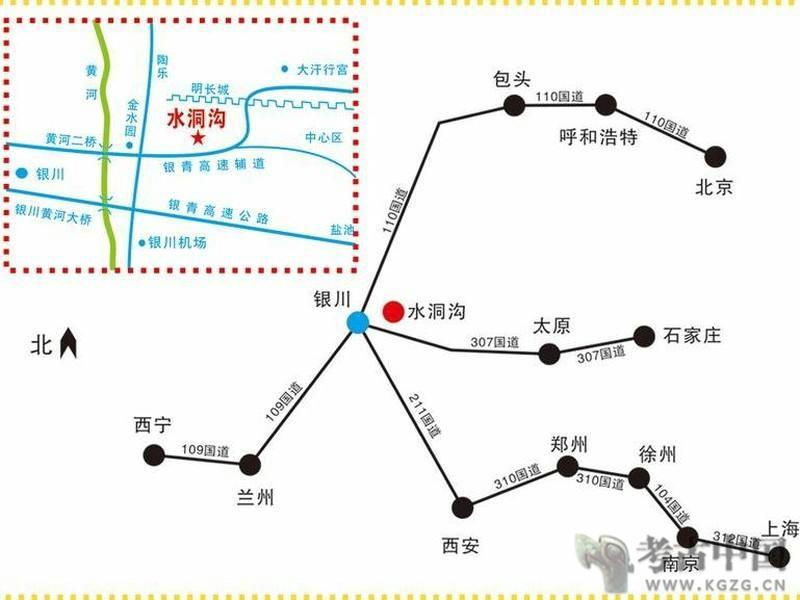葛兆光:“亚洲”或“东部亚洲”,凭什么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头条创作挑战赛#
“亚洲”或“东部亚洲”,它为什么,或者由于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说的,我们当然知道,亚洲并不是一个,东亚、南亚、西亚、北亚差得很大,甚至连东部亚洲也未必是一个,从语言、文化、人种、经济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
过去写亚洲历史,都会碰到这个麻烦。我想举两部很典型的书为例:一是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他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桑原骘藏一样,亚洲历史包括了东亚、西亚、北亚和南亚,如果从宗教角度看,至少涉及了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家覆盖的广大地区。所以,他很聪明地不论述什么是亚洲的共性这个问题,你看他在第一章《亚洲诸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里,就是分别介绍古代波斯、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大概地分成三大块,然后再讨论各个民族与文化的相互交往。但是,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亚洲史》,则把大部分西亚的伊斯兰世界从亚洲隔出去,试图对此概括出一个亚洲性来。他用了一个“季风亚洲”概念,基本上西边儿只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你看他的书里,地图就只有这一半。为什么?他自己说,阿富汗以东和近俄罗斯以南的这一块儿,还有“一些有着普遍意义的特征, 使它成为一个合适的完整的研究学习单元”,他列举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包括:(1)大家庭和亲属关系网及其多重功能具有重要性;(2)为家庭或地位尊重知识;(3)尊敬长辈以及长辈有权威;(4)妇女处于屈从与谦卑地位;(5)社会分等级;(6)重视历史和传统;(7)集体优先于个人。他把这些称为季风亚洲所有地区共有的文化特征。可是,这个总结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些指标不具有根本意义,也不能涵盖整个季风亚洲,而且,所谓季风亚洲那么大,内部差异太大了,印度教佛教区域、伊斯兰文化区域、儒家文化区域,在这些方面不见得趋同。
 ▲《亚洲史概说》
▲《亚洲史概说》
 ▲《亚洲史》
▲《亚洲史》
当然,从历史上看,亚洲/东亚的某些历史联系,实在也是不少的。以前,我们特别爱用“圈”这个字,表示某个历史文化共同区域。比如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东海或者南海贸易圈等等。一个区域在历史学意义上可以成为一个“圈”,一定得有一些联系的要素才行,这个联系的要素,就是彼此可以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或经济世界的基础。而注重"联系"的全球史研究或者区域史研究,这个“圈”,也就是他们关注的“网络”,是把不同国家和族群连在一起的“网”。无论是“圈”还是“网”,一般说来,使一个区域成为一个历史世界的,应当特别关注的因素大概有以下五个——
战争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是不消说的。从小的来说,战争推动吞并和殖民,秦汉以郡县制把各种华夏边缘逐渐“纳入中国”,主要依靠的是武力,在政治制度上统一,否则六国诸侯谁听你的呀。同时,从大的来说,战争也推动技术、知识、风俗和物质在全世界范围的交流,影响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的变动。比如:(1)公元 750—751年发生在葱岭以西,也就是现在中亚一带的怛罗斯之战,就使得大批中国战俘进入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通典》里面说“高仙芝伐石国,于怛罗斯川七万众尽没”。你看从《通典》等文献中重新辑出来的杜环《经行记》就知道,很多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技术都向西传播。据有人说,西方早期都是用羊皮纸,一直到怛罗斯之战,中国战俘被虏,大食人学会了造纸术,在撒马尔罕造纸,向西方出口,从此这种书写新材料才逐渐传到西方,于是,用纸书写和印刷的世界就形成了,这对欧洲来说影响巨大,甚至后来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民族国家形成,似乎都和这个技术传播有关。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年鉴学派大学者费夫贺和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2)接下来八世纪末,回鹘和崛起的吐蕃王国之间争夺北庭的战争,有人指出,尽管吐蕃控制,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北庭和西域的控制权,但是信奉佛教的吐蕃,也使得更西边的伊斯兰力量未能更深入地东进,这影响了西域乃至中国内地的宗教与文化。(3)蒙古时代为什么可以说是世界史的开端?就是因为蒙古大军东征西讨,通过战争把欧亚大陆连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世界了。(4)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壬辰之役”,就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日本和中国打了一仗,很多朝鲜人被掳到日本,从这些朝鲜战俘那里,日本也学到了很多大陆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包括烧制瓷器(像下面讲到的古伊古丹瓷器即“有田烧”),如果谈论“瓷器制造的世界史”,中日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圈”。
在亚洲/东亚地区,移民是使各个区域各个国家在文化上互相联系的重要因素。现在,大家都说日本大和民族多么单纯,其实,日本的早期人口中,有多少是原住民?有多少是从百济移民过去的?现在流行的说法,说日本绳文时代的人来自东南亚,弥生时代的人来自东北亚。就连日本的天皇,还有人说有来自朝鲜半岛的血缘呢,这绝对是真的。日本有名的桓武天皇(かんむ てんのう,737—806), 他妈妈高野新笠就是来自百济的。如果按照江上波夫(えがみ なみお,1906—2002)“骑马民族”的理论,日本人还有一部分是北方亚洲游牧征服者的后代呢。当然,日本也有中国人后代,你们都会记得“徐福”的传说,徐福是不是真的有,还可以讨论,那几千个童男童女是不是真的去了日本,也可以怀疑,不过早期日本所谓“归化人”,也就是中古时代从大陆过去的移民嘛。
 ▲桓武天皇
▲桓武天皇
中国也一样,不说最早的,就是到了中古,那各族移民也同样多了去了。唐代以前的,你读一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唐长孺的《魏晋杂胡考》和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你就知道北方中国胡人移民的情况。到了七世纪,唐王朝打败东突厥,也曾把突厥人安排在长安附近居住,突厥人慢慢地就成了长安人;联合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时候,也强迫高句丽和百济的很多人进人唐王朝控制的地区,于是,高丽人就变成中国人;至于西北过来的中亚西亚胡人,比如什么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来自西亚的“波斯胡”,还有所谓“菩萨蛮”,也是外来人口呀。举两个大家可能熟悉的例子,一个是白居易,陈寅恪就认为他的先人是“蕃人”;而尉迟恭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和秦叔宝一块儿当门神的那个武将,日本的羽溪了谛、榎一雄,中国的向达,都曾经猜测他家族来自于阗,而赵和平就考证了在青海、甘肃一带,有八个尉迟家族的人物。最近尉迟氏的墓志出土了,证明尉迟氏是鲜卑人,魏孝文帝之后,分为洛阳和并朔两支,在北周、北齐都很显赫。你们看,中外之间,是不是移民很多?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例子,以前,葛承雍说崔莺莺是“酒家胡”,有媒体借机宣传说,就是“外国酒店女招待”,这当然是哗众取宠的媒体标题党,但当时长安酒家的胡姬,确实是很多,李白的诗就说“胡姬压酒劝客尝”嘛。
当然,明清以后的移民现象更值得注意,如果说中古以来,特别是东晋南渡、安史之乱、宋朝南渡为代表,引人瞩目的是北方胡人南下,中原汉人再南下,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地理空间,那么,对于明清以来的移民,你要关注的,一是海上移民,从东南沿海区域向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文莱的移动;二是从广西和云南向缅甸、越南、暹罗的移动;三是从湖广地区向川黔的移动。前面两种移民,把东亚、东南亚连起来了,也重新塑造了南方中国和东南亚高地、平原和港口地区的文化交流。后面一种移动,有人说是内部殖民,实际上和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文化开发,逐渐纳入华夏,很有关系。
商品流通是广袤的各区域之间最明显的联系了,也许不用多讲,现在学界有说“环东海贸易圈”的,有说“南海贸易圈”的。大家都知道,传统时代的商品流通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丝绸”和“瓷器”。丝绸的贸易形成了“丝绸之路”,把东亚、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系起来,而瓷器则构成更广泛的陆地和海上贸易圈。2016年,我曾经在新加坡的亚洲博物馆参观“黑石号沉船”的出土物品,让我非常震撼和感慨,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居然有这么大的商船,经由中国沿海,到南海,到马六甲,到印度洋,然后到达波斯;居然有这么多的瓷器,包括河南巩县、湖南长沙的产品,通过这些海上的贸易船,运到遥远的地方。瓷器的贸易甚至一直到 达非洲东岸,考古学家说,在非洲肯尼亚,就出土过元明清三代的瓷器。大家知道,北起韩国木浦、中国山东,南到福建泉州、广东阳江,都出土了好些沉船,这些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只,很大很大,宋元时代就有可以装载30万斤,五六百人的大船,包括从中国出去的,也包括来自印度洋的,他们通过香料、瓷器、丝绸的贸易,把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上的印度、波斯、非洲,都连在一起了。
 ▲黑石号复原模型
▲黑石号复原模型
顺便说,对瓷器的需求,还促使这种制造技术在东亚的传播,我曾经在日本福冈国立博物馆看到,中国的瓷器技术经过朝鲜,传到日本,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壬辰之役”中被日本俘虏的朝鲜工匠,就把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瓷器制作技术带到了日本,后来,日本九州的所谓“古伊古丹瓷器”,就是后来所谓的“有田烧”, 反而比中国的瓷器还好,甚至在外销欧洲的时候,抢了中国的生意。不过,在通常注意的“丝绸”和“瓷器”之外,我觉得香料,以及白糖、茶叶和鸦片这三样,特别值得注意。像德川时代的日本长崎,与中国合法的贸易中,最大宗的就是白糖。一只船几十吨上百吨的糖,像乾隆四十四年(1779)沈敬瞻当船主的南京船元顺号,船上装了165000斤白砂糖,12000斤冰糖;乾隆五十四年(1789)朱心如当船主的安利船,也是165000斤白砂糖,装了1420包, 冰糖19500斤, 装了100桶。在这个需求和贸易背后,也许,还有很多可以说的话题呢。
顺便插一句,商品流通的同时,还有钱币的流通,古代中国出土了不少古罗马、古波斯的金币、银币,而环东海南海各国也出土了很多中国的铜钱,中国的铜钱有一段时间就像“国际通货”,在日本、朝鲜、安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流通的,为了铸钱,而中国的铜又不够,于是要从日本进口铜,一直到清代,各省还是要从日本贩运铜来铸钱,这也可以是一个“钱币的全球史”吧。
文字和图像,是“无脚走天下”的东西。以前西嶋定生说的“汉字文化圈”,就是把东亚——其实还包括越南——连在一起,依赖汉字书写的习惯的一个文化共同体。汉字就像欧洲的拉丁文,各国都用这种文字来书写、联络、纪事,各族就一定共同拥有一些思维习惯、传统文化、礼仪规则。就像拉丁文的传统一旦崩溃, 各国开始用各自的“国语”和“国字”书写、印刷、传播、教育,大帝国或共同体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以前胡适就说,文艺复兴催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国语”,“国语”则是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
但是,在传统时代,东亚确实就是共同使用汉字的,这种文化把东亚联系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到了近世日本用假名,朝鲜用谚文,各自创造自己的语言文字,促成各自的文化独立意识,以汉字作为通行书写文字的东亚历史世界就开始分化了, 但是,你看看长崎唐船贸易里面,有多少汉字的书籍在流通?日本学者大庭脩对江户时代唐船贸易中的书籍流通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彼此锁国的时代,大量汉字图书也一样把东亚连成一个知识网络,而废弃汉字,可能会导致对中国传统的背离。所以,朝鲜世宗二十六年(1444),也就是明朝正统九年,朝鲜国王颁布《训民正音》,推广谚文也就是有音无义的朝鲜拼音文字,有一个叫作崔万理的三品官员就反对,他说这很危险,因为推广了这种文字,就违背了“华制”。什么是“华制”?就是书同文。他说,只有蒙古、西夏、日本、西蕃(西藏)才另有文字,但是另有文字的“是皆夷狄耳”,可见文字是一种很重要的联系,所以才有“汉字文化圈”的说法。
同样,图像也是一种构成共同文化的要素,从古代中国形成的绘画,包括它的色彩线条、形态风格、欣赏习惯,更包括若干共同的主题。比如墓室壁画中的四神星象、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日本的“飞鸟美人”和集安的高句丽墓室壁画,以及西安的唐朝墓室壁画,很多是很像的;再比如宗教雕塑和绘画中的佛菩萨、十殿冥王、高僧,以及文人艺术中的幽玄山水、花鸟鱼虫、都市繁华等,这些共同的主题和风格,都是把东亚联系为一个历史世界的“要素”。比如,宁波的画家,就专门给日本绘制他们订购的佛画,现在我们还看到一些日本保存的宋代佛画,像《十王图》,就是那个时候的出口商品。最近,艺术史界讨论很热烈的《五百罗汉图》,分别收藏在日本的大德寺,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这就是南宋前期(约孝宗、光宗、宁宗时代)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画家周季常、林庭珪画的, 后来辗转被日本镰仓寿福寺收藏, 先后经过当时日本执政者北条、丰臣秀吉所拥有,最后才被大德寺所得,其中又有十几幅流落到美国,就是这些罗汉图,也就构成了一个联通东亚艺术史世界。我以前读到石守谦讲山水画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宋代开封流行十一世纪后期日本的绘画折扇,当然这种"倭扇"也可能并不是真的日本货,而是高丽商品,因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里面说,高丽国每次派人到中国,都带了折叠扇,“其扇用折青纸为之”,有的“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为之倭扇”,当时有人分不清日本、高丽,还以为日本是高丽的附属国,所以高丽的折扇也叫作“倭扇”。北宋人记载说,熙宁年间,汴梁相国寺,也就是首都最热闹的地方有卖日本国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般小舟,渔人披鞋衣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但是,你从描述来看,这折扇画风完全是中国的,但是这折扇却是日本的,也可能是在高丽纸上画的,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东亚艺术确实有共同要素。
 ▲《五百罗汉图》(局部)
▲《五百罗汉图》(局部)
在亚洲或者东亚,曾经流行,并且超越国家或王朝的,有好多宗教,中古有所谓“三夷教”,就是从欧洲、阿拉伯半岛、西亚逐渐过来的宗教。琐罗亚斯德就是袄教,摩尼教后来也叫明教、食菜事魔,景教也就是后来的也里可温、天主教、基督教。此外,还有回教也就是伊斯兰教。其中,普遍存在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一直不断的,最明显的当然是佛教。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一个世界性宗教,但更应当说,它就是亚洲的宗教。它从尼泊尔、印度起源,一面传到中亚、西域,一面传到南亚、东南亚,通过陆、海两道 进人中国,从中国到朝鲜,从朝鲜进人日本,不仅形成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而且还分成不同流派,密宗从印度传人中国,在盛唐热闹了一下,很快衰落,可是在日本,却大大兴盛,成为日本真言宗;佛教在中国大部分 地区是汉传佛教主要是大乘,但是在云南却受缅甸、印度和西藏佛教影响,好多地方是小乘或密宗;在发源地印度,佛教衰落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东南亚却非常兴盛,你看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就知道。
不光是佛教这样所谓世界性宗教,就是很多看上去是某个国家的土产宗教,像中国的道教、日本的神道教,也有很多外来因素,不把它放在亚 洲或者东亚背景中,也研究不好。甚至包括墓葬壁画、神像、随葬品等等,也是各个区域互相影响的。举个前人研究很深的例子。十二支,也就是十二地支,作为十二生肖神像,以前,最早有章卷益讨论过,童书业和他的女婿黄永年先生也考证过;日本更早,像内藤湖南也考证过,而西嶋定生则写过一篇长文《中国、朝鲜、日本十二支像的变迁》,就非常仔细地讨论中古墓葬中的十二支像,在新罗、日本和中国的流传和变化,说明先是在墓志石上有兽身兽首的十二支,这从隋代就出现了,到了唐代天宝年间,出现了人身兽首的十二支像,到了晚唐九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人身人首的十二支像。这种十二支的变化,陆续影响到新罗、高丽、契丹、日本,出现了相应的十二支像。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你再看法国学者沙豌的《突厥十二生肖》, 就会发现这种信仰实际上还不只在东亚流传, 甚至还传到吐蕃, 宋仁宗时代就由出使的官员传到啪厮啰(就是吐蕃之一部),也逐渐波及东南亚,元代就传到了柬埔寨和暹罗,那里的十二生肖名称,是从安南语转译的汉语;甚至早在唐代中亚、北亚的骑马民族就已经知道十二生肖并用来纪年。沙豌甚至还认为,可能是突厥人发明的十二生肖,在公元初年才传到中国,“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之前,应将十二生肖的发明归功于突厥人”,这就更麻烦了。这就是一个贯通亚洲历史的很好例子。
古代宗教信仰是这样,那么,近世的宗教信仰呢?我讲一个例子,基督教传到东亚来,在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反应就值得比较,我以前写过一篇论文,通过十九世纪初朝鲜“辛酉教难”中的黄嗣永帛书,就讨论过日本德川时代、李朝朝鲜以及清代中国对基督教的不同反应。
如果你把宗教传播、宗教反应,放在东亚整个区域连在一起讨论,你就能看到很多有趣的文化史现象。
(本文选摘自《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出版
- 0001
- 0000
- 0000
- 0001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