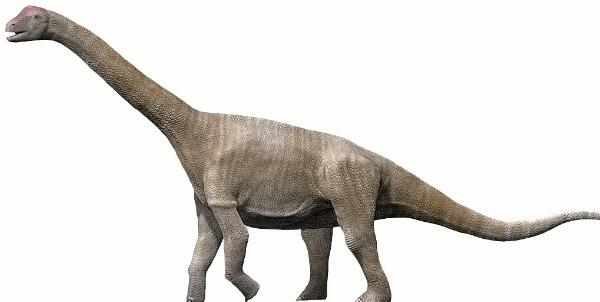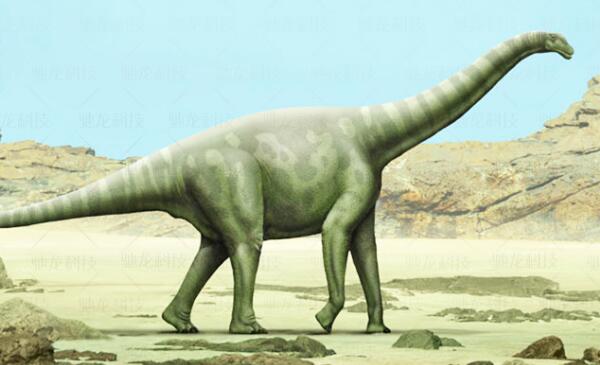从石峁遗址谈 “共生” 社会的形成
郭静云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完整公布, 其地层、 年代、 分期、 遗址布局、 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还难以确定, 但基本可知这是文化混杂的遗址,既包含本地长居的农耕和渔猎族群的聚落, 也包含有数波来自草原的流动的游战族群。 这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的 “共生” 现象, 在距今 4000余年前的南草原地带(即欧亚大草原南缘) 颇为普遍, 从铜石并用时代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直至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 (Andronovo) 文化都有,形成了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大文化体系。

这种 “共生” 现象起因于游战生活方式的形成。 由于气候变冷, 在亚洲大草原地带, 原本南缘就很脆弱的少量农耕衰退, 采集狩猎者赖以维生的食物资源亦变少, 一些原本以游猎为主兼少量农耕的族群转变到以掠夺维生, 努力发展战争技术而成为专门的游战族群。 游战族群逐渐发展出军力政权, 以游战掠夺或远程贸易营生。 他们在历史上发展青铜兵器技术, 并逐渐掌握驯马交通技术。
我们不能以为游战族群只是不停的流动, 不定居更不会建城。 正好相反, 他们因以战争维生, 一定需要有掠夺后回来的保护区,也在活动范围中需要建筑几个据点。换言之,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部分流动, 同时亦有定居点或根据地。 所以, 在从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内,在亚洲草原丘陵地带出现了非常多的大、 中、 小型城池,它们均属于军城, 作为掠夺、 游战族群的城邦和堡垒。 这类族团甚多, 但是他们自己不耕地, 不养猪、鸡等, 不生产定居生活族群的产物, 所以其日常所需严重依赖农耕和畜牧的定居聚落, 尤其是在建城时, 需要与本地原居的农耕或放牧族群建立 “共生” 关系。
在此要说明的是, 这种 “游战” 族团未必有血缘关系, 往往依据某种势力或凭首领感召而混杂组合为一群, 群体分合变化纷繁。从青铜时代早期以来, 这类族群组团结合很多, 他们不仅依靠掠夺农耕或牧业生产者维生, 彼此之间也互相竞争, 不断互斗和战争。 尤其是在选择栖息地点方面,每一游战族团都会追求尽可能占据有利之处。
这种 “有利之处” 有几个指标, 其中最关键的有二: 便于建堡垒的破碎地形 (陡峭山丘与山谷),包括能用作瞭望塔的地点;周围一定有定居的以农耕和饲养家畜为生的聚落, 能提供部分食物来源。 因为当时掠夺族群不少, 所以本地农耕聚落也面对必须接受这种共生关系的局面, 以免被众多游战族群不断轮番地抢劫, 而是专养一群强人以保护自己, 或许还可以从固定庇护人的强大与获胜中获得额外收益。
石峁所在地点和其他一切条件都完全符合游战族团栖息所需,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其地点恰好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带, 南下掠夺路线于此开始。 当时生态条件比现在好, 故周边亦有农耕、 畜牧和渔猎聚落存在, 山上可狩猎野兽。因破碎地形而形成的诸多陡深沟壁等自然障碍成为修建坚固堡垒的自然基础,使工程量大大减少, 坚固堡垒的修建成为保护自身安全并存放战利品的据点。
因此当时这应该是很多族群都希望掌握的地点, 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早晚占据过石峁军城, 屡被沿袭使用且不断地补建 (这从石峁群城的建墙技术不同且明显可见多次补建的痕迹可以看出)。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大族群的大聚落, 而是很多族群在某段时间掌握, 互相纷斗或被竞争驱赶的中转站和据点。
简言之, 在青铜时代早期, 亚洲草原南部与山丘交界之地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体系, 这是一个定居与流动、 农耕与游战“共生” 的地带, 是游战生活方式的发祥地。 石峁遗址的地点恰好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土高原破碎的蚀沟梁峁地形交界之区, 是族群流动、互斗和掠夺并存放战利品最频繁的地带。 游战生活方式的发展, 到了殷周时期, 生计逐渐转换为以远程贸易为主。 黄河水系从北往南下来的部份会有游战族群短期的据点, 但是到了后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成为草原与殷周贸易的联接地带(如马匹贸易), 从事远程贸易的族群与本地农耕、畜牧居民 “共生” (以陜北清涧县的李家涯、辛庄遗址为例); 而黄河水系 “几” 字形的上段北游是游战族群栖息、 安排较常用据点的地带(以神木县石峁群城为例)。 也就是说, 在共生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族群, 在不同的地带和历史阶段中, 或是以远程贸易为生计的贵族, 或是以战争掠夺为生计的贵族。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25日
- 0000
- 0000
- 0004
- 0002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