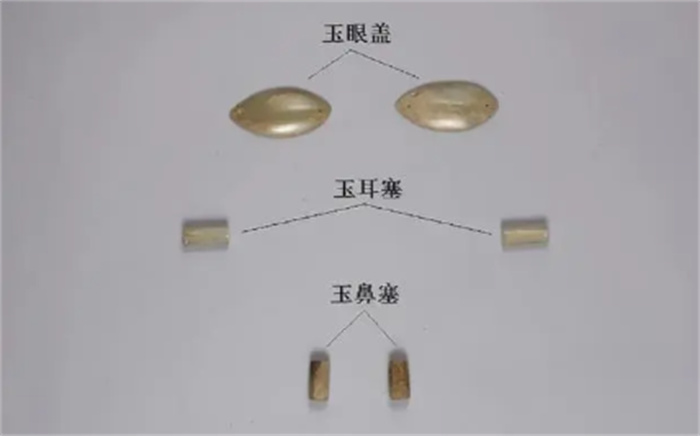陈春声:真正的学术群体应该“脱俗”
2016-07-20 陈春声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我以为,从事“华南研究”的这个学术群体,应该不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我一直以为,目前有许多年轻的学者和学生从事传统乡村和地域社会研究,蒐集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进行实地考察或田野调查,关注民间信仰、宗族组织、乡村社会组织等等,并不一定是因为大家在学术价值观上比较接近,认同或接受了某种共同的学术规范。我的感觉是,许多年轻学者在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习的阶段,觉得学位论文的选题不容易确定,在原来的通史教科书的套路下写大的题目不容易有新意,就去选个村落的、区域的、家庭的、个人的历史做论文题目,这样的“小题大做”貌似比较安全,答辩时比较容易通过。至于这些具体研究的背后有没有大的问题、大的学术史背景,有没有建构理论的学术追求,那就另当别论了。比较担心的情况是,大家看到许多同行在做类似的研究,以为“华南研究”的学术追求得到了更多的理解,有了许多志同道合者,而实际上可能大家不一定真的拥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观。

如果一定要讲几点体会的话,我想下面这三点是应该被提到的。
首先,一个有共同追求的真正的学术群体,应该是“脱俗”的。也就是说,这一群人必须没有俗气,大家一定要把学术当真,不会特别计较,尤其是不会计较个人的所谓“得失”。譬如,有一些学科的学者比较不喜欢同行去看他的田野调查点,据说这是“行规”。我们这群人下乡去做调查,常常邀请同行们也去看看,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调查点上举行过不止一次的考察和研讨活动,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把自己学生的调查点也开放给其他的老师,请其他老师提意见,一起指导学生。
说实在的,“华南研究”的共同学术兴趣和问题取向,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和氛围中培养起来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我才认为“脱俗”对于真正的学术群体的形成,实在是太重要了。只要不俗气,把学术当真,就必然会影响到学生。老师不俗气,就自然会有些不俗气的学生跟着你。反过来,如果老师都俗气了,要学生“脱俗”真的很难。人文学科跟社会科学、自然学科有所不同,人文学科更多是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学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人文学科的工作好不好,有用还是没有用,价值大还是小,不仅仅是看文章,不仅仅是看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以一个一个活着的人文学者做榜样的,看他怎么做人处事、怎样研究和讨论问题。

其次,是要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一些最基本的带有信仰和价值观色彩的共识,或许有点像库恩所谓的规范。这些共识常常是从共同的具体问题开始的。“华南研究”的朋友们一直拥有一些可以共同讨论的具体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一直在变。20世纪90年代初,在做“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时,大家都比较关心乡村的庙宇和民间信仰的历史;而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举办“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之前,他给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单子,希望大家讲清楚:所研究地方最开始出现宗族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当地第一个祠堂是什么时候建设的?什么时候有第一部族谱?问的似乎都是与宗族有关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讨论一个报告,讲一个地区的事情。几天下来,我们逐渐明确了大家应该共同关心的是:拥有不同文化的不同地方的人群,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背景下,成为“中国人”的?换言之,地方文化千差万别的广袤地域,是通过什么样的历史进程形成这样一个叫“中国”的统一的国家的。
在日后的研究实践中,我们更加明确了,了解王朝制度的演变与地方社会如何结合是整个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制度的研究来理解不同的地方社会如何融进国家,从这一点出发或者有可能重新解释整个中国历史。从这样的角度看,在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里,制度史的脉络可能是本质性的。近年推动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计划,让更多的年轻学者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实践和探讨这一学术理念。这样的过程可能跟自然科学有些不一样。在自然科学界,可能在出现一些关键性的颠覆性实验之后,科学共同体就会很快地明白某个学科领域的核心问题在哪里,然后大家就共同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而人文学科常常要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大家才慢慢地明确共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更要命的是,从明白共同问题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经在想,这个有点带着“规范”味道的问题也该“过时”了,又开始想新的共同问题。特别希望学生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第三,我们还是一直在强调人文学科的学术本质在于传承,而传承的本质又在于“叛师”。我在其他的场合讲过,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传统中国地域社会研究,属于有着深远渊源和深厚积累的学术追求的一部分,所谓“华南研究”的学术取向和价值追求,是学有所本的。我们这群人一直强调自己追随的是梁方仲先生、傅衣凌先生所奠基的学术传统,我们的工作仍然可以归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范畴。我们这几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过的,常常会提到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前辈们的影响。傅斯年等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这里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并在研究所设立人类学组,培养研究生,开展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先生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他们所开展的乡村社会调查,表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特色;杨成志、江应梁等先生,以及当时任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序经先生等,还在彝族、傣族、瑶族、水上居民和其他南方不同族群及区域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奠基意义的努力。这些工作都是所谓“华南研究”的出发点。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学术传承的本质还是叛师,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叛师其实是学术传承最重要的环节,所谓“师我者生,似我者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家觉得你能够继承自己老师的前提,是因为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先跟着老师学,最后做得跟老师不一样,也就“顺便”弘扬了老师的贡献,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传承”。所以说,传承背后最本质的一点,是要有一点叛师的精神,不叛师就对不起老师,这是关键,而叛师是需要有自信的。很高兴的是,我们的学生做了许多与我们很不一样的工作。
讲到学生,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研究生在学校的时间有限,写学位论文的时候,常常来不及扎根某个村落做深入的研究,而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有一个观察、研究了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村落,作为区域研究的立足点。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没有一个深入的村落研究的经验和体验,是会影响到地域社会研究的质量的。村落研究是最能达致所谓“总体史”境界的,必须能够用“乡村的故事”将“国家的历史”讲通了,关于地域社会演变的理解和解释才能立得住脚。我们常常被视为“进村找庙”者,且不时也会听到说我们的工作“鸡零狗碎”的批评,其实村落研究对于理论建构的重要价值,是没有类似经历的同行难以理解的。我以为,对于我们的学生辈来说,村落研究仍然是不能轻易就绕过去的一个坎。
讲到今后可能的发展路向,也许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要充分预见“数字人文”时代到来的学术影响。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以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为特征的所谓“数字人文”的时代正在到来。传统时代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
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因为这样,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我们学生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的更重要的尺度。
我们要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的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三十多年前我们面对的更复杂、更艰难。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是:50年后的历史学家想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要到哪里去找资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除了今天我们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讲授的这一套东西之外,也许他们更需要懂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个人密码破解技术等等,因为他们要蒐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获取。在使用历史资料的技艺层面上,我们这一代已经落伍了。现在就理性地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处,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可能在本质上预示着学术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要考虑是不是到了该编写一本好的中国历史人类学教科书的时候了。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我们强调,要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通过个案的、区域的研究来表达整体的历史关怀。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反对随随便便对自己的研究做概念性的总结,觉得让大家了解和接受的最好方式,还是写几篇像样的研究文章,出版几部像样的学术专著。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范本”比教科书更重要。
不过,近年我们中开始有人在讲编撰教科书的必要性了,这或许与人的生命周期有关,老之将至,就难免会多想一些比较体系化的东西。我自己以为或许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但这应该是交由学生们去做的事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明清史研究资料”。
作者:陈春声
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 0001
- 0000
- 0001
- 0000
- 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