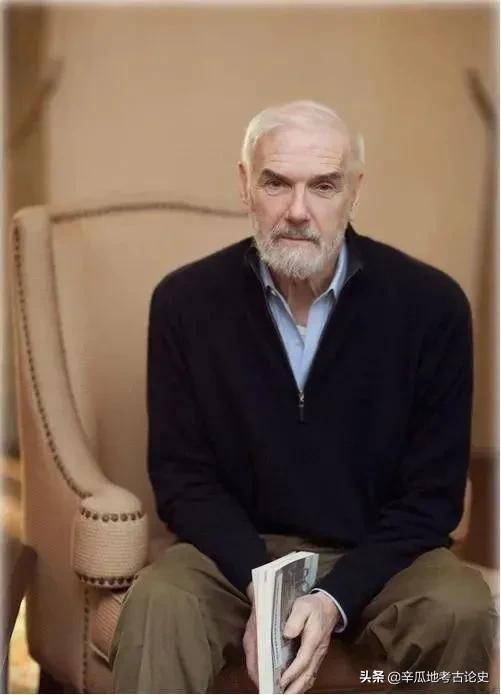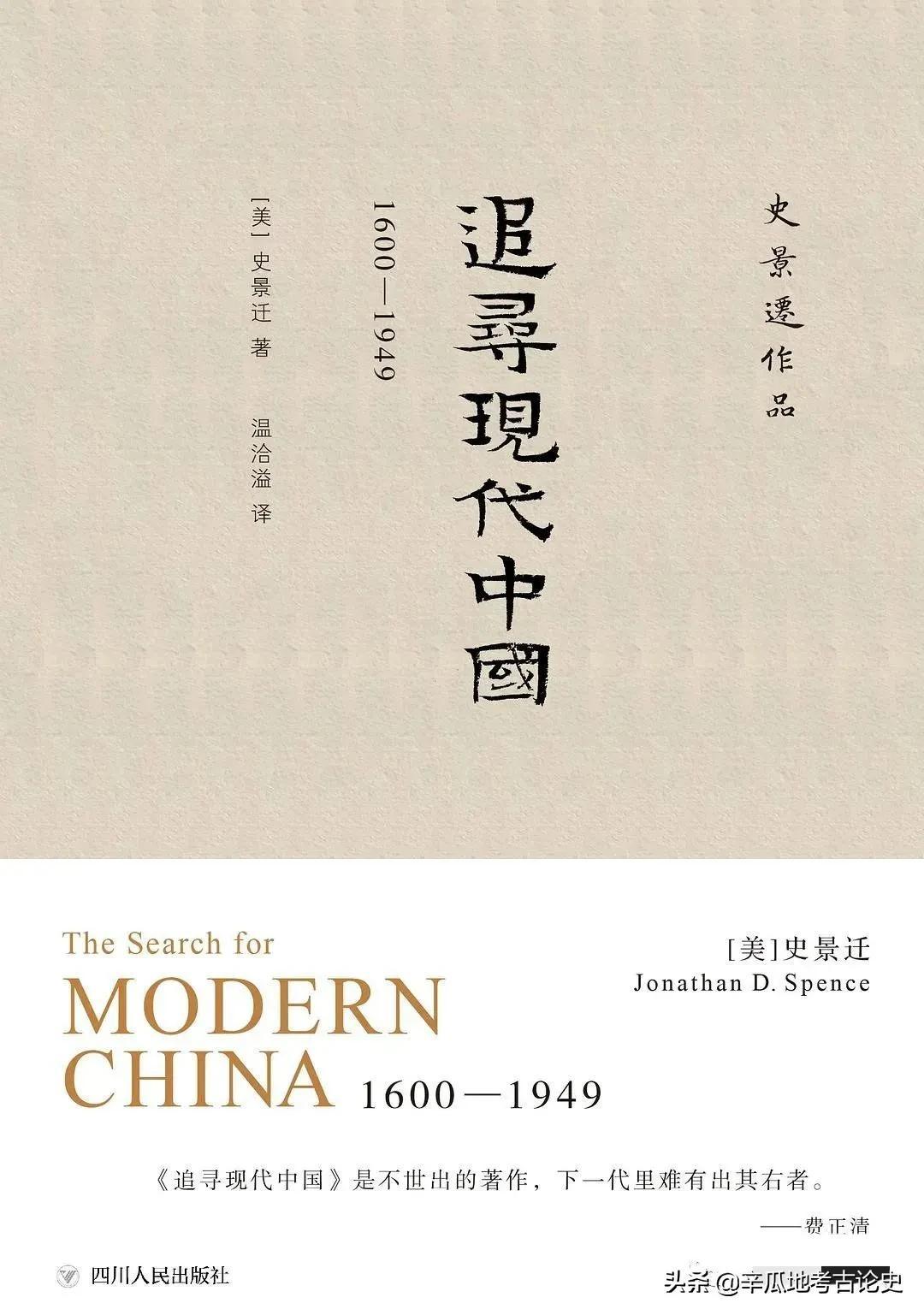柴尔德与苏联考古学
#以书之名#1935年,柴尔德对苏联进行了短暂访问,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带有同情但不无批评地谈到他的访问所见,而1936年在美国,他则毫不犹豫地把苏联形容为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他访问苏联的一个目的看来是要收集有关当时苏联史前研究的信息,并设法与苏联同行建立联系,以便使他能够跟上苏联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有关苏联的考古材料,对于他更新欧洲史前史的综述以及设法确定印欧语系人群的起源地至关重要。后面这项研究一直是他与科西纳和德国国家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内容。

在苏联的时候,他获得了苏联考古学家的一些最新发表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克鲁格洛夫和波德加耶茨基对东欧草原氏族社会的研究之作,还有克里切夫斯基研究中欧战斧文化和较晚的特里波列文化,以及特列季亚科夫专门研究俄国和斯拉夫考古学的书籍。没有证据表明,在1940年代之前他受到过这些研究内容的特别影响。当他“重新”阅读它们时,就将其中比较有趣的解释用到他自己的研究中去。不过,他坦言这次访问从苏联考古学家那里学到了他们是如何“不求助于无法论证的外来因素解释某些史前文化发展” 。
柴尔德访问苏联时,苏联考古学刚经历了五年的取向改变,以便与共产党政策更加保持一致。1929年,许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允许进行相对自由研究的考古学家被指控为反动分子,试图倒退回去,并脱离生产人工制品的社会来孤立研究它们,以逃避社会主义建设。前一指控特别针对那些遵循奥斯卡·蒙特柳斯和约瑟夫·德谢莱特类型学方法的学者。为了纠正这个问题,考古学的名称被禁止,考古研究被归入物质文化史,后来被归入前资本主义社会史研究的名下。在国家(原俄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院里,考古学受尼古拉·马尔的领导,他坚持认为,所有的语言变化反映了社会而非族群的历史。在1950年受斯大林批判之前,马尔的思想一直主导着苏联的社会科学。
苏联考古学家的主要工作,是从产生考古材料的社会来研究它们。考古学家被要求抛弃物质文化是沿某些内在逻辑发展,因此与社会无关的想法。相反,技术被说成是因社会内部矛盾而发展起来的。这要求对任何文化变迁的解释中,主要强调社会发展。技术时代的标准序列被一条单线的社会阶段序列所取代,每个时代以特定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为代表。这些阶段被用前氏族社会、氏族或异教徒社会(其本身又分为形成中的、母系的、父系的和瓦解等亚阶段)和阶级社会(也做了进一步细分)来表示。迁移被排除在考古材料变化的解释模式之外,重点放在了平行的独立发展上。在这个问题上,马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否认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必然体现了这些语言群之间的历史关系。比如可以这样说,克里米亚哥特人不是德国人,只是类似德国人的当地部落混合而成的一个群体而已。信奉平行演化,苏联考古学非常强调利用民族志的类比就并不令人意外了。他们在发掘中日益强调对营地遗址和作坊的关注,强调这要比迄那时为止考古学家所倾心的富墓更能说明普通人的生活。
不过,在1930年到1935年,理论和范式的构建要比发掘更加受到重视。1935年,芬兰考古学家塔尔格伦也访问了苏联。他一直关注苏联考古学,而他主编的《欧亚大陆古物》(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杂志就是传播有关苏联考古学信息以及发表苏联学者论文的一个平台。因此,塔尔格伦要比柴尔德更加了解苏联考古学的情况。回到芬兰后,塔尔格伦在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报告,介绍了1930年到1935年发生的对苏联考古学家的政治迫害。由于这篇报道,他再也无法访问苏联。
各种英文出版物对塔尔格伦的报告进行了讨论。1936年,格拉厄姆·克拉克在《史前学会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里对此做了总结,1940年根据这篇文章写成的一篇社论登在了《自然》杂志上。在回应《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柴尔德谴责了塔尔格伦所指控的疯狂举措,但是对自塔尔格伦访问以来苏联考古学出现的某些颇有希望的趋势予以了关注。他特别指出了对发掘有一种新的重视,创办了一本令人尊敬的新杂志《苏联考古学》(Sovetskaya Arkheologiya),以及对材料阐释的一种较为包容的态度,包括对迁移概念谨慎的复苏。柴尔德承认,苏联考古学有它的缺陷,但是声称,这些缺陷不应被作为西方考古学家与苏联同行中断来往的一种借口。他的立场反映了他想与苏联考古学家交流信息的愿望,以及他坚持反对在任何地方或对任何课题设置不利于学术交流的障碍。
而且,柴尔德认为在苏联考古学中发生了一种变化是正确的。1935年,前五年的那些好战的文献被宣布过时,技术专长被给予新的重视。苏联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焕然一新。在苏联考古学中,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继续发挥着一种主要作用,但是考古学家再次被允许讨论技术阶段序列,并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传播与迁移。另外,1930年代晚期的国际危机时期,苏联考古学发起了对斯拉夫考古学问题的强力担当,这导致采纳某些德国考古学的分析程序为苏联所用。并不奇怪的是,柴尔德后来认为1930年到1935年这段时期的苏联考古学总体上要比后来俄国人所创造的所有内容对他史前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有更大的启发。
在他的《回顾》一文中,柴尔德声称,他对苏联的首次访问令他采纳了“蒙昧”“野蛮”“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并将它们用于考古学的时期或阶段,这些时期或阶段又被他的两次革命所划分。然而,柴尔德过去曾非正式地应用过这些术语,一直要到1942年出版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里,他才开始以上述的方式系统地应用它们。也一直要到那时,他才将两次革命指称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
恩格斯从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那里借鉴了“蒙昧”、“野蛮”和“文明”的术语。这些术语早于摩尔根,并以几乎与现在相同的含义在18世纪被威廉·罗伯逊和其他苏格兰学者所采用。在19世纪,这些术语在人类学中变得十分流行。柴尔德是在阅读恩格斯文章之后了解到摩尔根的,但是在写给布雷德伍德的信中,他坦诚自己起先认为这两人的文章极其陈旧。只是当他看到俄国人如何“应用该一般性理论”,他才发现他们的研究“对于许多方面助益良多”。恩格斯与摩尔根不同,他强调蒙昧与野蛮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经济的,即食物采集与食物生产之间的不同。柴尔德认可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与他自己的想法一致。他也认为恩格斯的原创性贡献总体上说要优于他从摩尔根那里借鉴的材料,“因为恩格斯真正了解德国历史和考古学的许多内容”。
大概在访问苏联的同时,他被要求为一本计划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撰写史前期和早期东方的章节。这令他要阅读大量的有关早期科学的文章,特别是以研究古代精确科学闻名的奥托·纽格鲍尔(Otto Neugebauer)的文章。后来柴尔德声称,这些研究令他进一步偏离史前史的族群政治观,而采纳一种较为明确的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考古材料。他开始视工具为科学知识以及社会传统的体现,并且是应对大自然的一种手段。他也开始坚持认为,手工艺学问对现代科学的贡献与占星术家或炼金术士的推理相同。柴尔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同侪本杰明·法灵顿(Benjamin Farrington)的想法如出一辙。
 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
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