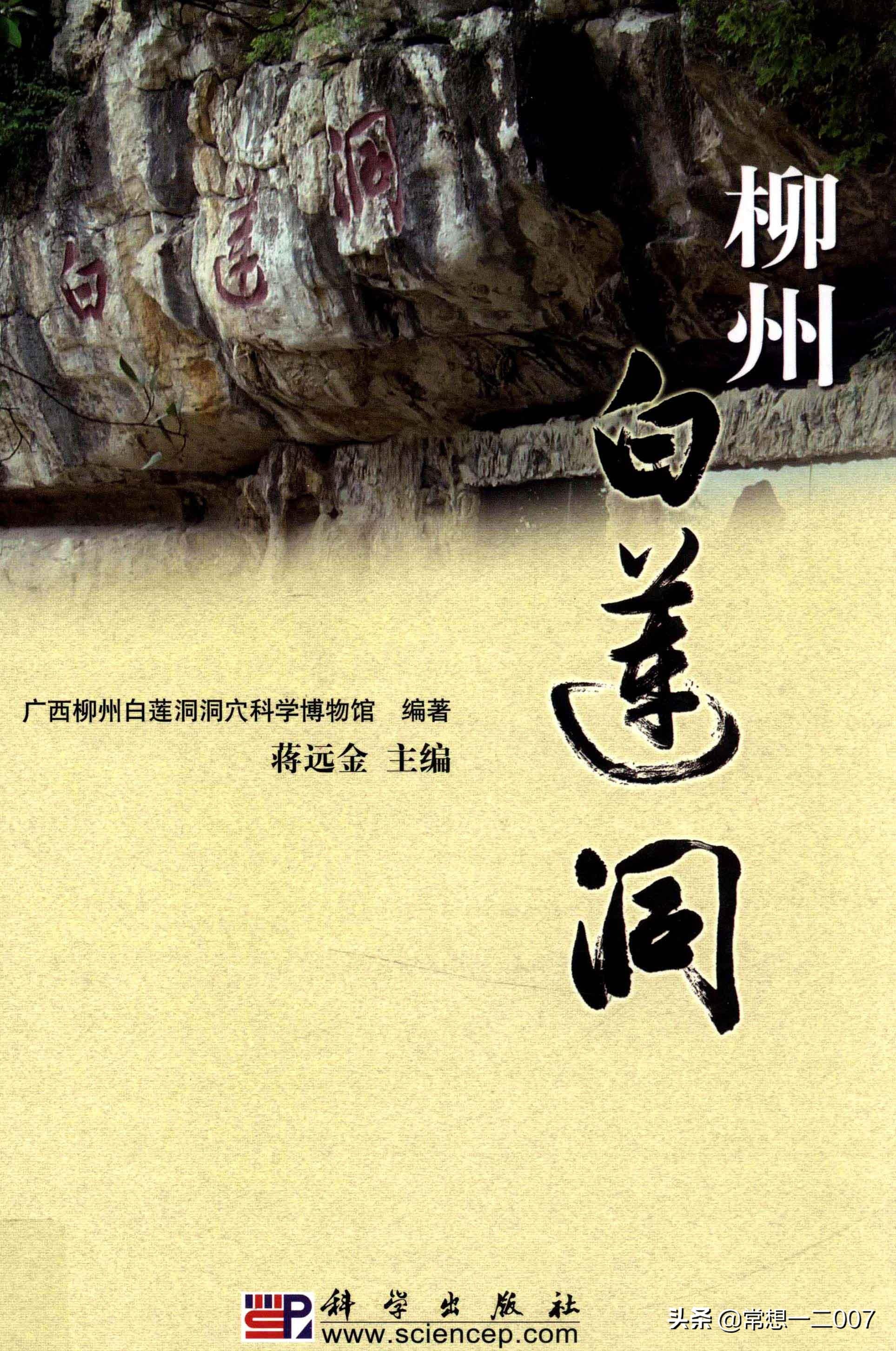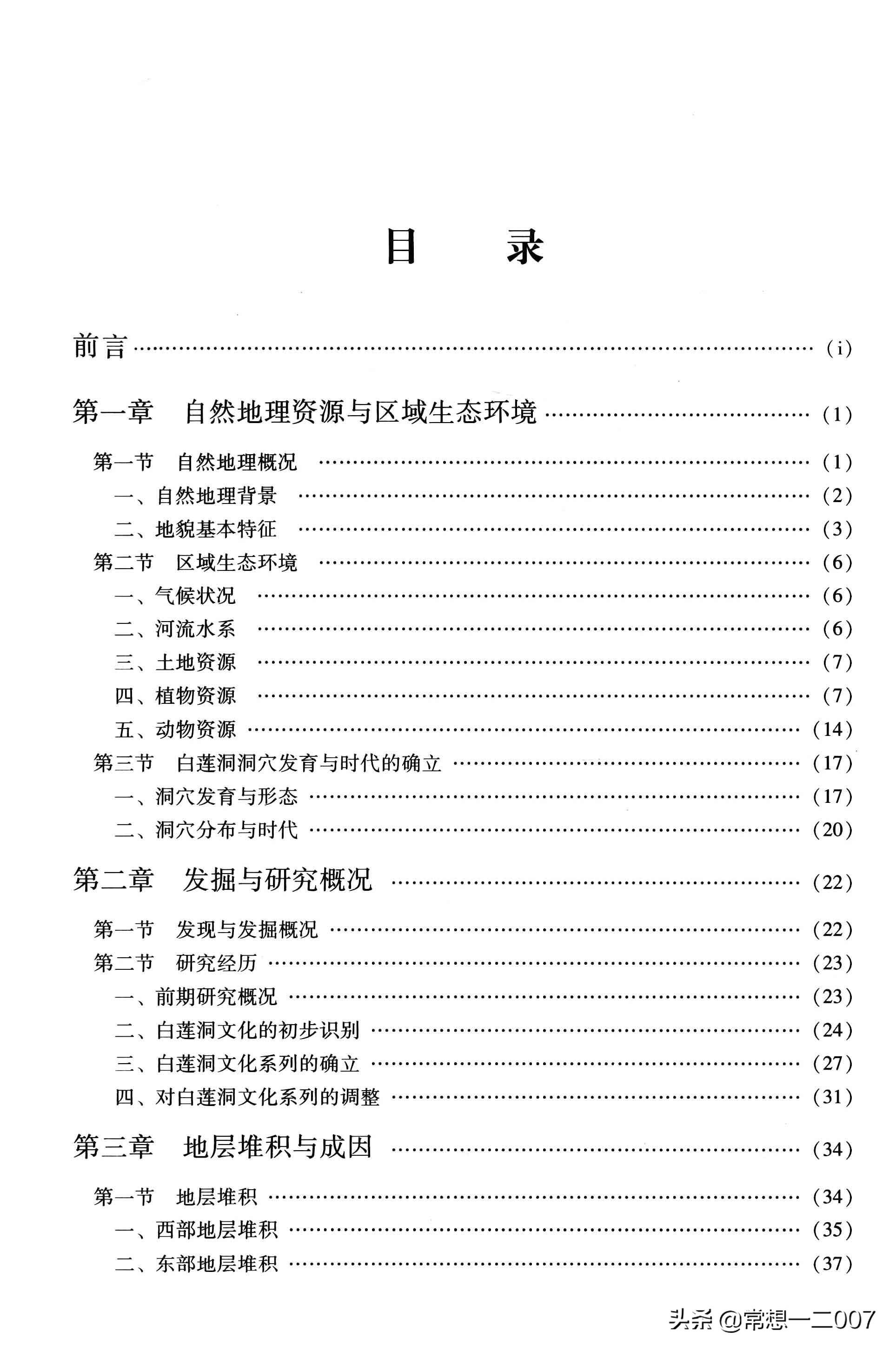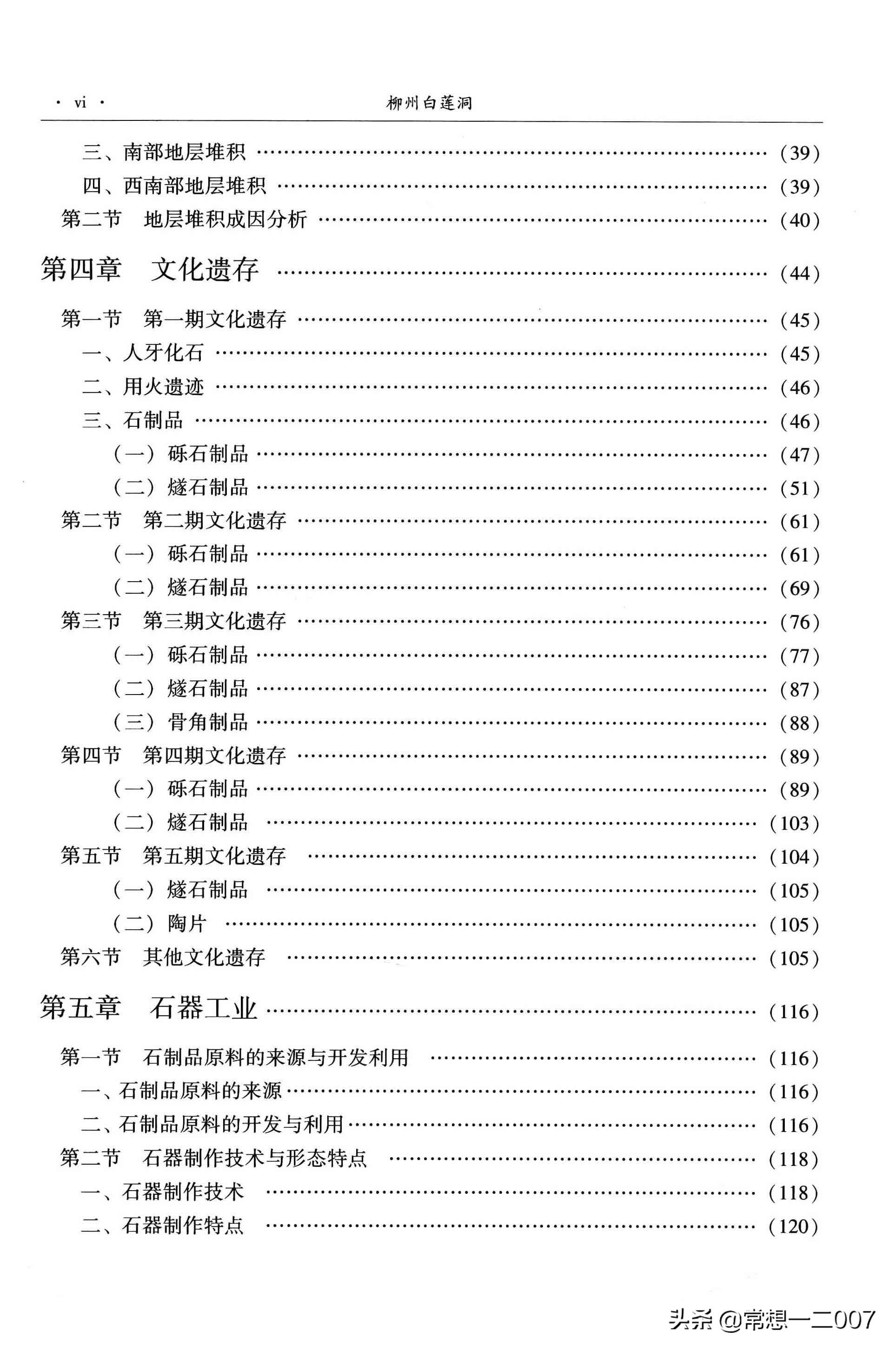“三星堆最大金面具”发掘经过大揭秘
半张惊世金面具,刚发现时像个揉皱的纸团
2020年12月11日,是四川大学考古队正式入驻三星堆考古方舱、开始发掘工作的日子。这一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遗存坑,编号为K3~K8,排在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头两个坑(K1和K2)后面。
其中,K3、K4和K8都各自独占一个考古方舱,而K5、K6和K7三个坑被罩在了同一个方舱里——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气质,也从一开始就始终伴随了这个舱内的考古发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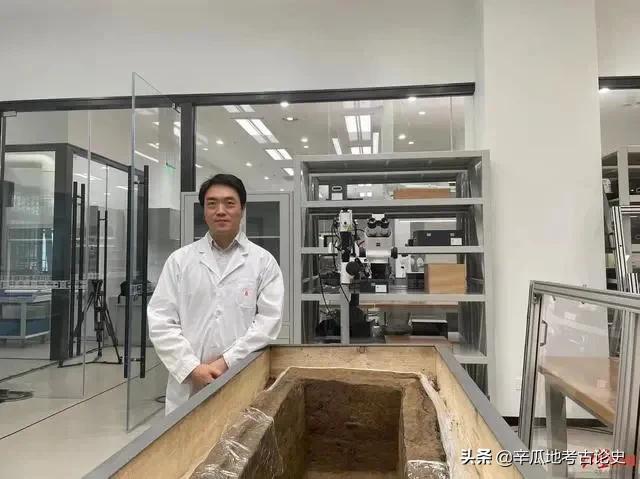 黎海超(他身旁就是6号坑的那只木箱)
黎海超(他身旁就是6号坑的那只木箱)
“这三个坑发掘的相对难度较大,首先6号和7号有一个打破关系——年代更晚的6号坑破坏了7号坑的一部分,是唯一一组有明确年代早晚关系的祭祀坑。”黎海超说,“5号坑虽然最小,但里面的东西最细碎,组合关系最复杂,清理难度也最大。”
更令人头大的是,在那个年代较晚的6号坑里,三星堆先民古蜀人埋下了一只木箱。木质早已炭化,全靠箱内填满的泥土支撑形状,而这填土的木箱不仅极重,还很脆弱,考古人员没有任何可能赤手空拳将它抬出坑。
两个坑仿佛两只纠缠的手,其中一只手里还握着块易碎品。在将两只手分开的过程中,稍有不慎,手里的东西就毁了。
考古发掘的规矩是:先发掘年代较晚的遗迹遗址,再发掘年代较早的。这一顺序也很自然地体现在常见的地层叠压上——越接近现代的遗存,离地表就越近,从上往下慢慢来。
“5号坑和6号坑是差不多同时开始挖的。2021年1月5日,我们在5号坑里发现了那半张金面具。”黎海超回忆说,“因为5号坑的器物普遍比较小和细碎。刚露头的时候以为也是个小件金器。”
 尚在泥土中的金面具
尚在泥土中的金面具
面具被发现的位置位于5号坑的中间偏西南方向一点,随着考古工作人员细致小心地清理掉周围泥土,他们渐渐发现这是一块较大的金箔。“金箔”最初出土的状态,颇似金沙遗址著名的太阳神鸟——像个揉皱的纸团一样,完全被压扁在泥土里,看不出真正形状。“但在逐步清理的过程中能辨认出鼻子、耳朵的形状,推测很可能是件金面具,大家就都很振奋了。”黎海超说。
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左右,重约280克。据此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500克——比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更大更重,也比目前我国出土的商代最重金器——三星堆金杖(463克)还要重。
 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金面具对比
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金面具对比
“这件金面具是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早出现并且最重要的器物之一,也是迄今发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金面具。”黎海超说。“5号坑下面应该还有大件的金器,新的发现仍有可能。”如果在后续的发掘中,能够出土另外半张面具,那么,这件完整的黄金大面具将超过金杖,成为目前我国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但这些发现多半都不能在现场完成:一些圆形金箔几乎是等距离分布在坑内,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组合关系,这种明显的规律在6个坑中显得极为特别。为了最大程度保持住这些小金片现有的分布状态,显然不能一片一片单独提取了,“所以专家们的建议是整体切割(连泥土带器物金片),拿到实验室里做进一步清理和研究。”
 修复后的半张大金面具
修复后的半张大金面具
镜头下的考古
脆弱的木箱如何走出“发掘困难舱”?
与以往和常规的绝大多数田野考古不同,身为“超级网红”的三星堆,在本轮考古发掘过程中,除了直播之外,平时也全程暴露在各种各样的镜头和目光之下。
最热闹的时候,在考古大棚进进出出的人群,甚至可以用“川流不息”来形容——前来观摩交流的考古界同行、各大高校考古文博专业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占据了其中相当一部分。
包括在考古方舱里面,也随时都有跟拍的镜头守在坑边——央视和四川电视台都要全程拍摄,未来利用这些宝贵素材剪辑成纪录片。
纪录片也需要情节,为此,这些常驻摄影师除了客观记录之外,也随时在寻找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而他们不约而同都很“青睐”黎海超所负责的三号舱。“其他坑基本都是按部就班、平稳推进,只有我们这个舱里,从头到尾贯穿了各种困难。”
 5号坑里的细碎器物和小圆金箔
5号坑里的细碎器物和小圆金箔
最先开挖的两个坑都有各自的“独门难题”——5号坑的细碎金片不敢轻易扰动,就连清理工作都只能用最细的小竹签,像挑牙缝一样一点一滴做工作。
6号坑则是“一箱当关 万夫难开”,要保护无比脆弱的木箱,同时还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坑壁原状,不能说为了方便提取而随意扩挖。
“我们就是一边尝试一边反复修改方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保护遗迹和遗物之间寻找平衡点。”黎海超说,“6号坑的木箱一天提取不出去,7号坑就一天没办法挖。眼睁睁看着其他坑一层层下去,说心里不着急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止我们自己发愁,因为几个舱都是打通的,经常隔壁舱的人走过来看着,也忍不住替我们发愁……”
他们一度考虑过拆掉一部分大棚,把木箱吊出去,但这样做实在太过折腾。最后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方式,依然够麻烦——舱内搭起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地上铺好钢管,把套好保护套的木箱慢慢吊出坑,轻轻放在钢管上,像当年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时运送石料一样,通过隔壁8号舱的门一步步推出去。
黎海超清楚地记得,那天当这只沉重的木箱终于“踏出”了8号舱的门、落到了舱外地面上的时候,他感觉心里面一块大石头也随之落了地。“花了半年多时间,这才终于和其他舱站到一条起跑线上,可以放手继续挖7号坑了。”
 6号坑木箱“走出”考古舱
6号坑木箱“走出”考古舱
7号坑对待他们也并没有很客气: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象牙盘根错节,连透过象牙间的缝隙、窥探一下更深处的器物都做不到,只能耐心地一根根往外提。“到目前为止,前后提出来231根象牙,各种不同类型都有——大的、小的,有些带有切割痕迹,有些被烧过,有些没被烧过。”
目前7号坑内最令黎海超好奇的器物之一,是今年9月直播时就露了头但迄今还未提取出来的那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可以肯定它没什么实用功能”——针对一些网友说这个网格像烧烤架的玩笑话——“应该是和古蜀人的祭祀体系有关,但目前还很难推测它在祭祀体系里具体是承担怎样的功能。”黎海超说。“它应该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奇特的一件青铜器了,以前从没见过哪一件和它稍有相似的。”
 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
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
青铜面具方孔之谜
古蜀人比现代人想象的走得更远
李白的名篇《蜀道难》把四川盆地形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闭塞之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事实上,古蜀人与外界的交流,无论是密切程度还是所跨越的地理距离,均远超大多数现代人的想象。“在商晚期,整个长江流域已经通过水路连接成了一个密切的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点都与北方的商王朝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黎海超说,“三星堆所展示出的交流范围还要超出这一网络——有着良渚文化典型因素的玉琮,来自热带海洋的贝壳……甚至三星堆的铜器,有很多可能也并非是在当地生产。”
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三星堆博物馆的很多青铜面具,额头正中有一个方孔。“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些方孔的形态都不太一致:有的方孔非常规整,是与面具同时一次性铸造形成的;但也有一些方孔明显地是后期切割出来的。甚至还有个别面具上的划痕显示:或许有工匠试图切割,但最终放弃了加工。”
为什么三星堆的先民要费这么大劲儿进行“后期加工”呢?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很可能制作这些面具的人不是三星堆的人,因为疏忽而忘记留这个孔。三星堆的人拿到之后,为了要使用而不得不进行二次加工。”黎海超说,“因此有一部分铜器可能是三星堆先民们订制的产品,并非在当地生产,且来源也不单一。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一部分青铜器很可能是三星堆的先民们自己制作的,他们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
 黎海超工作照
黎海超工作照
黎海超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是“资源与社会视角下的商周铜器”。在他眼中,三星堆的青铜器便是古蜀与周边世界之密切联系的一个缩影。“这些铜器哪些是三星堆自己生产的?哪些是其他区域生产的?其他区域的人为什么要为三星堆制作这样一些铜器?我希望通过研究这些问题,能够看到三星堆与同时期周边世界形成的这种巨大的交流网络,也能更好地去理解三星堆在古蜀文明发展脉络中的意义和作用。”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