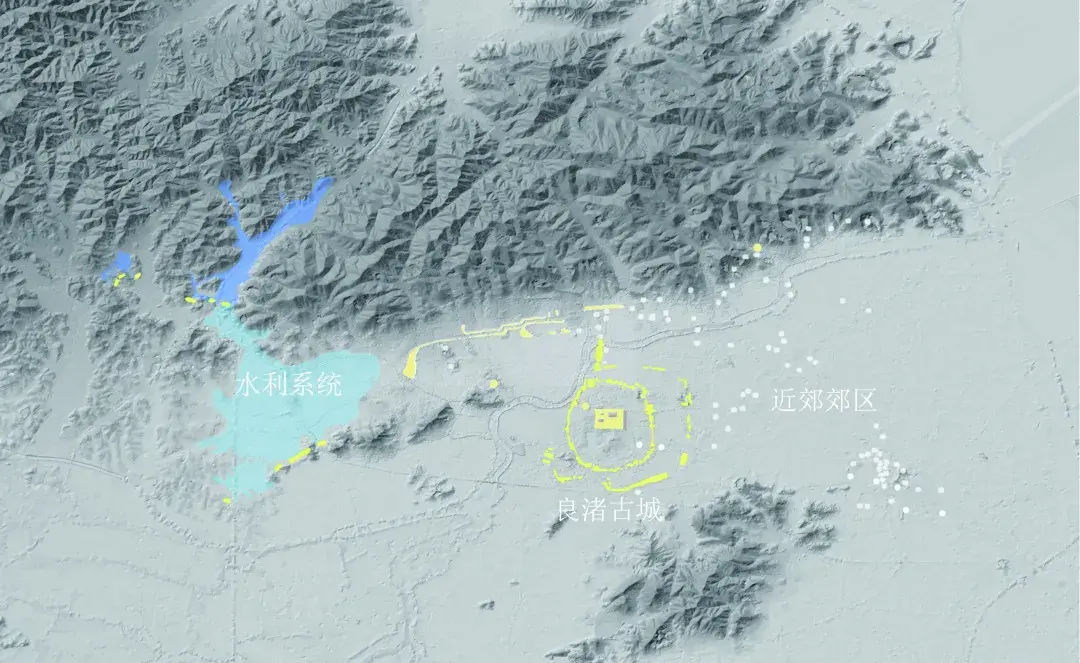荐书 |《镇江孙家村遗址发掘报告》:一座土墩的生长史和一个社会的生活史
孙家村遗址是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长三角地区、宁镇地区商周时期考古的重大收获。最近喜得新出版的发掘报告。以下仅就本人拜读发掘报告后的些许想法略作阐发。

编著:镇江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大城市学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定价:460.00元
孙家村遗址的发掘于2019年结束。仅仅过三年,发掘报告即正式刊布,实属神速。该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发掘成果,特别是发表了大量日常陶器,为完善和细化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在我看来,这次发掘的更大意义还在于融入了中国考古学转型期的发展洪流,为我们从考古学上认识宁镇地区的两周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曾有学者指出,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界,中国考古学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对于孙家村遗址所在的宁镇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来讲,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然构建起了本区域的基本文化谱系和序列。如何进一步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更为全面系统地认识本区域两周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成为考古工作者必须直面的。进入新世纪以后,长江下游的商周时期考古工作开始关注以城址为代表的遗址类遗存的工作,先后在一系列城址开展工作,包括无锡阖闾城、镇江葛城、江阴佘城(花山)、姜堰天目山城和苏州木渎古城等,最近还在无锡鸿山越墓附近发现吴家浜城址。这些城址的工作为我们勾勒出本区域商周时期宏大的历史图景,极大地深化了对本区域社会发展历程的认识。但此类研究失之于大,缺乏对历史细部的认识和了解,需要以一处基层聚落遗址为捉手,进行具体而微的观察。孙家村遗址的发掘恰恰补足了这一缺环。
首先,这次发掘促进了对本区域两周时期聚落形态的新认识。上世纪50年代尹焕章等先生通过在宁镇地区的调查,确认古代遗址位于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台(土墩)之上,并称之为“台形遗址”。以往发掘工作都仅仅关注到土台本体的堆积情况,而对土台的具体布局探索不足。通过这次发掘,确认了孙家村遗址由中间的土台和周边的环壕两部分组成,土台边缘有土垣环绕的基本布局。以此认识为线索,考古队在周边地区展开的调查中发现多处类似布局的遗址:南神墩遗址、东巨遗址、谢家神墩遗址台地边缘有土垣,外侧有壕沟;断山墩、癞鼋墩遗址和文昌阁遗址在外侧发现有壕沟;东庵前遗址的台地虽被破坏,但钻探显示周边仍有壕沟;锣鼓山遗址和乌龟墩外围有洼下的条形地,可能也是壕沟的孑遗。这些表明,此类带有环壕的土台是本地基本的遗址形态。此种形态的遗址并非宁镇地区所独有,在南方的广大区域均有发现。江西抚河流域调查发现的遗址中约四分之一的是“环壕类遗址”。其一般由中部台地、壕沟及外围台地构成,中部台地与壕沟有较大的高差,多为2~3米,亦有高差达5、6米者,也是被围壕所环绕的台形遗址。安徽霍邱堰台遗址处于江淮之间,外部有内外两周围壕,中间为一处高约2米的土台。太湖三板桥遗址由东、西墩以及北墩三个土墩构成,其中在北墩南侧有一段东西向壕沟,与东西两侧的自然河道相接,构成了三面闭合的环壕。此外在江汉平原史前时期也发现很多带环壕和城垣的遗址。此种带围壕的遗址可能是南方地区早期遗址的常见形态。“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如果遗址位于平地上,潮湿的环境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如果居于高处,则距水太远,生活不便。平地上的遗址通过围壕和土垣等设施将水阻隔开,并不断向中间覆土加高确保居住区域的高爽和宜居,同时也保障了日常生活用水的来源,实现了疏水和亲水的完美结合。孙家村遗址除了外围宽约14米的围沟,还有高达2.3米的土垣围绕,各类遗迹单位均分布在土垣内,足以抵御水患。在后期的使用中,中间逐步垫土升高,最终形成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台。此种形态的遗址是对本地湿润环境适应和改造的产物,是南方地区的主流遗址形态。
其次,孙家村遗址的科学发掘帮助我们科学认识台型遗址的形成过程。孙家村遗址是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晚期逐步形成的高约4.5米的土台。在漫长的使用期内,不断覆土加高,可以想见有着复杂的“生长”过程。此外,遗址在各个时期内是否有布局结构的变动?聚落的布局结构及变动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组织?这是聚落考古最为关心的问题。这就需要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下,以探索土墩布局、结构及演变过程为学术目标,摆脱以往以遗物为首要关注点的学术惯性。通读发掘报告,明显可以感觉到发掘者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在明确的学术目的指引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工作,探索土墩的生长史。平面上,对土墩采取了全面发掘的方式。孙家村遗址的整体布方面积约4650平方米,除了对下部围壕的解剖外,基本将约5000平方米的墩顶完全打开,从而确保了对遗址整体平面布局的认识;纵向上,通过局部清理到底,结合探沟等的发掘,既保护上部重要遗迹现象,又充分认识了土墩的基本堆积。两相结合,即使没有全部发掘土墩,也大体构建出土墩“生长史”。
发掘者依托已有的分期结果,将遗址分为七个阶段,并大体描绘出各个时期遗址的布局情况及发展演变过程。在遗址的第一阶段,仅是在平地上有零星建筑存在;到第二阶段,遗址进入了迅速发展期,外围出现围壕和土垣等防御性设施,各类遗迹单位分布在土垣内,遗址整体状况大体成形。以后的各个阶段,人类的活动集中在土垣内,有着土台(建筑基址)、灰坑、道路、窑址、灶坑等各类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垣内遗迹也不断堆土改建,渐次升高,形成了最终的聚落格局。孙家村遗址的基本遗迹单位是有着四个柱洞的小土台。聚落的基本格局是多个小土台(建筑)再围绕着中间的大土台(土台6)分布。这些土台是当时的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数有着很强的“传承性”,表现为“建筑使用一段时间后堆土加高,成为新的建筑,但位置基本保持不变”。对于这一现象,发掘者在遗迹编号中特意用同一编号下的A、B、C、D等来彰显此种传承:如土台44,在第三阶段的建筑编号为土台44F,第四阶段加以堆筑,编号为土台44E,第五阶段有两次堆筑,分别编号为土台44D、土台44C, 第六阶段的两次堆筑分别编号为土台44B、土台44A,直至第七阶段的完全废弃。由这一编号体系使我们较为容易地把握遗址的延续使用情况,对于系统认识土墩的布局大有帮助。可以想见,如果各阶段建筑各自编号的话,势必彻底割裂开此延续性,使研究者陷于在平面图上不断查对土台位置的窘境,无从理解土墩的生长过程。
资料整理后的资料发表工作并非简单地罗列,既要充分科学完整地体现发掘成果,又不能失之繁琐,成为一本流水账。纵观《发掘报告》,基于宁镇地区两周时期的较为完善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资料整理者不再拘泥于遗存时代的划定,而是以土墩的“成长史”为主轴,按照时间轴度来串联起所有发掘资料。《发掘报告》将遗址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晚期的使用阶段分为四期七段,并根据不同的布局情况详略得当地介绍土墩的形成过程。对于遗迹数量相对较少,但布局和遗迹结构形式变化较大的第一至第四阶段逐层加以介绍;为避免繁琐,将布局情况已经基本固定、遗迹结构形式变化较小的第五至第七阶段则合并介绍。此外在“遗迹列表”中详细列上各土台和其他遗迹的所处时段和层位关系,结合各阶段的“遗迹平面分布示意图”等,方便后期的梳理和研究。这些工作构建起了纸面上的土墩“生长史”。
土墩是逐步向上堆积形成的。考古发掘就是对这一过程的逆向操作,以复原土墩由低到高的“生长”形成过程。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逆堆积”过程,需要采用更为合适的发掘方法来立体地发掘和复原土墩的形成过程。孙家村遗址的发掘采取的是传统的探方法,各探方同步逐层向下清理,中间留有隔梁来比对层位关系。这一方法相对较为保守,且使整个发掘场面较为零碎,难以窥见遗址的全貌。在发表的土台平面图上,时不时中间有一道隔梁横贯,或者小半部分在隔梁下。《发掘报告》中将土墩内的层位堆积分为东西两区分别介绍,虽然“东、西部地层堆积相近”,但“细节层次略有差别”。然后仅用两个探方(T0806、T1109)的剖面来说明整体堆积状况,略显单薄。如果有一个贯穿整个土墩的大十字剖面,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土墩的生长过程。
现在土墩墓的发掘中已经普遍采用了十字隔梁法,采用类似“剥洋葱”的方法,同步清理各象限内的堆积,同步出露同一层位下的堆积。对于较大的土墩可以采用多留几道隔梁,如“ ╪”形、“丰”形,来控制地层。在清理掉某一层面时,可以在留下关键柱的前提下打掉隔梁,全面了解某一层位下的布局情况。遇到较为重要或者完整的遗迹单位,可以随时打掉隔梁,确保遗迹单位的完整。这一发掘方式在现今高精度测绘技术、三维建模技术和无人机的技术辅助下,应当是不难完成的。在发掘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堆积层次的统一划分,以整个遗址生长过程中大层面为基准来划分层次,或许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对于孙家村遗址,最为引发关注的是与铜器生产相关的遗存。但翻检报告,与铸铜流程相关的遗迹包括六座窑址和两处烧灼坑。发掘者仅是推测可能与铸铜作坊有关,但并没有提供相关依据。报告附录中关于青铜器的检测分析研究,也仅仅是对铜器、铜渣、陶范、泥芯以及坩埚等熔铜遗物进行的检测,并未对这些遗迹在铜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加以分析。出土的铸铜相关遗物仅有29件,包括陶范、石范、鼓风嘴和坩埚残片等。这些发现尚无法构建起完整的铸铜工艺操作链,对其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等还是无从复原。遗址内发现的19块陶范,2块石范,可分辨出的产品仅有戈2件、剑1件,其他难以分辨器型的范腔大多扁平,当是两面合范的简单器物,未见有容器范。大港—谏壁墓葬群内发现的大量精美铜器,当非此遗址能够生产的,孙家村遗址如此大体量的遗址,这些铸铜遗存属实少了些,因此当非一座专门的铜器生产作坊遗址。因此,发掘者提到孙家村遗址居民从事多项生产活动,除了铸铜外,还包括农业种植、纺织和捕鱼等。多业生产或许就是本地一个小村落的基本业态和生活状况。
孙家村遗址的铸铜遗存也反映了当时铜器生产技术的下沉,一般性聚落能够从事较为简单的铜器生产。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手工业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一般聚落内是如何因陋就简进行铸铜活动的?具体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有哪些遗迹是与铸铜活动相关?铸铜技术是什么时候开始下沉的?遗址内出土的铸铜遗物主要集中在上部的第五到第七阶段,在较早的第四阶段仅出土一件陶范。这或许与遗址下部发掘面积较小有关,也提示我们从更早的层位中去寻找证据。
孙家村遗址的考古工作由最先的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转向主动性发掘,但发掘者秉持着考古工作的学术自觉,通过细致的发掘和精心的整理为我们揭开了两周时期宁镇地区社会状况的一个小角,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对于此类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孙家村遗址并非孤立存在,附近有谢家神墩、南神墩、东巨、断山墩、东庵前等一批遗址,不远处也有大港—谏壁的高级墓葬群,构成一处规模宏大的遗址群。只有将孙家村遗址置于聚落群中加以考察,才能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作者:唐锦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 张怡 实习编辑 | 胡博雅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0002
- 0000
- 0000
- 0001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