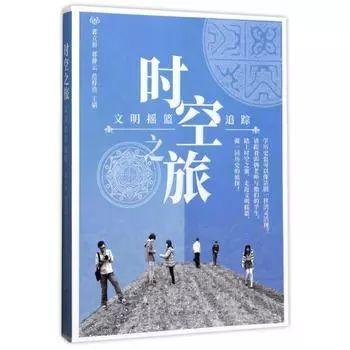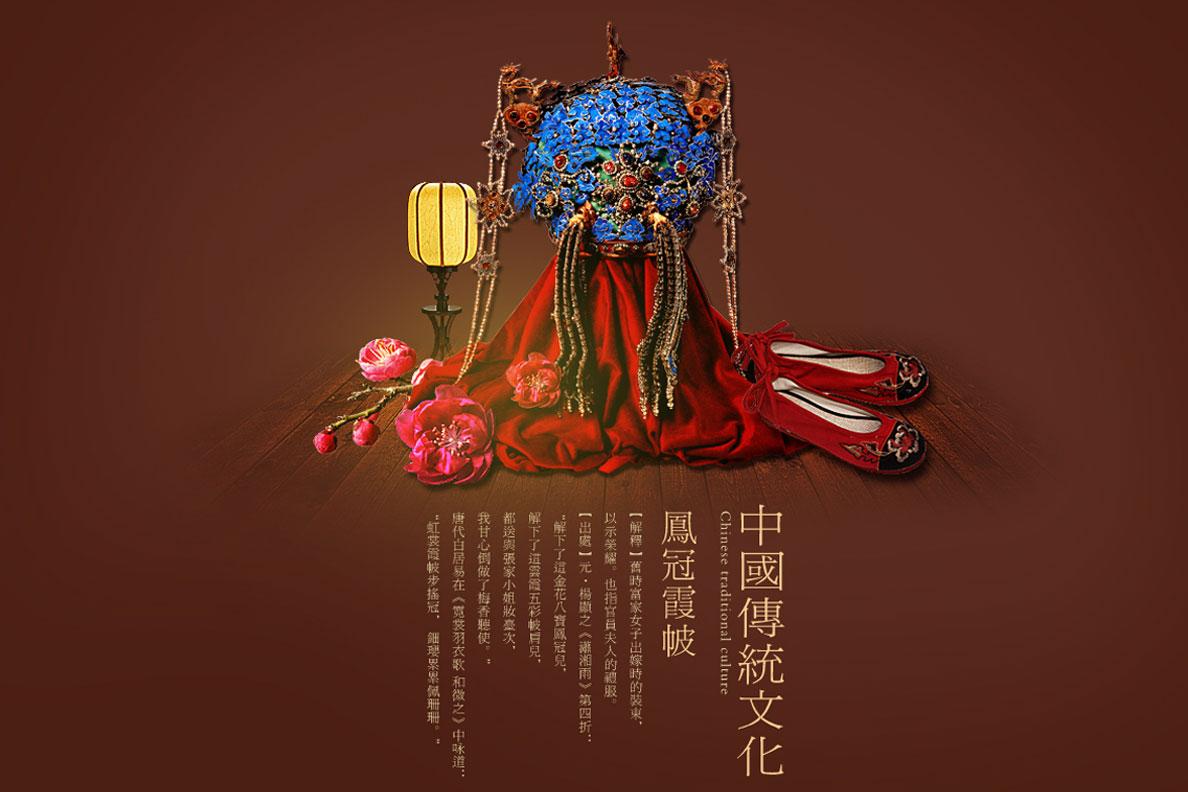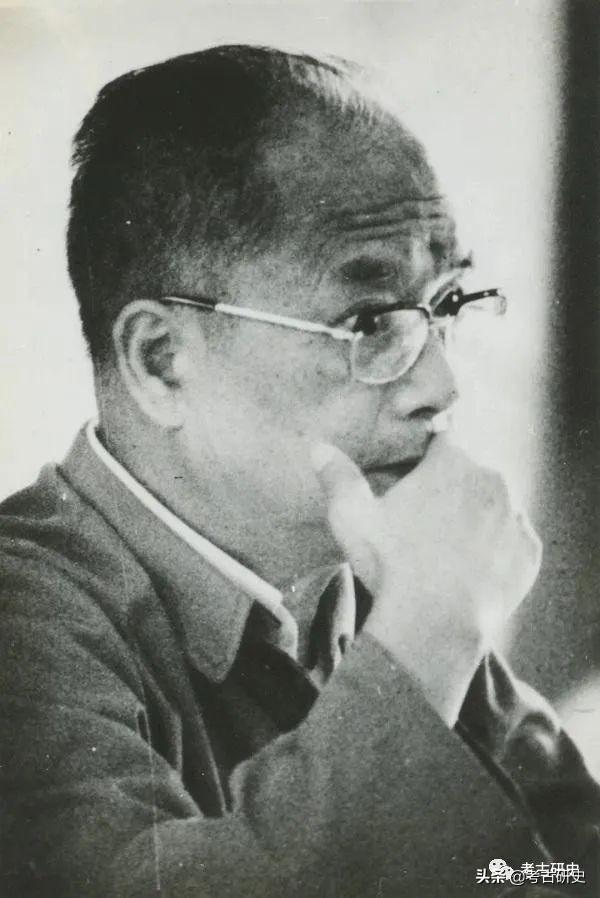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
前几年我应邀在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后经友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7期上,标题为《走出疑古时代》。1995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的小书,书名便移用了这个题目。对于有关问题,我本已没有新的话可说,只是发言中引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提法,未能详细说明,有些遗憾。这里想略谈几点,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
我所引冯友兰先生的话,见于30年代后期他为《古史辨》第六册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先生说: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 ;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冯先生的这段话,由于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作为补白的“语林”摘录了,[1]已经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来,学者们谈起冯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总是当作三个阶段来理解的,甚至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辩证法的正、反、合。重看上面引的有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吟味冯先生所讲,信古一派将归消灭,显然已属过去;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需,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作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
“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而“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一思潮及其影响提出来的。
疑古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经把这一点反复说明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好几股疑古的风气,各有代表的学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袭来说,确有一贯的脉络。但是,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2]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集宋学大成的朱子,便是富于这种精神的,其流风遗韵直至明代。
疑古之风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学,而于辨伪书方面则继续了宋人的统绪。他们所辨古书,每每同反对宋学有关。例如阎若璩等指摘古文《尚书》,宋儒津津乐道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便失了依据;胡渭等批评图洛书,也是针对周敦颐以至朱子的学说。清人崇尚门户,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刘逢禄作《左氏春秋疏证》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趋向,在龚自珍学说中已见其端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3]这一学派中有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著《礼经通论》,等等,都主张辨伪,梁氏书中已有详述。至于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书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受廖平影响,“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4]我们却不能说廖氏也有像康有为那样的变法维新立场。由此可见,不可以把当时的今文学派同变法维新完全等同起来。
康有为的著作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有颇大影响,可是两者的思想性质实有根本的不同。康有为和其他今文经学家一样,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后来力倡建立孔教,而20年代的疑古思潮则与此相反。顾颉刚先生于1924年在一则笔记中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地辩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5] 这与康有为的孔教刚好对立,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我曾说“今文学派作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6]即指此而言。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确实把信古打倒了。凡细读过七册《古史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
《古史辨》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随之一个阶段的论争主要是环绕古史问题。后来讨论的范围渐趋扩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古书的真伪问题更是突出。现在看来,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正是在古书的辨伪问题上。冯友兰先生专门提出的史料审查,也即这个问题。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7]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中,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冯友兰先生所讲融会贯通释古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我们看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观点和考古发现,而这两者都可溯源到20年代。
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先生早年治哲学、文学,1911年冬东渡日本后始转攻经史小学。他研究经学,既不是康有为那样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样的古文家。实际上,他对于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并非漠视,而是做了很多切实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916年开始研究汉魏石经,尤其注意魏石经的古文,这一工作随着石经陆续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还在继续。[8] 也是在1916年,王国维在研究石经中,“颇怪汉石经诸经全用今文,而魏时全用古文,因思官学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书共三卷。[9]他从古文字学角度,专门研究古文,1916年著《汉代古文考》,[10]1918年校唐写本《尚书孔传》和薛季宣《书古文训》,[11]到1926年还作有名文《桐乡徐氏印谱序》。[12]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过与古文经学有关的《孔子家语》。至于他对《尚书》研究的贡献,是用不着在这里多说的。
1927年3月,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姚名达给顾颉刚先生写信,讲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13]这体现了王氏对疑古一派的态度。王氏是努力于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荐王国维到正在筹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胡适遂向清华推荐。[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迁入清华。7月,应学生会邀请,向暑期留校学生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发表于《清华周刊》。[15]文中列举近期古器物图籍的发现,强调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王氏讲课题为《古史新证》,其总论对信古、疑古都有所批评,接着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16]
这对他7月讲演的观点,作了理论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与疑古的差别,在上述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史的先声。他在自序中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里特别讲到“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18]并就顾氏提出的夏禹的问题,依据“准实物的材料(齐侯镈及齐侯钟、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的。
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冯友兰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审查,是很正确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国学者)担心我们不重视史料审查了,也不无道理。现在确有些论作忽略了史料审查,他们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做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19]
这就是我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
注 释
[1]参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第48页。
[2]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7页。
[3]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4]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页。
[5]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6]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第7页。
[7]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383页。
[8]参见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57、120、122、124、133、138、150页。
[9]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62页。
[10]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63页。
[11]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78页。
[12]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62页。
[13]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39页。
[14]参见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36页;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01页。两书所记月分稍有不合,似应以顾书为准。
[15]参见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此文后收入《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五,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6]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1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304页。
[19]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来源:《原道》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 0000
- 0002
- 0000
- 0000
- 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