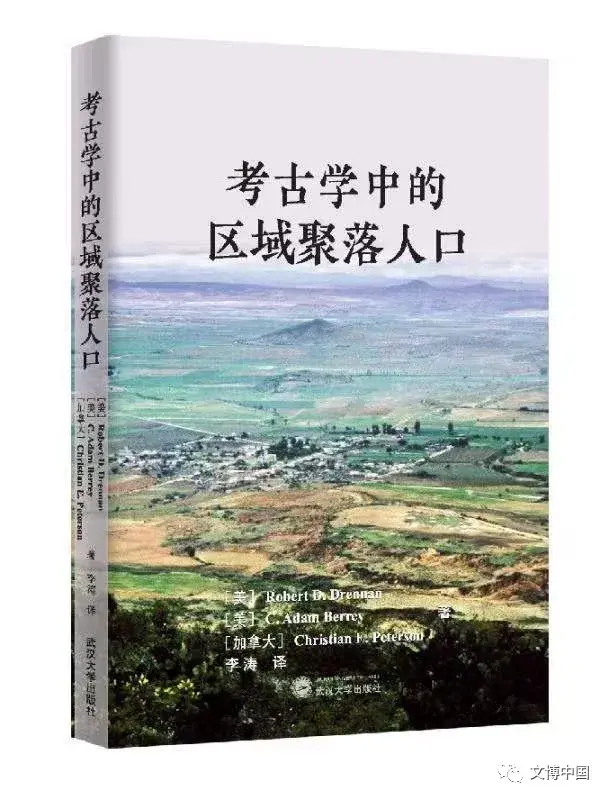冯骥才: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百年纪念日已经到来。于是,一个中国文化界无法放下的问题,再次焦迫地摆在面前:敦煌文物何时归?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发现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悲剧性的。三万多件珍贵文物,流散到十多个国家。这是有史以来出土于一地的文物;经受最惨重的一次文化瓜分。
然而今天,对于敦煌文物的物归原主,我国文化界却依然忧心忡忡,并不乐观。不大相信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眼下会回心转意,把东西送回来。这是因为近三十年,他们对此的各种强辩与巧辩说得实在太多,这表明他们对敦煌文物的占有欲强旺依旧,没有任何松动与超越前咎的觉悟。
在藏经洞被发现了一个世纪的今天,历史已经没有秘密。藏经洞发现史与蒙难史的所有细节,都明明白白写在纸上,任何辩驳皆无意义。然而,我们还是要强调如下的事实:
一、藏经洞的发现者是敦煌道士王圆箓,时间是1900年6 月22日。
二、最早认定藏经洞文物价值的是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时间是1903年。
三、1904年3月,敦煌县令汪宗瀚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一次调查后, 遂命令王圆箓将文物就地封存。这是正式的政府行为。
四、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2月25日,前后抵达敦煌莫高窟。他们都是先得知藏经洞有珍贵文物出土,随即直奔文物而来。并都以少许银钱买通文物看守人王圆箓,启封取走大批珍罕绝世的敦煌文物,运回各自国家。随后是日本人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以及俄国人奥登堡等。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连串事实的细节,是要说明——斯坦因和伯希和不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者。他们是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和被封存之后,设法将其启封取走的。可能有些人被当年伯希和在洞中翻阅敦煌遗书的那帧照片所迷惑,以为那是在进行考古发掘。但相反——那决不是在发掘现场进行考古鉴定,而是为了取走文物而做的识别性筛选。这一点,必需认清。
我们承认斯坦因和伯希和是两位优秀的考古学家,伯希和还是一位天才和罕世的法国汉学家。他们对敦煌学的确立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特别是伯希和,他与斯坦因的不同之处是,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目的,是割取莫高窟壁画,只不过因那里的佛教徒太多,他不敢下手。伯希和不但没有伤害壁画,相反对莫高窟进行有史以来首次的考古调查,而且学术意义很高。但还是要指出,即使是这样——即使在当时,他们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也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敦煌学的贡献与他们非法取走敦煌文物,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分而论之。
当然,这行为在当时的西方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前期,西方中心主义的肆虐,有着所向披靡的殖民主义背景。这便使他们的考古狂潮从希腊顺利地越过地中海,将金字塔中法老的干尸,以及长眠地下的亚述、巴比伦、苏美尔和赫梯等古王国那些美丽的残骸,一个个搬到太阳之下,然后再搬到他们的国家,入藏他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跟着一路自西向东,进入了古老的印度和中国。殖民者从来无视殖民地的文化主权。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偏执和荒谬,不是谁能避免的。故而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殖民地的“土著”人自己的任何发现,都不算数;而他们之中第一个看到的才是发现者。在学术领域里,殖民地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成立,这些成果最多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素材性的参考,只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学术承认。故此,西方的一些著作总说斯坦因是敦煌文物甚至莫高窟的发现者。包括《大英百科全书》也这样写。斯坦因没到敦煌之前的一千多年,莫高窟一直有中国人在那里。难道它一直等候这位英国人来发现?而且斯坦因到了敦煌,拜见当时的敦煌县令王家彦时,王家彦对他常识性地讲了莫高窟的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他才知道莫高窟由何而来,这也算一种考古发现?在这里,发现这两个字显然已超出考古学的意义。它似乎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谁“发现”,谁就是它的主人。就像儿童游戏那样,谁先看见就算谁的。如今,虽然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源远流行的背景和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仍然使今天的一些人不能走出那个荒谬绝伦的历史误区。这便是敦煌文物不能归还原主的最深在的根由。
然而,今天思辩这一问题,并非只是为了责怪过去,而是为了一种超越。
因为20世纪,人类文明遗存的处境实在艰辛。殖民主义掠夺、战争抢劫、盗窃走私,再加上一些殖民地缺乏严格的文物保护法,那里的人们又缺乏文化的自觉,致使不少文明遗址遭到破坏。文物从它的发生地流散各处,后果极其混乱,不少文明遗址已经支离破碎,失去了它所必需的完整性。
在世纪的交接中,接过20世纪这个糟糕的文物状况的新世纪应该怎么做?是承续上世纪那个谬误,还是纠正历史,还文明以文明?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万件文物,绝大部分是中古时代的文书。同一地点出土如此浩博和珍罕的古代文书,举世独有。而且它内含无涯,包容恢宏,极大角度地囊括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及其对外交流的历史信息。然而,其中深刻的意义,只有当它置身于这文明的发生地,才能真正充满感染力地显示出来。
文物——尤其是重要文明遗址和重大文化发生地的文物,都有着不可移动的性质。它们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本土。它是那一方水土的精髓,是历史生命活生生的存在,是它个性经历的不可或缺的见证。文物只有在它发生过的本土上,才是活的,才更具认识价值。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都有它自身的完整性,都有它不可移动与不被肢解的权利。这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文明的尊严,也是人类的一种尊严。
谁先认识到这一点上,谁先步入文明。
刻下,一些欧洲国家不是已经开始交换二战中相互劫去的文物吗?这应被视为告别野蛮、自我完善、走向文明的高尚行为。因为,当今的人们已经深知,文明遗址中的文物不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谁把它当做财富来占据为己有,谁就亵渎了文明本身。站在这个文明的高度上说,谁拒绝文物归还原主,谁就拒绝了文明。
1909年,伯希和将已经运出中国的敦煌遗书,选取若干带回北京,展示给我国学者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等人。当学者们获知这些绝世珍奇已落入外国人手中,即刻展开一场义动当世、光耀千古的文化大抢救行动。学者们一边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火速运抵京都;一边将这情况公诸国人,于是更多学者加入进来,对敦煌遗书展开迅疾而广泛的收集、校勘、刊布与研究。它显示了我国知识界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和学术上的敏感。随后,学者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等,奔往巴黎与伦敦去查寻和抄录那些遗失的宝藏。学者姜亮夫几乎倾尽家财,自费赴欧,去抢救散失在海外的文化遗产。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流落他乡的敦煌遗书抄录回来。很多人一干就是多少年!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浩荡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做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上世纪初,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有感于敦煌受难之惨剧,说出铭刻于敦煌史上一段著名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余,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耳。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这痛心疾首的话,有如霜天号角,曾呼叫着当时国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呜,唱尽一代学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怀。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依然强劲地牵动着我辈的文化责任。从今天的世纪高度看,这桩没有了结的敦煌公案,不仅是敦煌——也是人类文明犹然沉重的一段未了的伤心史。因此,今天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捍卫文物的主权,而是为了捍卫文明的尊严,来呼吁和追讨敦煌文物。那就不管别人是不是觉悟,我们都要不懈余力地呼吁下去。催其奋醒,重返文明。先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自发的文明,尊重先人的创造,才是一种自觉的文明。故而,只有在敦煌文物归还故土,世界各大文明遗址流散的文物全都物归原主,我们才能踏实地说:地球人类真的文明和进步了。因为人类的进步的前提,就是不再重复过去的谬误。
来源:《文艺报》2000年第0622期
- 0001
- 0001
- 0002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