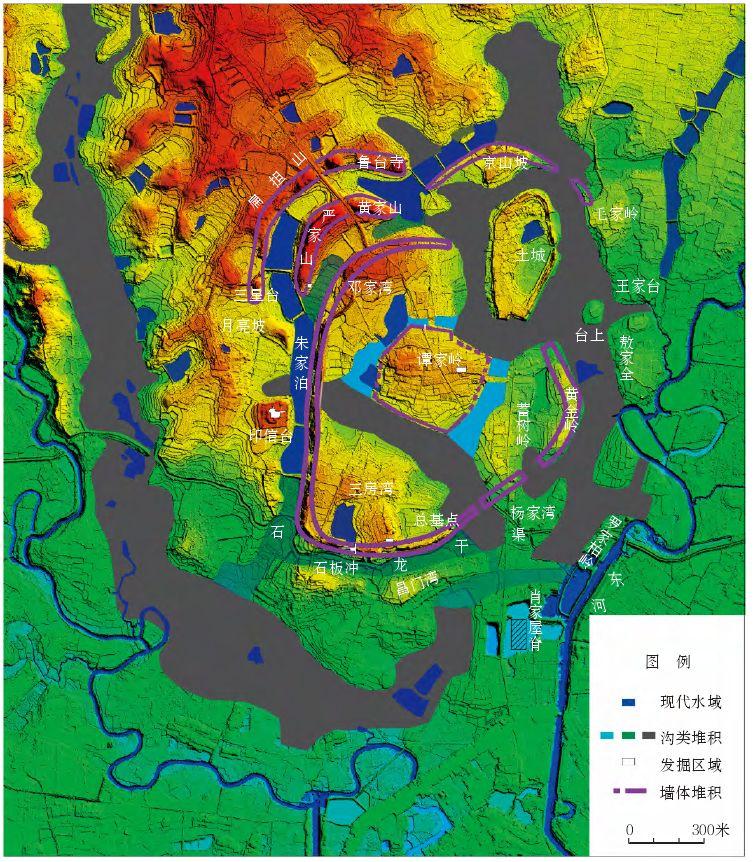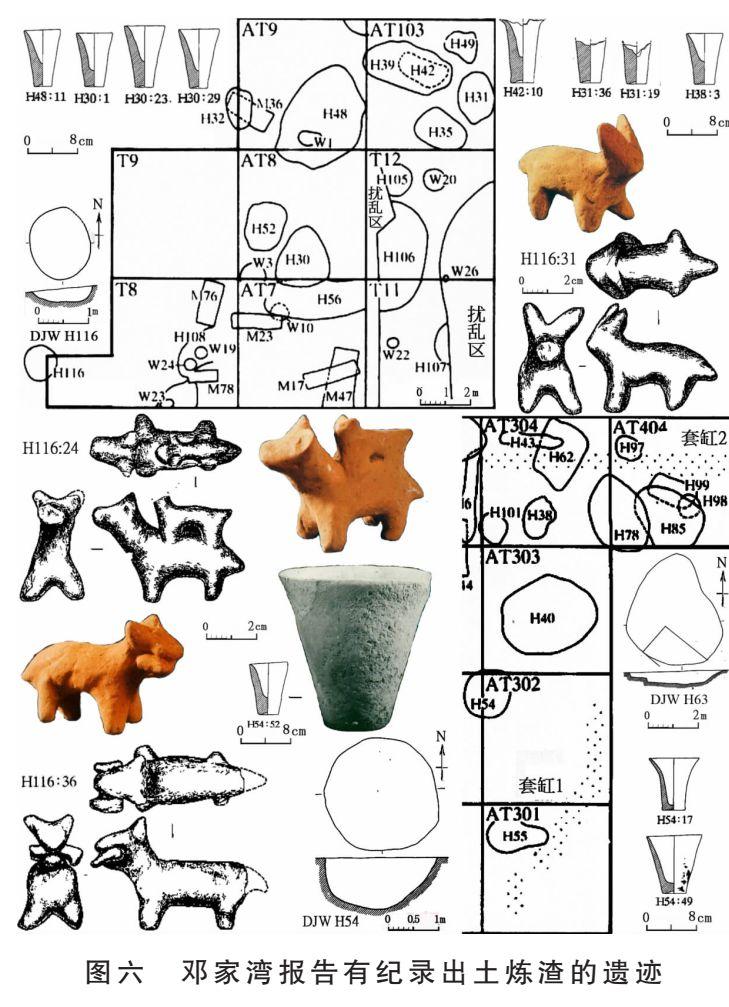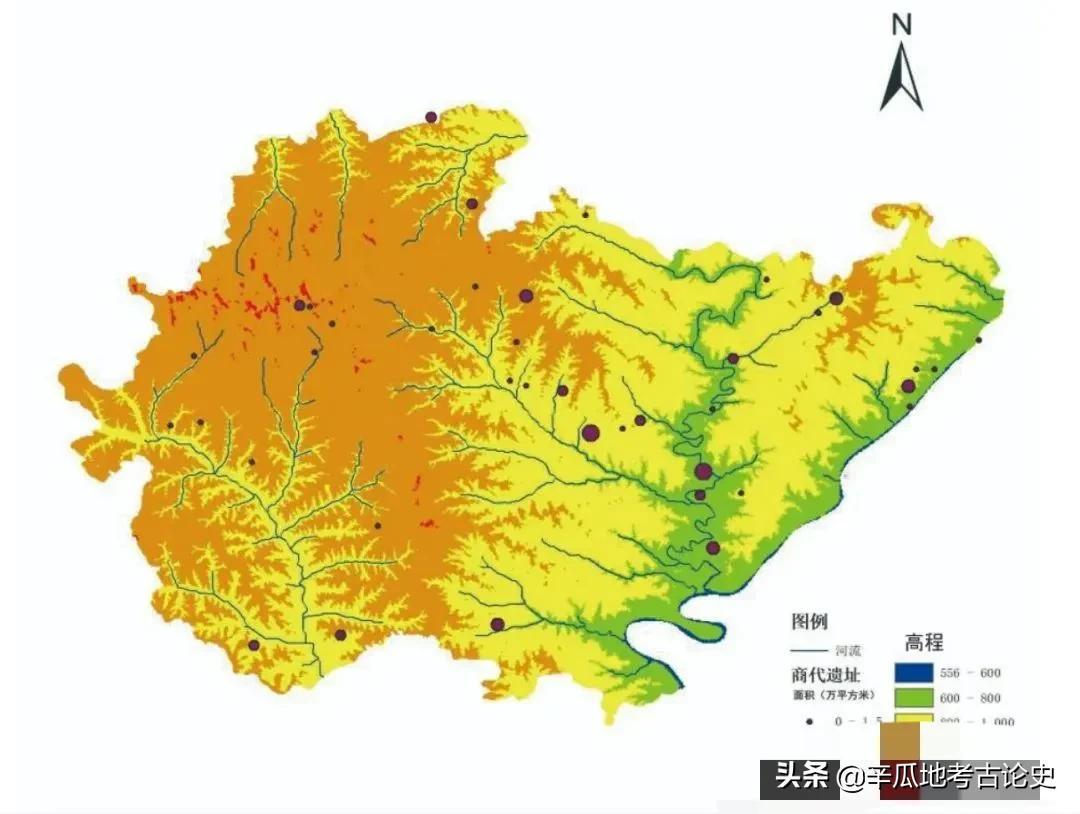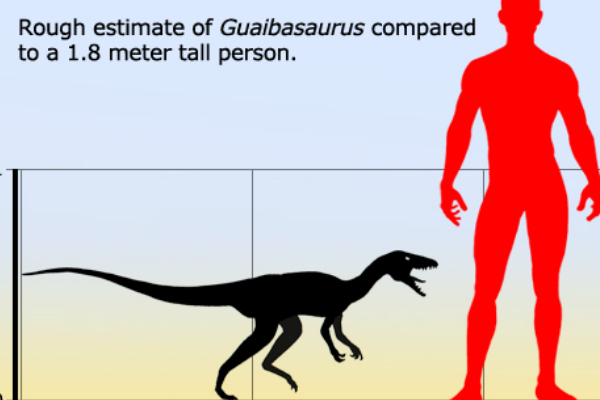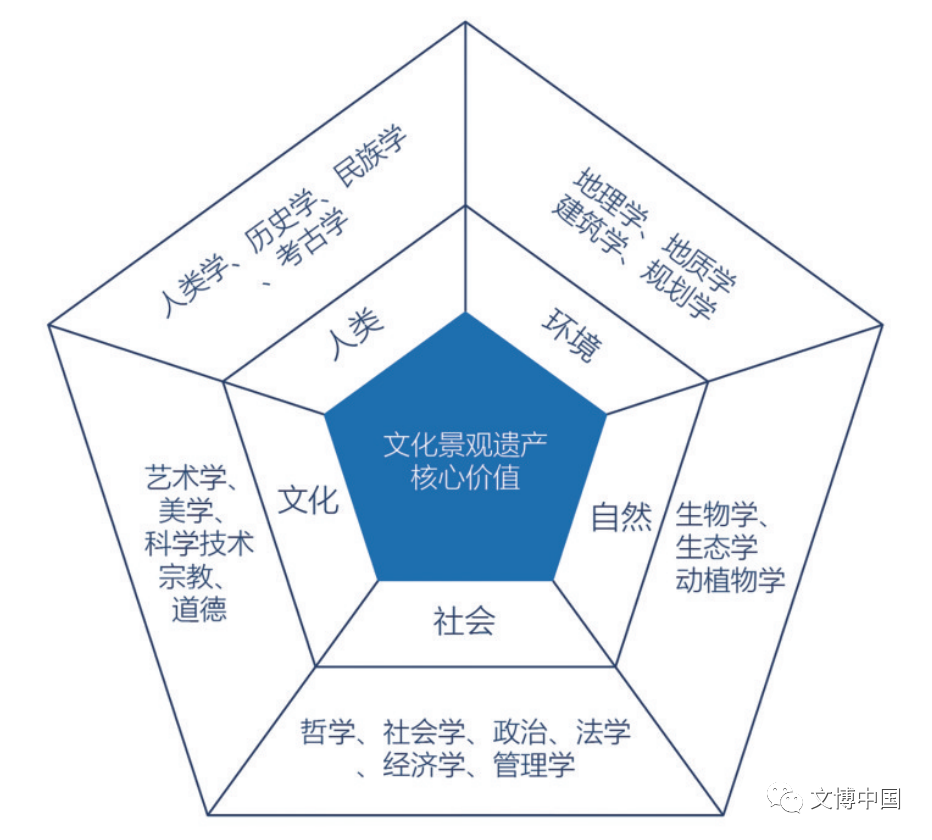张天恩:论西周采邑制度的有关问题
西周的采邑制,是当时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西周王朝建立后所出现的封国(封建诸侯),就是这一制度的推广和发展,东周列国的封君制则是其延续,西汉及其以后的封国实际也有对这一制度的承袭。
对于采邑制在西周时期已经存在,几乎是大家都相信的。但可惜的是,在先秦的历史文献中,实际上连“采邑”这个词也不曾出现,也就没有什么更具体的记载,故学术界很少有人对西周时期的这一重要制度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侯志义先生的《采邑考》一书,虽对采邑的形成、体制、生产关系及其没落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讨,可称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但论述的重点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对西周采邑制的讨论却相当简略,不免仍存遗憾。笔者长期从事商周考古学的研究,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往往与此相关,故不得不进行思考,渐形成了一些的看法,为了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拿出来供大家批评。
一、西周采邑的由来
“采邑”一词并不见于周代,先秦的文献中尚没有出现,较明确的说法似乎是出现在东汉以后。《史记·鲁周公世家》的首句为“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宋裴骃在《集解》中对这句话解释时,首次提到了“采邑”这个词。但所引的是“谯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而在对《燕召公世家》的“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句解释时,《集解》引文则为“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可见采邑也可以称为“食邑”,两者似无本质的区别,均是指某人的封地和封邑而言。
后来,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说明《鲁周公世家》的同一句话时,称为“菜邑”。谓:“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以为周公之菜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风雍东北故周城是也。谥曰周文公,见国语。”《索隐》在《燕召公世家》中也称为“菜邑”。看来“菜”与“采”当是文字之异。
而较早文献的说法是“采地”或“采”。《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有“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之说,《礼记·曲礼上》则说:“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更早的记载,则可以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找到线索,但也称之为“采”。
《中(方)鼎》铭文曰:“惟王十又(有)三月庚寅,王才(在)寒師(次),王令(命)大(太)史兄(贶)(K21S402.jpg)土。王曰:‘中,兹(

)人入事,易(锡)于珷(武)王乍(作)臣。今兄(贶)畀女(

)土,乍(作)乃采。’”
《谴卣》和《谴尊》铭文曰:“惟十又(有)三月辛卯,王才(在)厈,易(锡)谴采曰趈,赐贝五朋,谴对王休,用乍(作)姞宝彝。”
这几件铜器的年代相当,约在西周早期偏晚的昭王时代,近似的记载还可见于时代相当的《静方鼎》等铜器的铭文中。
侯志义先生指出《中(方)鼎》铭“作乃采”和《谴尊》铭“锡谴采”的“采”,就是对于“采地”或“采邑”的最早记载。前者是说以

地作为中的采邑,后者是以趈地为谴的采邑①。他还对采地的得名进行了分析,认为采字应按甲骨文作“

”的字形, “象取果于木之形”,大夫之邑名“采”者,盖取义于此。这些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论断。究其实,采之原意就是取采摘、采撷。由此分析,周人最初所赐的“采”实际上就是赐予土地,让臣子们采收可以食用之物。
这是因为周代尚处于比较落后的农业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条件均非常低下,早期的国家政权还没有形成聚集社会财富的赋税制度,更没有成熟的货币体系和商品经济,王朝就不可能有俸禄薪水及其他方法来供养不断增加的王族成员,以及提供用以维持国家机器运行的机构中官吏、贵族的生活、享用之需。另外,还有为这些人服务,并依附于其主人的所谓臣妾、奴仆类人员,同样有得到赖以生存资源的需要。没有有效的机制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也就不能够保证国家机器进行正常运转。
在商周时期,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基本状况是人口稀少,耕地富余。当时人的生活需求并不甚高,生活资源也不丰富,但王室广泛占有的土地,就成了最主要的财富之源。《诗·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而土地使用权的获得,则可以解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在当时的情况,要解决上面所说的实际问题,所能采用的最好和最适宜的方式,就只能是根据臣民们各自的身份、地位、功绩,划给一定份额的田地,使之安居乐业。各自依靠在份地上劳作、经营的收获,来供养自己家庭的成员及依附者,并以之支撑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行。这种份田,就是我们在西周金文中常见的赐予臣工们的田地。如:
《

鼎》铭文曰:“惟八月初吉,王姜易(赐)

田三田于待

。”
《多友鼎》铭文曰:“易(赐)女(汝)土田。”
《敔簋》铭文曰:“易(赐)田于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其它还有《大克鼎》、《不其簋》、《永盂》、《吴虎鼎》等许多铜器的铭文,均有赐田的类似记载,这里不再列举。得到了这些土地,受赐者就获取了在其上生存和生活的权利,所以称之为“采地”则是非常恰当的。
采地的主人欲从土地上获得所需,并赖以生存生活,则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庄园聚落,必然会形成居邑。《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类建筑于新赐采地内的邑落,首先是采主们为了方便作务经管而筑的居室。《礼记·曲礼下》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可见最初采地之邑内可能还会建立宗庙。这些居住的邑落,处在采地之内,便形成了既有采又有邑的格局,很自然地会被称之为采邑。这便是史书上所谓的“采(菜)邑”或“食邑”。也就是《礼记·祭法》所谓的“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这大概就是从最初的采或采地,发展演变而被称为采邑的过程。故《曶鼎》铭文有“尚(當)卑处氒(厥)邑,田氒(厥)田”之说。
二、周人采邑制产生的年代
关于周人开始实行采邑制的时间,侯志义先生认为草创于武王灭商以后②,似乎仅限于从征之人。但我们以为,周人不大可能在灭商后的短暂时间之内就能创造出这样一种比较成熟的制度,应该有一定的渊源。而据已有文献的记录分析,当可以提早到周王朝建立之前。
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曰:“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燕召公世家·索隐》谓:“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都明确指出在文王受命后,将周人岐周故地的周、召之地分赐周公、召公。《毛诗正义》云:“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曰周,其召是周内之别名。”
至迟可能自受命之年起,文王已有了迁都的考虑,故把都城岐周附近的土地开始分赐子弟。至于文王受命之年,文献记载还是比较清楚的,一般认为是从决虞、芮之讼之年算起。《史记·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又说:“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正义》谓“十当为‘九’”。可见在灭商之前,文王在位的时间应有九年。《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说法一致。武王继位后两年,率军伐纣,两王共计十一年。所以《周本纪》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就说明周、召二公受赐采地,应是在灭商前十一年。
除了周公、召公以外,在灭商前受封的可能还有卫康叔及其他人。
康叔封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年齿较小。《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康叔排行第九,在霍叔处之后,仅长于冉季载。《索隐》谓:“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史书虽无康叔受封采邑的确切记录,但据“从康徙封卫”语可知他在封于卫之前,已在畿内有名“康”的采邑,徙卫仅是改封。
康叔改封的时间比较清楚,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说法,是在周公平定武庚和管、蔡之乱后,即周成王四年,灭商后的第六年。康叔之称既在此前,当非此次所封。武王伐商后曾有大规模封赏,司马迁在《史记·管蔡世家》中说到康叔年少未得封,故其应是在伐商之前曾被封于畿内名康之地。但《史记·周本记》载康叔参加了武王伐纣,自宋以来学者就推测《尚书·康诰》是武王之诰,至今也有学者支持这一认识②,则说明康叔初封畿内的时间当在灭商以前。
那么,那些年长于康叔,参加了伐纣灭商之战的兄长,除了周公、召公之外的叔振铎、毕公高、毛叔郑,以及功臣宿将如姜太公、散宜生、南宫括等,均应在战前已有采邑。所以,认为周人的采邑制度出现在立国之前,当不成问题。
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一制度出现的时间可能还会更早一些。
文献记载中有周文王的弟弟,武王兄弟之叔父封于虢的记载。《国语·周语》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东汉贾逵的注说:“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也。”韦昭谓文公为“虢叔之后,西虢也。及宣王都镐,在畿内也。”《秦本纪·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但是,这些记载均无虢叔受封的具体时间。
作为周文王的弟弟,获封的时间,即使不是在其父王季在位之时,也应该是在文王的时代。《尚书·君奭》提到文王重用的五位大臣为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和南宫括。《周本纪》记载参与武王伐纣的元老中,除了虢叔外,其他四人俱在,或是因为虢叔年齿过大甚至已经故去的缘故。按照《尚书·无逸》和《周本纪》所载文王在位五十年的说法,到受命之年封周公、召公时,文王的年龄大约在60岁左右(这里不取《集解》引徐广曰:“文王九十七乃崩。”的说法),其母弟当为50岁上下。到伐纣时,约在60岁左右。在文王受命之年封周公、召公时未提到,武王灭商后大封功臣时也未涉及封西虢,但文献却有此记载,只能是先前已经存在。
杨宽先生曾说过,“西虢当是虢最早的封邑,虢原先也是畿内诸侯”,“……周文王开始重视在王畿内用分封制扩展周人占有田地和扩张势力”③。其说虽无深论,但可能也是作这样考虑的。《史记·晋世家》的《正义》引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异母弟虢仲於夏阳”,此为北虢,应该是从西虢改封于夏阳,显然不是始封。故可以推测周人赐采和采邑制的出现在文王执政的早期或更早一些,而不应以受命之年为限。但可能在文王晚期由于本族人口的衍生,以及外来依附投奔人员的增加而使这一制度渐趋成熟。
由此可见,采邑制的出现肯定是在周王朝建立之先,到西周初期分封功臣时,实行的已是一种实践多年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灭商之后为了酬封功臣才创建的。只是到“周武王克商后,在原来商的王畿内分封北、鄘、卫而设置三监,同时分封同姓亲属,身居要职的如召公、毕公、荣伯等人的封邑,也都在王畿之内。到周成王时,周公就进一步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分封亲属而扩展周的疆土和统治势力”④。
但可以推测,这一制度的出现也可能不会太早。因为从史书上有周太王的儿子太伯、虞仲奔荆蛮的记载,应该相信其在太王时代还没有产生。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史记》等文献记载,太王迁岐时不仅有“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而且还有“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面对突然增加的大量人口,古公采取的措施是“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集解》引徐广曰:“分别而为邑落也。”就是分别安置在不同的聚落中。这种作法,是否为周人后来在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行采邑制提供了借鉴,倒是值得思考的。
三、西周的采邑与封国的关系
正因为周人的采邑制在立国之前已经初步形成,故在武王伐纣获胜,占据了殷商王朝统领的广大东方地区时,就推而广之,顺理成章的变成了对新拓国土管理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成为周王朝对全部国土进行统治管理的有效措施和主要方法。绝大多数周王的子弟,以及仕于王朝的同姓和异姓的贵族,特别是那些有功之臣,都可能有机会得到周王或上司的赏赐,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采邑。
除了周初武王、成王的大量分封外,西周时期的受封者在文献记载中比较明确的还有一些,如穆王时期的祭公谋父、造父,宣王时期的郑桓公友、秦非子等。
《史记·周本纪》载祭公谋父是周穆王时的大臣,曾阻谏征犬戎。《集解》引韦昭曰:“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为王卿士。谋父,字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郑州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大夫祭仲邑也。《释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也’。”应在今河南郑州市以北。
郑桓公友初分之郑也在畿内。《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周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索隐》:“郑,县名,属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也。”《周本纪》所记相同。《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一般认为地在今陕西华县境内,但现在也有在陕西凤翔境内的说法⑤。
与前两者有所不同,造父、非子均不是周室王族子孙,而是异姓他族。《秦本纪》记载造父因善驭,为周穆王驾八骏“千里救乱”有功而“封赵城”为赵氏,地在今山西霍县,成为战国赵国的始祖。因为非子为周王室“主马于千渭之间,马大繁息”之功,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地在今甘肃清水境内。并得以复氏继祀。在此基础上,秦人逐步发展为西垂大夫,以至后来始国并成为诸侯。
金文的记载就更多。如《墙盘》所记微氏家族为殷遗民,归周后武王命周公为之舍寓于周。《宜侯夨簋》所记周康王在宜,将虞侯改封于宜地,赏赐土地人民,以及弓、矢诸物,而称宜侯夨。
据有关历史文献和金文资料,我们还能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西周时期许多人或家族的采邑并非仅有一处,而可能存在两处甚至多处。也就是说一个人因为功绩的大小,或者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等原因,往往有初封,以及后来的益封或改封,本人或其家族成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获得采邑。
《礼记·王制》所说“方伯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虽可能并不尽然,但从《左传》记载郑与鲁易枋、许田的故事,还是能看出确存在这样的事实。《周本纪·索隐》:谓“祊是郑祀太山之田,许是鲁朝京师之汤沐邑,有周公庙,郑以其近,故易取之”。《正义》杜预云:“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国朝宿之邑,后世因而立周公别庙焉。郑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邑在祊。郑以天子不能复巡狩,故欲以祊易许田,各从本国所近之宜也。恐鲁以周公别庙为疑,故云已废泰山之祀,而欲为鲁祀周公,逊辞以求也。”《括地志》云:“许田在许州许昌县南四十里,有鲁城,周公庙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费县东南。”说明鲁在国境外还有受赐的采邑,并建有周公庙,郑也有靠近泰山的采邑。名称虽是“汤沐邑”或“祀田”,其实际也是采邑的性质。但到东周由于王室衰微,无力进行巡狩和祭祀泰山等重大活动,诸侯们为了就近管理的方便,就可以互相易换了。估计这些田地的范围可能也不是很小,不然就不值得要当作重要的事记载下来了。
再如秦非子初为附庸,受封采邑于秦。至其四世孙庄公破西戎,为西垂大夫,周宣王增加赐予其先大骆所居地犬丘,地可能在今甘肃礼县东北部⑥。以及《大克鼎》载周王赐给克的康、匣等多处田地,宜侯由虞改封于宜等均可对此说明。还有郑桓公徙民洛东,虢、郐献十邑而居之等。
无论是在灭商之前,还是在西周建立以后,以上例证体现的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王室所有制。分配形式则是周王据具体情况赏赐采邑,呈现的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图景。正好可以印证《国语》记载周襄王所说的,“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虽然,从三年《卫盉》、五祀《卫鼎》等铜器铭文可以了解到西周中期已经出现了土地交易的现象。但参加交易的人员有王室大臣,说明其活动仍要得到王室的认可,并不是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还不能认为当时已经存在实际意义上土地私有或买卖问题。宣王十八的《吴虎鼎》是西周晚期的标准器,记载吴虎在接受其先祖或同族的土地时,不仅有大臣参与四至勘界,还有周宣王重申的厉王命令,就是最好的证明。毕竟当时地广人稀,一直到西周晚期周王室仍有田地可以赐人。甚至到了春秋中期,《左传》还记载周襄王曾赐四邑之地给晋文公。
这些赐田的性质,主要是作为姬周王族和异姓贵族的采地,即采邑。从理论上讲,各级贵族只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并无所有权。所以,一旦有过错,王室就有权予以追夺。故武王去世后管叔、蔡叔挟武庚作乱,被杀或被迁,即是其例。后蔡叔子胡率德改行,又得复封于蔡。
不过,像这样的例子,在整个西周时期也还是比较罕见的。绝大多数封地均成了各家私产,子孙传袭,世代继承,文献和金文中常见的西周及东周世族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家族在其采邑上建起了宗庙,形成都邑,多数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大小不等的封国。正如《史记·外戚世家》所说的“家化为国,不变其姓”,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将国称为“国家”的历史根源。但在西周却没有称其为国的证据,只有赐某人以“某田”或“采”,邑名后缀以国是晚出的说法。所以,周代封国实始于周天子分赐的采邑,因采邑及封国曾受过周王的册命,从礼制讲还是周天子统属,故其封国之君主,仍是王臣。
在封国之内,国君同样也可以把土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属臣,作为采邑。《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时在西周灭亡前两年,虢、郐有邑献郑,可以说明之。再说,周初封鲁的殷民六族,封唐叔的怀姓九宗等,也不大可能都居于一邑之内,很难想象让其都邑外方百里封地的范围,不设置任何进行控制经营的居址邑落。所以,西周诸侯国内无采邑的认识⑦可能是有些偏颇。但这类采邑并不称国,而只称邑,受赐者只是采邑主,属于封国之大夫,一般不是王室的大臣。由此就可以明白《礼记》所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的道理所在了。
而如果是封国内的采邑,由于没有得到周天子赏赐册命,即使发展壮大,富可敌国,势并诸侯,但仍不会被视之为国。其主人仍为封国之卿士,要跻身国君的行列,尚需要周天子的册命认可,否则就难以得到世人的承认。所以,《秦本纪》载周平王是在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东迁的,岐、丰故地已根本无力恢复,但他仍可堂而皇之地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甚至到了战国之初,韩、赵、魏三家已将晋国土地瓜分殆尽,原来的宗主国国君晋幽公反朝于三卿,但还需要天子名义上的册封,有了周威列王的赐命才得为诸侯⑧。可见周天子为天下土地之主的观念,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分封之制虽说是为了“公侯伯子男,各有宁宇”,但实质还是为了巩固屏护姬周王朝的统治。《左传·定公四年》所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由于周天子不断赏田赐采,以至到头来无地可赐,结果则是权威丧失,其统治也就难以为继了。
四、西周采邑与诸侯国的问题
应该注意的是,西周时期除了数量众多的赏赐性采邑发展起来的封国,还有一部分是出于战略形势需要特意所封之国。主要有监和侯两类:
所谓的诸监,既有周武王克商后,为了防止殷商贵族的反叛,镇抚殷遗民,在殷人的王畿所设的“三监”。也有为了管理其它地区,出于类似目的所设的某些“监”,如《应监甗》铭的“应监”。诸监的一部分后来也发展为封国。
至于诸侯,主要是在克商之后(或说在周公东征后。此问题争论较大,这里不便再展开讨论),封于周边地区与夷、狄之国为邻,有守土保边职责的侯国。如武王所封的齐、鲁、燕等,成王所封的晋(初封唐)、康王改封的宜、平王益封的秦襄公等,均是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国,与一般的采邑和由采邑发展起来的封国并不相同。
西周金文对诸侯和诸监是有所记载的。《仲几父簋》铭文的“仲几父史(使)几史(使)于者(诸)侯、者(诸)监”即是。此铭的记录说明诸侯与诸监在西周并存,地位也大体相当。其根源虽均与赐采有关系,但在本质上与采邑却有较大的差别。
有关的方面,可以从他们多属于改封,原来基本都有采邑之点得到说明。其不同之处,在于被分封的诸监和诸侯不是周王的至亲子弟或至近姻亲,就是至信近臣,所设、所封均有明确的目的,不是为了安土,就是为了守边。与仅从周王朝受赐一块或多块采田,使子孙衣食有赖的一般同姓和异姓贵族,或为奉先王之祀的先代后裔之国大不相同。《秦武公钟》所说“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的话,就包含了这两个层次的含义。“赏宅”可能是指初封于秦的非子采邑,“受国”则指襄公益封为诸侯。
具体到“监”与“侯”两者之间,同样也还有一定的差异。所设诸监,在隶属关系上仍为王室直辖,听命于周天子的指令,具有“王官”的性质。但改封之诸侯,虽也归王室统辖,却有更大的权利,往往被赋予征讨之责,拓疆之权,协助王室安定天下,属于一般所谓的“方伯”性质。《左传·隐公四年》载管仲对楚使的名言:“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诗·鲁颂》的“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以及《秦本纪》“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记载等都是明证。而且在分封时就明确讲是“侯”于某处,不同于一般的仅赐田地,经营生业。
《诗·鲁颂》就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克罍》、《克盉》铭文曰:“王曰‘太保,惟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命)克侯于匽(燕)’”。
《宜侯夨簋》铭文曰:“王令(命)虞侯夨曰:‘繇,侯于宜。’”
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四十二年速鼎》⑨铭文曰:“余肇建长父,侯于杨。”此铜器铭还可以印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的记载。
徐中舒先生曾指出过诸侯和诸监的分野。说“诸侯可以独擅一国,诸监为王室镇抚人民,自身该受王室节制,用后世的名词说,诸侯仿佛‘土官’,诸监仿佛‘流官’。”⑩对此,顾颉刚先生补充说:“后世的流官是三年一任,周代的诸监却是世袭的,有这一点不同。”(11)两位前辈的看法颇有道理,这就是诸侯与诸监的主要差别,更与一般由周王所赐采邑发展起来的封国不同。所以《史记·卫世家》记载卫顷侯为了让周夷王将卫改命为侯,曾厚赂夷王。
在采邑基础上发展演化出来诸侯国,是西周王朝统治边远地区的重要形式。其始虽与王臣采邑类似,但处在王畿之外,分封时多已获得较大的自主权便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就有了较大发展的空间。进入东周以后,王权衰微,兼国拓土的主要是西周时期所封的一些诸侯国。后世对畿内采邑也往往以国相称,但因缺少这种权利和区位优势,最终没有一个发展成为强国的例子。
犬戎之乱,周室东迁,食采王臣则竞相逃亡,尽徙河洛之地,致使在岐丰经营三百余年的王朝基业,旬日之间便土崩瓦解。直到秦文公十六年伐戎至岐以前的二十年间,关中地区基本是政治真空,未出现一支能代表王室而具号召力的集团或势力,不能不认为与西周王朝在畿内只封采邑,未建诸侯的历史原因有关。
五、余论
我们的讨论,将西周采邑制度的产生追溯到武王伐纣以前的文王时代,并指出其应是为了适应从小邦周向大邦国发展的过程中,满足周民族自身快速衍生,又要接纳大量依附投奔人群,扩展生存空间所实施的一种重要策略。实际上,这与周人当时正处在早期国家阶段,由血缘部族向地缘国家转变之初的社会形态有直接关系。
当然,不排除他们当时也可以采取另外的手段,谋求发展。如让成年的亲属及其他人员分散,自行拓展,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周本纪》所记太伯、虞仲“奔荆蛮”的故事,也许正是如此。但这样做的结果则往往会极大地降低国族内部的凝聚力,更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甚至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自己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在社会开始跨入国家的门槛时,必然会给国族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西周的采邑制则不同,是将本族所能控制区域的土地,由最高权力体现者——周王,根据家族内亲属的远近亲疏、才德,归依者的才能、功绩等,赏田赐采,建国封侯,形成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使家、邦同形,族、国一体,极大地增加了国族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抵御外力的能力,并有力地推进了早期国家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对周代礼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可以认为,周王朝对于不同级别的采邑及与之相关的封国之封赐、诸侯之分封,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社会之基础。
但是,与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一样,采邑制度也存在自身的弊端,没有救弊的办法,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周代长期实行这一制度,最终出现了《论语》所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至“自大夫出”的局面,反而成为导致了周王朝衰落灭亡的主要根源。
故对西周采邑制的研究和采邑考古的开展,将能推进西周历史文化和典章制度研究的深入。文献资料的不足,长期以来制约了这一方面的工作,考古事业的发展,有可能为此开辟新的途径
来源:《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 0001
- 0000
- 0002
- 0004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