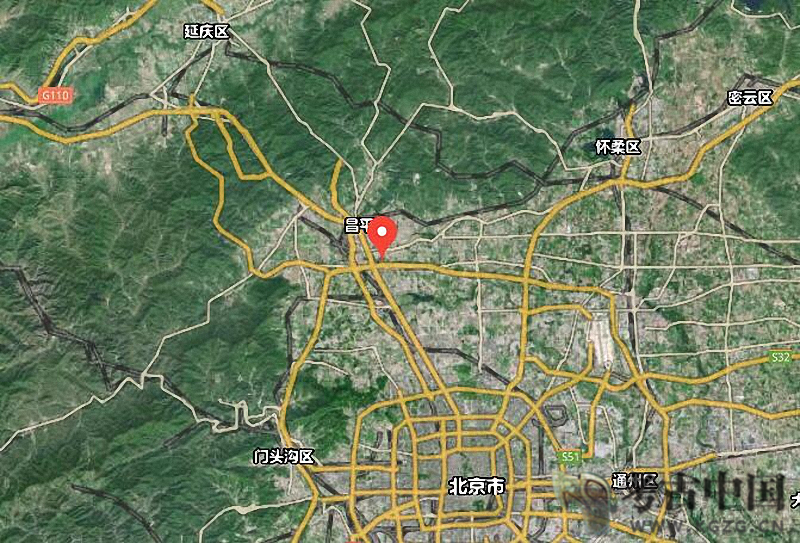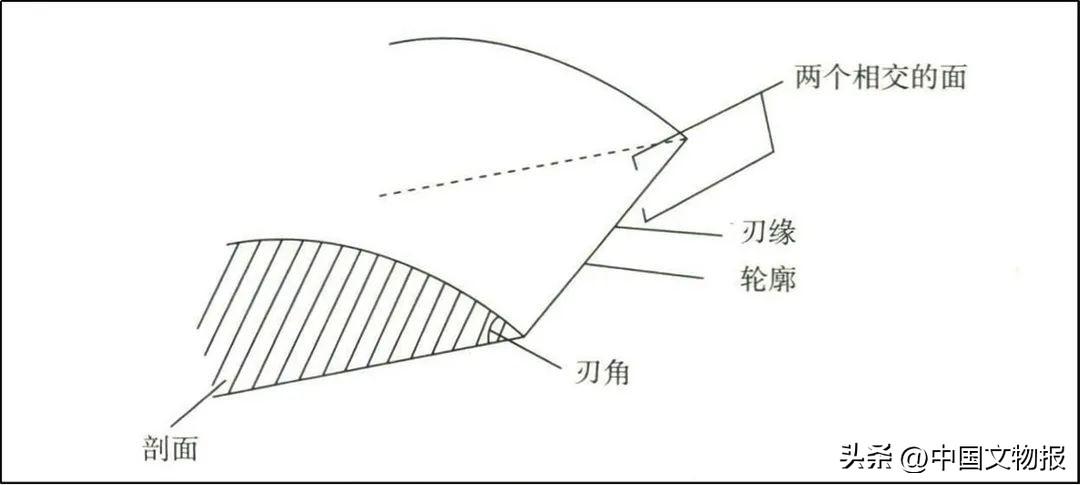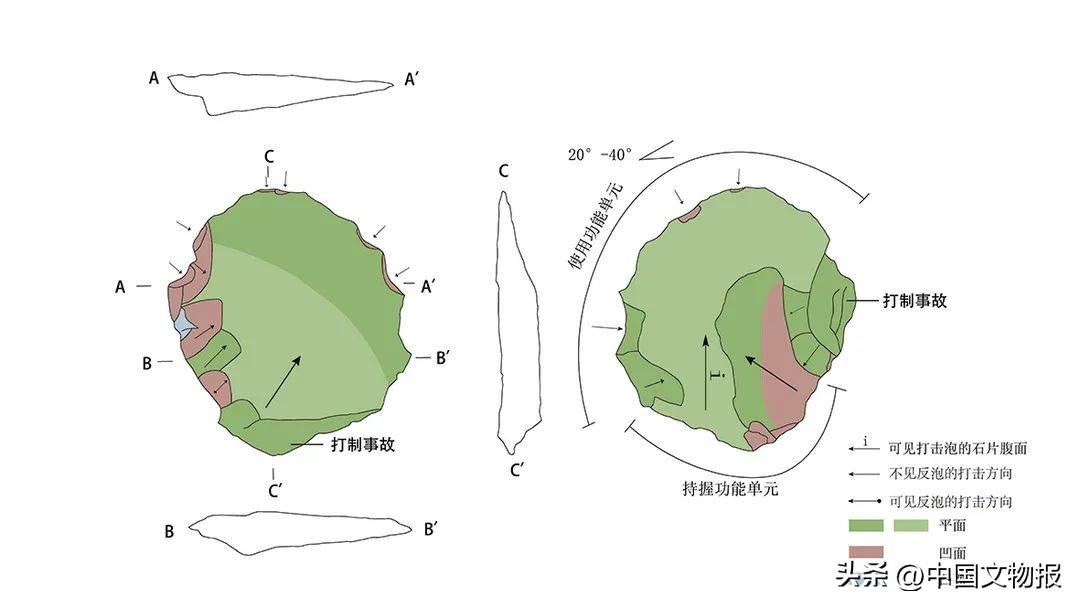安志敏:关于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
一
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是我国东北发现的重要史前遗址之一。自1983年开始发掘以来,以“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发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86年由于考古学家发表的众多讲话和传媒的互动配合,形成了一个热点。以红山文化为基础而提出了“文明的曙光”的观点,把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导入了一定的误区。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牛河梁遗址又陆续出现许多新的论据,从考古学实证的角度来考察,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认识。这里可以牛河梁遗址及其新发现的事例,作为继续讨论的参考。
二
自牛河梁遗址开始发掘以来,通过发掘简报的公布和报刊的大量报道,它的重要性已为人所共知。1986年9月,作者有幸参观过发掘现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女神庙”的结构问题。据当时目睹的印象,狭长的坑口已然揭露,在一侧的局部遗有小范围的解剖坑。据发掘简报:“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总长18.4、东西残长最宽6.9米”(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1-17页。)。从发表的平面图上也可以看出,经过清理的只是一部分。同时泥塑的残块也没有规律地散落在地面上,有关“女神庙”的建筑结构和泥塑的具体分布,都还不十分明确。至少表明“女神庙”遗迹还没有全部被揭露,所谓“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的结论(注:《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一版。),还难以得到证实。正像最近所报道的那样:“女神庙位于主梁顶部,至今未作全面发掘”(注:郭大顺:《牛河梁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0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如此重要的遗址竟被搁置了近20年,未免令人困惑不解。其二是积石冢群的时代问题。当时目睹的一座石冢表层的石棺里曾出土过一件铜饰,似不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在过去发表的资料中,一般也没有接触到铜器问题。最近公布的“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注: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序言,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又提出了新的信息。特别是1987年的发掘中所出现的冶铜炉壁,经过化验和碳十四断代,已确定其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比红山文化晚了一千多年。(注:李延祥等:《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研究》,《文物》1999年12期,44-51页。)那么,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此外,尚有其它的旁证。如这里出土的大量玉器,一直被作为红山文化积石冢群中的代表遗存(注: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海文物学》1994年1期,9-13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4-8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9-14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发掘》,《文物》1997年8期,15-19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市牛河梁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年8期。)。这里的积石冢群的石棺中出土了大批玉器,迄今为止,牛河梁遗址所发掘石棺墓的总数尚不一致,有47(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工作五十年》10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座或61(注: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8期,20页。)座之说。通过大批考古发现证实,牛河梁共发现64件玉器,主要出自石棺墓中。一般缺少伴存的遗物,也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这就为玉器的断代增加了一定的困难。至于“女神庙”却绝无玉器的存在,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牛河梁遗址共发现61座石棺墓(包括三官甸子城子山的3座),其中有随葬品的31座,只随葬玉器的26座,占随葬品墓的83.9%;随葬玉器同时随葬石器和随葬玉器同时随葬陶器的墓各1座,各占3.2%;只随葬陶器的墓葬3座,占9.7%,显然大多数石棺墓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至于第二地点四号冢的3座墓里虽然葬有彩陶,但不见玉器共存(注: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年8期,20页。)。以上的述说尚不可能为玉器的断代提供可靠的标志。有些出玉器墓葬的填土里虽然见到彩陶片,只能证明墓葬打破了红山文化层,并不能把随葬的玉器也提早到红山文化。在同一个石冢里,可能还包括不同时期的石棺墓,如有的石棺墓中出土的铜饰便是有力的证明。由此可以断定,牛河梁遗址的玉器主要出自积石冢群,一般没有明确的断代依据。同彩陶共出的,可能与红山文化有关,却没有玉器的伴存。至于惟一的玉器与陶器共存的墓葬,究竟是那一座墓?玉器和陶器又具有那些特征?都缺乏必要的交代。那么只有玉器随葬的,则不一定属于红山文化,至少从玉器的形制上还不可能找到具体的断代根据。因为这些玉器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的相接近。如具有代表性的兽首玉玦(猪龙玉饰),便见于河南殷墟妇好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版一○五,1-3,文物出版社,1980年。);而勾云形玉佩和箍形玉器则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图八三,2、6,图版五二,3、五三,4,科学出版社,1996年。)。最近河北阳原县姜家梁75号墓也出土1件兽首玉玦,但共存的陶器却与红山文化不相雷同(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2期,13-25页。)。据认为同内蒙古赤峰市大南沟的“后红山文化”相一致(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至于“后红山文化”是否属于“红山文化的延续”,尚值得再讨论。不过大南沟两座墓葬人骨的碳十四测定(墓35和墓54),约在公元前17-15世纪之间,明显地晚于红山文化。以上四处的玉器颇为类似,时代也比较接近,或可证明牛河梁石冢群出土的玉器同红山文化并没有什么联系。同时辽西和内蒙古接壤地带出土的同类玉器(注: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44-83页,知识出版社,1998年。),虽都被断代为红山文化,但尚存在一定的疑窦(注:安志敏:《论“文明的曙光”和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实证》,《北方文物》2002年1期,9-11页。),仍需作更深入的研究。不过它们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类似性,毕竟是不可否认的。至于牛河梁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的具体证据。因而牛河梁石冢群中可能包括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个不同的时代,从地层堆积和打破关系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在最近的发掘中,已由地层、遗物和断代得到确认,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不是牛河梁遗址唯一的遗存,这里还包括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把两者混淆到一起,势必陷入误区,也无法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三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文明时代是继野蛮时代之后的高级阶段。一般是指,一个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正像恩格斯所界定的那样:“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1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从而文明时代象征着社会进化史上一个突破性的质变,这在世界学术界,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结合世界上的研究现状和中国考古发展的实际,阐述了文明的涵义及其研究过程,并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以二里头文化为开始点,《中国文明的起源》便是首发的代表作(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1986年由于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又对文明和文明起源提出一系列新的论点,最终归纳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作为一本总结性的专著(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两者的观点迥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
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出现,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这时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至于把文明起源和国家出现提早到遥远的氏族社会,那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那种把史前时期的红山文化作为“文明的曙光”、“五千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注:《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一版。)或“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8期,43页。)”,进而把文明起源提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乃至七八千年间(注:邵望平:《老当益壮睿智如涌—向苏秉琦师求学散记》,《文物天地》1993年2期,3页。)”,甚至还有“上万年的文明起步”(注:Arthur Cotterell,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p.8,1980.(科特雷尔:《古代文明百科全书》)。)等说法。把文明起源提早到如此遥远的年代,也是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开端的,这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还罕见类似的例子。
关于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独立诞生的还是相互影响的?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大体说来从最初的一元说发展到后来的多元说,既承认独立发生,又不否认相互影响。这些变化是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不断地更新人们的认识。最初把文明的起源看成是一元的,主要以传播论为基础,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便是它的衍生物。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文明起源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多元说也就应运而生了。近50年来,基本承认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有独立发展的六大古代文明,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发祥地,既是独立发生的,又不否认相互影响而逐渐扩大文明的领域,并从不同的传统上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些基本概念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不过以“新探”为核心的“满天星斗”说,却特别强调:“中国之大,很难说明什么地方有文明起源,什么地方没有。文明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注:魏亚南:《中华文明史的新曙光—就辽西考古新发现访考古学家苏秉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4日;又载《新华文摘》1986年10期,86页。)。这里把文明起源视作遍地开花的现象,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提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一部中国古代史就需要从头改写,甚至会影响到世界古代史的重新认识。不幸的是,这不过是在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说的基础上,所假设出来的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像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直到解放以前还处在原始公社的阶段,怎么能说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呢?尤其是它所指的范围是限于今天的中国疆域,还是要把“满天星斗”扩展到整个地球之上呢?决不能说由于“满天星斗”的存在,才决定了“中国文明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注:童明康:《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史学情报》1987年1期,34页。),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更严重的是,它违背了考古学实证的基本要求。在牛河梁遗址还没有深入发掘之前,就急于抛出一套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实际上红山文化仍处在氏族制度的原始阶段,尚无法作为“文明曙光”的象征;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可能已迈入文明的门槛,毕竟两者相差一千余年,也不可能用后者的文化因素来包括前者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因而“文明的曙光”势必成为过眼烟云。
四
文明起源和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考古学的实证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这是考古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目前的某些论点,虽然名义上也从考古学的角度着眼,实际上却忽视了考古学实证的要求,以“新探”为代表的便是典型的一例。因为在没有弄清牛河梁遗址的文化性质以前,就用推想来概括全面,并提早文明的起源,未免模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不足为训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考古发现,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开端。因为这里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概括全体遗存,更不能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来代替红山文化的本身。主要是没有建立在考古学实证的基础上,那么“文明的曙光”说,就难免陷于完全落空的地步。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历来是后来居上,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认识的变迁,便可以得到充分地说明。当然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只要我们实事求是,通过不断地工作,从考古实证上着眼,便比较容易为大家所共识。最后应该提出的是,牛河梁遗址从开始发掘到现在,已经快20个年头了,发掘报告一直没有发表,使我们难于进一步了解其基本面貌。后来的发现又出现一些重要的纠正和认识上的转折,无疑是崭新的考古学证据。我们相信随着今后继续发掘,必然会有更新的学术成果,对于解决红山文化的社会属性以及考古理论的问题上,都会做出重要的学术贡献,这是作为发掘参与者所不可推卸的学术职责!
来源:《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 0001
- 0000
- 0001
- 0000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