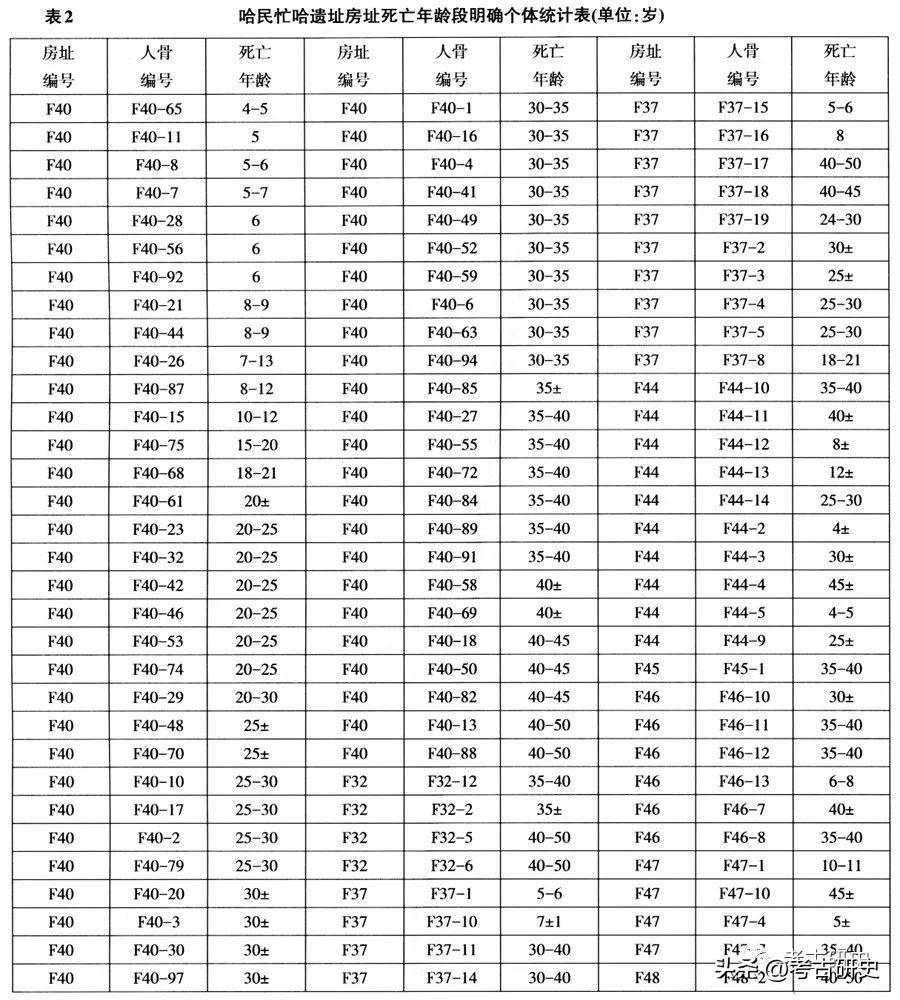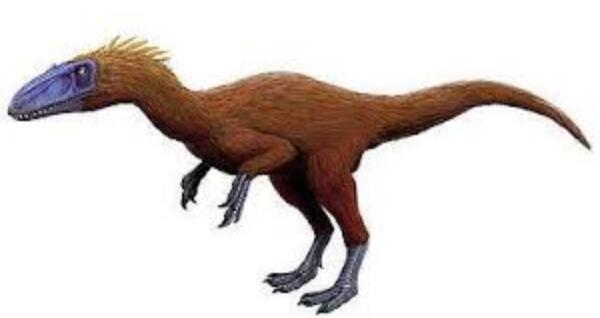高蒙河:研究考古遗存的三个过程及其方法
考古学的宗旨是通过遗存来复原历史,换言之,遗存系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核心。因此,在讨论有关考古遗存研究的诸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对遗存及其相关问题予以界定和辨义。
一、遗存的内涵与外延
作为考古学专业术语的“遗存”一辞,虽然经常出现在各种文献和研究论著中,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具体使用时往往见仁见智,内涵不一。比如:有的人将人骨、兽骨或植物种子等遗留物作为遗存;有的人则把具有一定功能的器具或使用过的遗迹作为遗存;也有的人将某一地点的窖穴、墓葬和房屋叫作遗存;还有的人干脆把一个地区的古代物质文化资料都看成是遗存,等等。另外,象“建筑遗存”、“细石器遗存”、“植物遗存”、“文物遗存”、“近代遗存”之类说法,也不乏见。实际上,上述种种说法尽管在内容上巨细有别,在对象上涵指互异,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相对合理性因素,却构成了我们从理论上澄清遗存这一概念的出发点。
归纳以上说法,可以看到遗存具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遗存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既看得见,也摸得着,既是形象的,又是立体的。第二,遗存有一定的时间范畴,大致从人类诞生的旧石器时代至近代。第三,遗存以地下或地上为其存在形式。第四,遗存的内涵比较宽泛,小如一个米粒,大到一座古城,包罗巨细。根据这些特性,又可以把遗存划分为两大类,即人工产物和部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产物。前者应作为遗存的基本内涵,后者则是遗存的外延。
包括人工产物和部分自然产物在内的遗存,通常又被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范畴,象前面提到的窖穴、房屋以及墓葬等,即是遗迹;而细石器、器具、种子、人骨、兽骨等,则是遗物。目前,对遗迹和遗物进行过权威性界定的著作是《辞海》,即:遗迹是“指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窖藏以及游牧民族所遗留的活动痕迹等等。”遗物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①]。在这里,以工具或遗址等具象性事物来解释遗迹和遗物,显然只是通俗意义上的表述,而非本质属性上的揭示。这就犹如“什么是人?”的讨论命题一样,有的会说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张某李某王某;有的则说人属于自然界中生物发展阶段上居最高位置的灵长目,具有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以及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两种表述所具有的大众化和专业化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前者只不过是一种根据性别、年龄或称谓所做的简单分类,并没有涉及到非表象的本质意义。同理,将上面确定人类本质属性的做法之于作为遗存的两大范畴的遗物和遗迹,便会得到如下界说:遗物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可以移动并不会在移动中改变其形态的物质,遗迹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否则便会改变其形态的物质。
本文之所以强调遗迹和遗物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而不是象《辞海》那样限指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是因为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近年来诸如地震考古学、天文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沙漠考古学等边缘新学科的出现,一方面拓宽了考古学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原有内核,亦即增加了那些非人类本身但却与人类相关的自然遗物和自然遗迹的成份。当然,指出考古学研究的非人工成份,并不是要抹杀考古学以人类的遗物和遗迹为主体的研究重心,即使前面所撮举的地震考古学等分支学科,也不是对自然界的纯粹的研究,否则,考古学又何异于植物学、动物学、地震学、天文学和环境学等专门学科呢?所以,本文的用意旨在借此明晰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广泛性,并且这种广泛性又不是单独的遗物或遗迹所能涵盖的,故必须冠以新界说,即遗存。
考古学中所见到的遗物和遗迹,都是人类在与社会或自然界的交往中所创造和利用的物质的结果,是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因此,所谓遗存,就是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物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界的物质。
考古学家只有通过对遗存的研究,才能复原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场景,才能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这种研究又是通过收集遗存、整理遗存和解释遗存这样三个过程来实现或完成的。
二、收集遗存的过程及其方法
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遗存,但客观存在的遗存本身却不会对考古学复原历史发挥任何作用。只有根据科学的方法将自在的遗存收集起来,进而进行整理和阐释,才能使遗存成为研究历史的真正资料。所以,遗存的收集过程应当是考古学研究的伊始或第一步。
遗存在自然或人为活动的作用下,常常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有的被埋入了地下或水下,象北京猿人遗址、青铜器窖藏、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泉州宋代沉船等。也有的存留在地上,如敦煌石窟、好太王碑、明代长城、乐山大佛、阴山岩画等。还有的流传在世上,诸如书画、玺印、钱币、玉器等。正因为遗存有如此诸多的存在形式,所以,遗存的收集方式也就各有不同。
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看,收集遗存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文献检索法。很多遗存是在发现后做过图文记载的,其中有些遗存保存了下来,但也有很多遗存因各种原因消失或看不到了。对于考古学来讲,已消失的遗存的文献记录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如宋代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就记录了839件宋代以前的古铜器,并且对每件器物都从图形、比例、款识、大小、容量、重量、考释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记载,特别是该书所定的器物名称,有很多沿用至今。再有象西晋时汲县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等简牍,尽管到宋代已经佚失,但由于进行过辑补工作,所以一直成为夏、商、周代纪年等方面研究的必引文献。另外,在关于龙山文化是否已有铜器的讨论中,人们发现清代《西清古鉴》中著录的一件铜鬶与龙山文化所发现的陶鬶极为相似,因此这件铜鬶常常被作为龙山文化已出现铜鬶的间接证据”[②]。实际上,诸如此类的遗存著录,在正史、杂史、传记、方志、乃至笔记小说中均不乏见,甚至现代流散在国内外的文物,经过著录而成为考古研究重要参考资料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如良渚文化的玉器等”[③]。总之,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对那些已被著录的遗存进行分析,加以鉴别,去伪存真,不但可以补充和丰富现有遗存的种类和内涵,而且还可以使之成为更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第二种是征集抢救法。遗存中的很多遗物是世代相传或未经科学发掘而流散在民间的,征集和抢救这样的遗物,也是收集遗存的重要内容。象吉林省征集的《文姬归汉图卷》、天津市征集的太保鼎和小克鼎以及我国最早记录月食的卜辞、北京市拣选的班簋、苏州市征集到的元代银槎杯等等”[④],都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根据征集和抢救的遗物,还会索骥追踪去发现某些重要的古遗址或古墓葬等遗存,象云南省著名的石寨山古墓群,就是以拣选到的虾蟆纹桃形铜矛和铜钺为线索而发现的,进而揭示出古代滇人文化的秘密。同样,昆明市西山小邑村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也是在拣选了一件有段石锛并记录了来源之后,进行追踪调查,继而昭示于世的”[⑤]。所以,对已失去共存关系和层位关系的流散文物,在征集或拣选时,要尽可能地了解其来源、出土地点、原存状态以及共生的其它遗物,以增加这些资料的科学价值和利用价值。除了对遗物的征集之外,对遗迹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也是收集遗存的有效手段。例如为配合全国重点工程三峡的建设,全国共有近20个科研单位和大学参加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大规模考古抢救工作,共抢救发掘了遗址、墓葬、窖址等200余处,揭露面积2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⑥]。
第三种是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阶段,而且也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甚至还可以有目的地完成特定的考古任务。田野调查之所以不同于下面还要提到的田野发掘,就在于调查工作是适合于在大范围区域内展开,并且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了解并获得大量的、科学的资料。象晋、豫、鄂三省组织的联合考古调查,就摸清了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诸遗存的概况,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提出了对晋国早期都城遗址、河济之间的夏商文化以及先楚文化等问题的认识和对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设想”[⑦]。
第四种是试掘钻探法。埋藏在地下的遗存是难以数记的,要全部发掘众多的遗存,显然会受到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等因素的限制。同时,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对已经发掘过的遗存的保护能力,也还存在着许多尚需攻克的难题,象古尸的防腐问题、壁画的退色问题、植物种子的风化问题、铜器的霉斑问题等等。另外,对类似于郑州这样的现代城市几乎直接叠压在古代城市之上的地区,要进行全部发掘,自然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地下遗存的内涵、分布和保存情况,就往往采取局部试掘或全面钻探的方法来收集或观察遗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试掘和钻探也是获取考古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第五种是田野发掘法。作为近代考古学区别于古代金石学的最重要的标志,田野考古发掘被认为是收集遗存并澄清遗物与遗迹自身或相互之间关系的最理想的手段。而且,更完整的发掘还应当是对整个遗址的全部揭露和对各种遗迹现象的全部记录和取样,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和科学地得到遗存在布局、组合、共存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信息,才能为接下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详实巨细的资料。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墓地和临潼姜寨遗址之所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去它们的遗存本身所具有的典型性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对它们的全部揭露并在此基础上较全面地公布了发掘资料,以至于使它们分别成为研究史前社会组织制度和聚落形态的范例”[⑧]。如果说考古调查是从“面”上了解各种遗存的分布情况的话,那么考古发掘就是具体地解剖一个“点”。这里又要强调的是,这种“点”的解剖要以层位学为依据,并严格坚持考古学发掘的“三要素”原则:第一,据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和遗迹等现象。第二,由上及下、由晚及早地进行发掘。第三,按单位归放遗物”[⑨]。
三、整理遗存的过程及其方法
为了使收集到的遗存进一步地为研究所用,就需要对各种标本和遗迹现象以及记录进行整理,因此,整理是考古学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过程。
通常的整理,是根据遗迹和遗物关系并按层位学和类型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的。它既包括器物碎片的拼对、修复、登记、统计、绘图、照相、造册、又包括对遗迹现象、自然物乃至可能有的文字进行鉴定和考释,还包括在层位学基础上对遗迹特别是遗物进行类比分析,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服务的,那就是确定已收集到的遗存的年代关系和空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考古简报或考古报告。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收集到的各种遗存确定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中,并弄清他们的发展系列和异同关系,不但可以为解释遗存创造条件,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研究。
在对考古遗存进行的整理中,目前有两种年代学的定位概念被经常地采用,即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前者指比较明确的具体年代,如隋唐长安城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后者指难以确定具体年代,而只能推定遗存之间早晚时序的大致年代,比如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绝对年代的确定既可以采用自然科学如C[14]测定的方法,也可以采用社会科学的手段,如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有文字的遗存的年代,象甲骨文、金文、货币、墓志、碑刻等等。但从实际情况看,没有文字的遗存是大大多于有明确文字记录的遗存的,所以,考古学研究往往采用相对年代来确定遗存的存在阶段和位置,对史前时期的遗存来说尤为如此。
确定遗存的相对年代,主要应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手段。考古学中的地层,由于土质土色的不同而呈现出上下堆积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有早晚区别的。即早期的堆积在下,晚期的堆积在上,晚期的堆积叠压或打破早期的堆积。所以,通过这种探讨堆积时序关系的层位学手段,无疑可以确立遗存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梁思永先生1931年在后冈遗址的发掘就是按土质土色区别出“三叠层”,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商代、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序列”[⑩]。如果说层位学的考察最适用于确立一个遗址中遗存之间的相对年代,那么类型学在确立相对年代方面却要比层位学有着更广泛的功能,因为在层位学基础上通过类型学手段所确定的典型遗存及其序列,往往具有文化标尺的意义,它可以跨空间地衡量异域的遗存。如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确立以后,不但解决了二里头遗址本地遗存的年代关系问题,而且远至山东的岳石遗存甚至更南部的上海马桥遗存,也都因器物类比的相似性,而解决了所处的年代问题。由此可见,即使互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层位关系,但只要确立了一个典型遗存的时序标准,并以类型学的比较为途径,哪怕只有一、二件器物或一、二个组合,也可以标识遗存的相对年代。
类型学不但具有确定遗存相对年代关系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对遗物和遗迹进行排队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确立考古学文化乃至于更大时空范围内的遗存的区、系服务。俞伟超先生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和张忠培先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就是用类型学方法来研究遗存的具体实践和科学总结,颇值得一读[(11)]。而本文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类型学的作用不仅应当反映在收集和解释遗存的过程中,而且更应当贯穿于整理遗存的始终,并使其操作结果呈现在遗存整理的最终形式——考古报告或简报中。
如果说近代考古学的水平,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运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程度,那么,作为记录这种运用程度的载体——考古报告或简报的编写来讲,也反映出编写者是否具有科学的整理意识和手段。所谓科学的整理意识和手段,就是严文明先生在读过《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后引述尹达先生的话,即“使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较全面、较系统地反映出某一类型文化遗存的社会面貌”,以及严先生在评述《姜寨》报告时进一步指出的“逻辑紧密,结构合理,文字简洁,插图、图版和表格等配合得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姜寨遗址的发掘成果”。[(12)]虽然这些话是针对新石器时代遗存而言的,但其提出的基本原则却应当是共通的。应当承认,尽管经过整理而形成的考古报告或简报有利于考古学本身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但目前仍然有很多遗存的整理者所编写的报告或简报不尽如人意。如:不区分地层堆积和遗迹堆积,只是零星地而非全部地公布所有单位的器物组合关系;只公布器物的探方号,不公布器物的单位号;只说明单位的所属层位,不标明单位的开口层位;一味描述墓葬而置灰坑等遗迹于不顾;沉溺于人骨鉴定但却忽略动物、植物的鉴定;等等。凡此种种,如果仅仅是整理水平或收集遗存的原因所致,尚可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学科发展进程的加快而得以提高或改进,但如果是有意地藏头去尾或据为己有,则就是学风和人品的问题了。所以,有人提出要点评《考古报告中常见错误一百例》,实在是有益于遗存整理的一个极具胆识的设想。
四、解释遗存的过程及其方法
苏秉琦先生指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发现(包括一些重大发现)仅仅是它的一个环节,它能给我们以启发,却不允许我们满足于现状。如何解释这些发现,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来指导我们正确地解释这些发现,才是最重要的”[(13)]。由此可见,前已述及的收集遗存和整理遗存的过程,事实上都是为解释遗存服务的。然而,服务不等于解释,或者说不等于解释的全部。换言之,经过收集而得到或经过整理而完善的遗存材料,其本身是否就能表述某种历史上的事件、场景和发生、发展过程等等问题,还要由遗存的内涵而定。
应当说,历史时期有文字的遗存,有些是直接记录了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的,如郑和下西洋时所刊刻的《太妃灵应之记碑》,就记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出发和到达地点等过程;再如甲骨文中也有某一个王在某次狩猎前的卜问和狩猎后收获的刻辞;等等。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船队为什么选择该时该地出发?为什么要至此地而不至彼地?另外象商王为何要狩猎?等等诸如此类的疑问,却是遗存本身没有回答或者未予解释的。有文字的遗存尚且如此,那么本身无文字的遗存也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即使是有文字的遗存,往往也不过是证明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以及发生在何时、何地而已。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问题,实在是包括有文字的记录在内的所有遗存都难以回答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仅凭遗存本身是很难复原历史的。
既然遗存本身在复原历史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那么是否就等于说,复原历史就主要是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的任务了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即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上来了。然而下述的讨论结果将证明,这个问题的澄清和辨证,的确有助于考古学乃至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通常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往往具备三个构成要素:一、研究的对象,二、研究的方法,三、研究的目的。在中国,考古学比起历史学来,还是一门本世纪初才出现的新兴的学科。只不过在过去,鉴于二者都是以复原历史为目的的共同性,所以考古学一直是一门分支学科,隶属于历史学。但近年来,由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逐渐明确,特别是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取得的成果日益丰富,其作为一门一级学科,已从历史学中独立了出来。其与历史学在某些方面的区别也就更加明显: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区别。考古学以田野发掘为手段,历史学以文献整理为方法。其次是研究对象上的区别,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存资料,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历史学和考古学各所依存的遗存资料和文献资料,互有不同的特性。首先看文献资料:第一,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献是不断地在破损、消失的,并且在传抄过程中,讹点日增。第二,文献是主观记叙的产物,故相当程度地融进了撰写者本人的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主观性较强。第三,文献偏重于记载历史上的大事件和有名的人物。第四,文献记录了许多非物质形态的事物,如音乐、舞蹈、意识等。其次看遗存资料:第一,遗存是不断地被发现、不断地增多的。第二,遗存是实物制品,客观性较强。第三,遗存更多地反映了一般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第四,遗存的实物属性使它具有了形象化的特点。以上对比告诉我们,遗存和文献的区别“在于各自均依据自身的不同研究对象,而猎取不同类别的信息。因此,狭义历史学只是研究反映研究对象的那一部分文献史料”“考古学所研究的只是物质遗存中反映其对象的那一部分信息”[(14)]。换言之,尽管二者共同之处都是以复原历史为目的的,但研究的方法和对象不一样。考古学所要和所能复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历史学所要和所能复原的历史,考古学是从遗存角度而历史学则是从文献角度,考古学是从田野发掘角度而历史学则是从文献整理角度来复原历史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遗存本身是能够复原历史的,只是这个历史是遗存所能够解释的那部分历史而不是全部人类历史,这就是考古学的局限性。同理,历史学实际上也有此局限性,所以郭沫若就针对历史学的研究说过“文献上的资料是不够的,必须仰仗于地下发掘资料”[(15)],这种办法也曾被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互为补充,各具功能,殊途同归,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当是如此。
“考古学遗存本身是形象的……要透过遗存探讨考古学文化所体现的那部分人类历史规律时,首先得把形象的遗存和它们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关系译成语言文字”[(16)]。这就是说,遗存的解释是考古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它的基础是遗存的收集和整理,而它的指向则是完成考古学复原人类历史的目的。目前,遗存的解释往往是在比较下完成的,比较的途径主要是文献资料、民族学资料和实验性研究。在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长期积累的文献传统和边远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活化石”,所以常常采取或比之于文献或比之于民族学材料的办法。而西方特别是北美,则因历史发展短暂和科学技术进步,多采用的是实验研究验证假说以及民族学调查相结合的办法。近年来,这种手段及其相关的理论也开始传入我国,如“新考古学”理论的引进、“民族考古学”的兴起等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找到一种解释遗存的途径所作的尝试。但国外的各种理论和学派是否适宜于中国这块土壤,是否能对中国特有的遗存作出合理的解释,尚是一个有待验证的未知数。实际上,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也已在考虑如何解释遗存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当有益的考古学实践,象“区系类型”、“谱系”、“文化因素分析”、“历史文化区和亲族文化区”、“聚落”等等理论与方法的提出、借鉴与施行,即是如此。
总之,遗存的解释与收集、整理相比,尚处在一个正在探索的阶段中。但既然存在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那么也就必然会产生出相应而且是完善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这已不是一个有无和能否解释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注释:
①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79),上海辞书出版社。
②高广仁等:《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1期。
③张明华:《良渚玉符试探》,《文物》1990年12期。
④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孟宪珉等:《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85年1期。
⑥蒋迎春:《9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9日一版。
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报告》,《文物》1982年7期。
⑧ (12)严文明:《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史前研究》1984年4期。又:《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12期。
⑨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5期。
⑩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张文同注(9)。
(13)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 (16)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12期。
(1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04期
- 0000
- 0001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