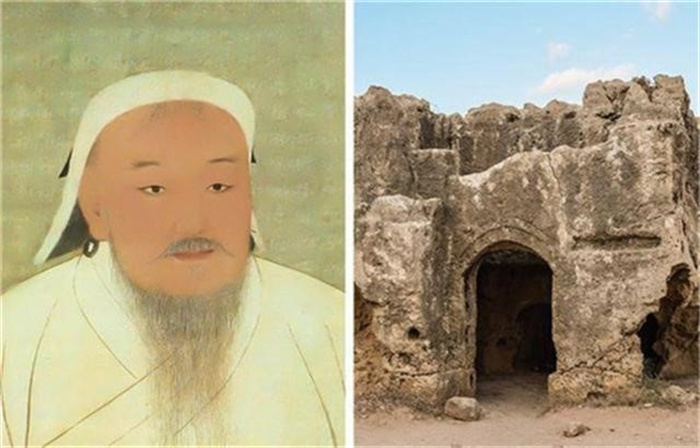陈胜前|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中国考古学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考古发现与研究方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在理论领域相对滞后。一般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以文化历史考古为主,而西方在文化历史考古之外还有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等等。然而,何谓“文化历史考古”,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面貌,文化历史考古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如何发展,如此等等,都是中国考古学界目前较为关注且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于文化历史考古的认识基本来自经典教科书,如以持论公允著称的考古史家特里格(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1]。但因为其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考古学者,书中着力回答的是一些西方考古学界争论的问题,这就使得其论述通常会忽略某些背景材料,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易理解;另外,作者也不了解中国考古学的需要,所以无法做出针对性的论述。本文不是对特里格论述的背书,而是一种运用“范式”视角的重新理解。同时,尝试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思考上述问题。
一、范式的视角
文化历史考古究竟是什么,争论颇多。西方考古学中,一般将之视为20世纪中叶之前,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而作为过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认为它还算不上范式,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2]。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过程考古学强加给文化历史考古的名称,有意将之固化为某种刻板的形象[3]。还有一些学者将之视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阶段[4]、方法[5]、视角[6]、运动[7]、解释倾向[8],或者是特殊社会政治情形中的学术适应[9]。韦伯斯特(Webster)对相关问题有很好的综述[10],在此不再赘述。
显然,如此众多的看法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视角有关。本文采用的是范式的视角,按照库恩(Kuhn)的原意,“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仰[11],它相当于一种思维框架或概念纲领,所有的材料收集、分析都围绕它来开展。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各有其擅长的研究领域。不过,较晚出现的范式在批评此前范式的基础上往往会拓展出新的研究范畴。本文则更进一步强调考古学理论具有一种分层与关联的结构[12],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联,通常称之为考古学内在的关联;另一方面是与社会背景、时代思潮、相关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可称为考古学的外在关联。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内史”与“外史”。
二、文化历史考古的性质与发展
(一)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逻辑
当前针对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中,更多侧重于典型文化历史考古理论基础的分析[13],过程考古学家的批评更是如此[14],而对于其形成与发展过程关注不多。这种偏于静态的研究有“树靶子”进行批判的嫌疑,文化历史考古其实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范式,它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不断变化的发展不等于文化历史考古没有一个共同的可识别的形态。文化历史考古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一种范式,关键点在于共同的逻辑基础。施瓦茨(Swartz)有精彩的论述[15],按他的说法,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设计可以分为七个步骤,归纳如下。
1.准备 初步了解基本的考古学问题与目标,即熟悉已有的工作,为野外工作做好技术准备。
2.材料获取 通过田野调查或发掘获得考古材料。
3.分析 把考古材料置于时空框架中,也包括使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考古材料。
4.解释 目标是要发现器物组合如何生产与使用。
5.整合 尽可能全面获取材料,重建古人的生活方式,通过综合建立更宏观的文化分类框架。
6.比较 也是整合的一种方式,与不同地区、时代进行比较。
7.抽象 解释、比较的最终目标是要抽象出理论或原理。
柴尔德(Childe)作为文化历史考古的代表人物,特里格认为他后来走向了“功能主义考古”,偏离了文化历史考古。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其实贯穿其中的还是这种内在的逻辑统一性。晚年的柴尔德写作了《社会与知识》(Society and Knowledge)一类具有哲学色彩的著作[16],代表文化历史考古最后步骤的理论提炼。柴尔德的学术历程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的步骤。
(二)文化历史考古发展的五个阶段
回顾文化历史考古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主题。
文化历史考古第一阶段的发展是在西北欧地区,代表性的成就是汤姆森(Thomsen)提出“三代论”,以及沃尔塞(Worsaae)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与史前生活方式的研究。这个阶段是文化历史考古的萌芽阶段,它着重解决如何对实物材料进行正确分类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断相对年代。同时,沃尔塞近乎前瞻性的研究已经预示了文化历史考古同样关注古人的生活面貌,而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形态。
文化历史考古的第二阶段是以蒙特留斯(Montelius)为代表的分类描述时期,拜赐于当时的铁路建设与博物馆的建立,蒙特留斯可以便利地旅行考察,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到整个欧洲的史前考古材料。然后,他在汤姆森“三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详细的史前史框架。同时,田野考古工作更加系统,出现了如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这样的发掘大师,初步建立起严格的田野考古方法。文化历史考古经常采用的严格的类型学与地层学方法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19世纪后半叶是“古典科学大厦”完工的时期,也是诸多社会科学初步形成的时期,其中包括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考古学也是在这个阶段初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不断受到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的影响。这对于文化历史考古下一阶段形成自身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
文化历史考古的第三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代表人物是科西纳(Kossinna),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来统合考古材料,并以之来研究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渊源[18]。在科西纳之前已经有其他考古学者用到这一概念,但科西纳显然扩大了其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要建立起考古材料与族群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一定时间范围内分布在一定区域的考古遗存的共同特征为基础建立起共同的“文化特征”,也就是一个群体所共同的“文化标准或标志”,这些特征使得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的集大成者,他在科西纳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地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构建欧洲史前史体系,成为文化历史考古第四个发展阶段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标志性的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的构架并不只是欧洲不同地区史前文化的年表,而是综合考虑到了各地区的文化(文明)形态、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19]。这也是下一阶段柴尔德推动文化历史考古转型的基础。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再来看柴尔德学术生涯中后期的工作,就会注意到他在前期以分类-历史研究为中心,中后期转向分类-功能的研究,这也就是文化历史考古第五个发展阶段的特征。他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中东与欧洲史前史,提出著名的“两个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与城市革命[20]。这样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化历史考古的范畴。特里格将之视为功能主义考古的代表[21],但是柴尔德的分类-功能的研究与典型的功能主义考古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又有明显的不同。他的概念纲领还是文化历史考古的,没有像过程考古学那样将文化看作人适应环境的手段,视文化为一个具有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并与众多其他变量相互作用的完整系统;也没有采用演绎-假说的方法。
无独有偶,柴尔德的转向并不是唯一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考古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也转向对古人生活方式的研究[22]。北美地区的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在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的鼓励与理论(文化生态学)支持下,发展出聚落考古[23],在这方面张光直也有相当的贡献[24]。特里格将他们的工作单独称为“功能主义考古”,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研究与先前的考古学家一脉相承。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就是,文化历史考古本来就关注古人的生活方式。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也表明所谓功能主义考古是文化历史考古的自然延伸。
三、文化历史考古的概念纲领及其问题
(一)五个理论前提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是考古学发展过程中最早形成的范式,其称谓是后来研究者添加的,当时的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研究属于某个范式。范式存在的前提是共同的概念纲领,因此分析其核心概念是理解文化历史考古的关键。韦伯斯特对此有精彩的归纳[25],对于他所归纳的五个理论前提,这里基于我们的理解再做进一步阐释,以便大家参考。
1.文化可以拆分 文化历史考古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即以文化的历史来指代人类的历史,文化即人,这是从广义上或整体上而言的。这样的认识来自文化人类学,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就曾对文化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所接受的一切的综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以及其他能力[26]。这里文化本身就是各种表征的综合,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视角强调文化某个方面的属性。
从狭义上说,“文化即人”衍生为“一个文化指代一个社会群体”,这里文化不再是一种作为人类普遍特征的整体性认识,而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对象,它有了存在的单位,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边界。
2.作为标准或规范的文化用一个文化来指代一个社会群体,这就意味着群体中每个成员共同分享某些共同的文化“标准”,从而将所有成员定义为同一群体。过程考古学先驱瓦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27]以及后来的过程考古学家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28],一般称之为文化历史考古的“心灵主义”倾向,即文化是由观念构成的心灵构建[29]。基于此,考古材料特征的共性成为确定一个文化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材料内在的差异性可能被忽视,这是博尔德(Bordes)与宾福德(Binford)两人之间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30]。
3.文化是流动的 基于对现代社会的观察,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影响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文化特征由中心区域起源,然后向其他地区传播,宾福德将之形容为“涟漪”——文化特征像水波一样从中心向周边扩散出去,越边远的地区,该文化特征出现的时间越晚[31]。按特里格的说法,传播论的流行与19世纪末人们认为发明是很困难的认识相关,近东作为驯化与文明的中心,逐渐向欧洲扩散;这也暗合基督教的教义——伊甸园在近东,人类由此向周边扩散[32]。但是,传播论无法解释文化特征起源、选择与接受的原因与机制。
4.文化是由一系列特征构成的单位 从人类学作为整体的文化到文化历史考古中具有单位意义的文化,就需要从模糊的、整体的判断走向明确的、特殊的判断,这里文化是由一系列特征构成的颗粒状(particulate)单位。这种观点与文化历史考古学兴起时人类学中流行的博厄斯(Boaz)的文化观是一致的,即文化是一系列明确的静态特征的组合。博厄斯式的观点是反对文化进化的,20世纪40年代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反其道而行,提出文化进化论[33],从强调特征的文化观再回到强调一般性的文化进化观,即功能意义上的文化,成为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进化论考古又注意到文化特征,把它们看作类似于基因的表现型(phnotype),受制于进化论的规律[34]。不过,进化论考古的目的与文化历史考古迥异。
5.这种单位就是考古学文化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文化历史考古构建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这个概念除了具有时空框架的意义之外,同时具有指示社会人群的意义。一个考古学文化地理范围的大小、延续的时间长度并没有一个客观、通用的标准,许多时候要依赖于考古学家的主观判断。就像曾经的“仰韶文化”分成了若干个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变成了“龙山时代”[35]。
文化历史考古的这些理论前提很少会单独提出来,以至于有学者如戴维·克拉克怀疑文化历史考古是否有像样的理论基础。过程考古学者通常批评这种将理论前提暗含在推理之中的做法。实际上,理论前提的不明确并不是文化历史考古所特有的。即便是在自然科学中,也有无法完全证明的理论前提存在,过程考古学同样如此。
(二)文化历史考古的主要问题
文化历史考古饱受过程考古学的批评,成为不断萎缩[36]的范式。作为文化历史考古代表人物的柴尔德在晚年选择了自杀,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遗书中表明他对考古学能力的失望[37]。他所主张的考古学研究遇到了什么困难,下文将着重讨论这些问题。
文化历史考古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对考古材料的认识上。考古材料的属性丰富多样,不仅仅具有时空属性;它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宾福德认为它至少应该具有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意义[38];它还是一系列文化与自然过程作用的产物,并非所有的实物材料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39];再者,按后过程考古学的说法,它是能动的,反过来会影响人类社会的构建[40]。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的考古材料属性是相对局限的,更多侧重其形态特征,很少考虑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的关系以及物质材料对人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的范畴比较狭窄。简单地说,它更多侧重研究“何时”与“何地”的问题,而很少研究“如何”与“为什么”的问题,不能回答文化为什么变化、如何变化,通常简单地将变化的原因归结于文化传播。对于“是什么”的问题,只能根据研究者的常识或是直接历史法(通常限于土著居民还在原地生活的地区,人们知道考古遗存与行为的关系)进行判断;而不是像过程考古学那样通过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中程研究,以及科学分析来确立考古遗存功能上的意义,建立起考古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的普遍联系,以了解古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后过程考古学还要更进一步,它强调物质材料的文化意义,物质材料渗透了人的历史认识,通过物质材料研究可以重建当时精神范畴的内容[41]。这些都是文化历史考古所缺乏的。
前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研究范围的局限,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则指向了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方法。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研究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分成若干个层次来实现[42]。第一个步骤毫无疑问需要对材料进行分类,浓缩差异性,从而便于理解与交流。同时分类也是探索性的,不同的标准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然而,从分类特征联系到人类行为,以及了解整个人类过去,中间还有很大的鸿沟需要跨越。至少还需要了解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哪些文化与自然过程参与到了材料的形成过程。此外,还特别需要了解人类行为、社会、文化等运作的机制,哪些机制的作用会在实物材料上留下可以识别的形态特征。
简言之,考古推理既需要从下(考古材料)到上(理论)的研究,也需要从上到下的研究;既需要从古及今,也需要从今及古(中程理论)[43]。
四、中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
(一)文化历史考古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早期渊源是与西方古物学类似的金石学,但更强调金石古物作为文化传统承载者的作用,即所谓“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44]。古物承载着三代时期美好的政治理想,观物是为了影响人,这样的认识似乎与当代的后过程考古学更契合,充满了人文色彩。然而,金石学的人文性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过程中,其地位不断式微。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始于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的研究。安特生1921年发现仰韶村与龙骨山遗址之后,以李济、裴文中、梁思永等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主导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图存”精神激励下努力学习,成为第一代考古学家。这些中国学者许多从西方留学回来;或是长期跟随西方学者从事研究,如贾兰坡;或是与西方学者合作,如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考古学家黄文弼。西方考古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占主导的范式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因此,中国考古学首先引入的就是文化历史考古。
从外在关联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面对东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凌,学术阶层努力以独立的学术研究建立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也不会有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强烈的民族情怀其实与这种历史背景的联系密不可分。如今,当有学者在质疑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倾向时,实际上有脱离考古学的社会背景关联之嫌。而中国在重新开放国门、改革发展之时,仍然具有强烈的构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需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再以战争而是以文化的形式在影响中国。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文化历史考古本身也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文化历史考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从李济对“彩陶西来说”的反感到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坚守,以及苏秉琦等对多元融汇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探索,民族情怀都是重要的理念基础。
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关联来看,按张忠培的说法,“19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创造出了一个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到处涌现新的材料,不断冲破旧概念,处处需要新的解释与概括”[45]。随着考古材料的日渐丰富,建立史前史的时空框架逐渐成为可能,“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开始引入与推广[46]。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47],标志着中国文化历史考古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新的中国史前史框架[48]、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模型[49]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的过程[50]。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范畴内,中国考古学可谓建立了中国学派。
(二)中国考古学的功能主义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典型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内。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最主要的代表就是郭沫若之于中国奴隶社会形态的研究[51]。他从两个层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层面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基础出发探讨上层建筑;同时,他还受到毛泽东《矛盾论》的影响,“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52]。郭氏发现农民与农奴、耕奴不易区分,于是以地主阶级出现为突破口。他注意到,春秋之时,“初税亩”提出统一征税,承认地主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战国中期铁器耕作技术已经十分普遍。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中推导出可以在考古材料中验证的假说——铁制农具的有无,判断“黑田”(私有田地)的出现应该更早,为了追求效率,农耕中开始使用铁器应该可以早到春秋之时,这后来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他的研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过程考古学所主张的“假说-演绎”的方法。他还反过来研究汉代的意识形态,指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奴隶社会基础之上,当时的经济基础也不支持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而批评汉代还属于奴隶社会的观点。这里他从另一个层面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理论,即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哲学基础,它还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形态与机制的普遍理论。表现在旧石器考古-古人类研究领域,“劳动创造人本身”成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表现在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领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在墓葬分析[53]、聚落形态研究[54]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只是“假说-演绎”的方法少有其他学者应用。
回顾中国考古学研究史,除了历史考古领域持续“证史”、“补史”外,新石器-原史(夏商周)考古领域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属于文化历史考古。例如,张忠培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研究[55],以及近年来开展的良渚墓地研究[56],都有很强的社会考古的色彩,不同于以分型定式为中心的文化历史考古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历史考古也发生了明显的功能主义转型,关注古代社会的经济方式,如严文明的农业起源研究[57];还有学者通过聚落形态研究探讨社会组织的变迁[58]。在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良渚古城研究中,尝试从不同考古遗存的相互功能关联来重建良渚史前社会[59]。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则出现了以实验考古、微痕分析等方法为中心,以确定器物功能为目的的研究[60]。当然,这些研究都没有明确地提出不同于文化历史考古的概念纲领,所以我们仍然将其视为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但实际上已经功能主义化。
(三)中国考古学有关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
中国考古学中对文化历史考古的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批判“见物不见人”的类型学研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考古学[61]。这种批判就是后来所说的“以论代史”。当时基本考古材料的积累与分析都尚未完成,所谓“见物见人”必定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规律简单地当成了历史,这是苏秉琦批评的“一个怪圈”。后来他找到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探索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大课题,突破了另一个怪圈——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一统观[62]。对这两个“怪圈”的突破可以算是对“见物不见人”批判的回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逐渐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俞伟超《考古学新理解论纲》,通过十个方面的讨论来探索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63]。但是,所有的反思并没有在概念纲领——“考古学文化”上获得如过程考古学那样的突破,更没有如后过程考古学那样深入到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但是,这样的反思促进了文化历史考古的功能化,也就是类似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柴尔德与格拉汉姆·克拉克的古经济学方法。
近年来,最为系统的思考来自王巍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在讨论影响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因素时考虑到文化系统的诸多子系统,尽管没有提及文化系统的概念,但他肯定了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价值,明确了其概念的适用对象[64]。他也没有如宾福德那样从功能意义重构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人适应环境的除身体之外的手段。毫无疑问,文化历史考古是有价值的,就像物理学上相对论出现并没有否定古典力学一样,而是明确了其适用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要在范式层面上拓展考古学,一定需要从概念纲领上进行,不然不足以形成新的范式。相比较而言,过程考古学所进行的反思首先就是重构了“文化”的概念,建立起以文化适应研究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发展文化系统、文化生态与文化进化理论支撑,进而形成跨时空的具有普遍性的认识,也就是文化科学。在这个强调科学的范式研究中,研究逻辑是假说-演绎式的而不是归纳式的,即是从上而下的研究,从一般性的原理推导出可以在考古材料中检验的假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后过程考古学范式同样如此,它首先否定考古材料作为化石记录的可能性,将之视为可以反复进行不同解读的文本,“文化”成了符号、结构、能动性的体现等[65]。西方考古学范式的变迁,尽管有其自身的发展背景与内在逻辑,但其理论反思与构建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五、文化历史考古的前景
文化历史考古还有没有前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加以探讨,一是现实的必要性,即文化历史考古研究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二是文化历史考古是否能与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结合起来。
首先,从当前考古学研究实践的角度来说,文化历史考古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从考古学“透物见人”推理的层次来看[66],了解考古材料的特征并进行分类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如果将汤姆森提出“三代论”视为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近代考古学花了近一个世纪来完善考古材料的发掘和分类整理。文化历史考古在考古实践上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汲取,不能因为高层理论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而否定其在考古材料层面上的基础工作。脱离了考古材料的分类和描述,考古推理也无法进行。
其次,文化历史考古所提供的时空框架是进一步考古解释的基础,不论是“过程”还是“后过程”的解释都需要它,后过程考古学者也充分肯定这一点[67]。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重建史前史,柴尔德重建欧洲史前史的努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柴尔德利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建立起从考古实物材料到古代社会人群之间的关联,尽管考古学文化代表古代社会人群的理论前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
再者,文化历史考古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那些具有殖民或半殖民历史的国家在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仍旧需要文化历史考古[68]。文化历史考古特别适合探索民族或文明起源之类的问题,这也就使得它在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中一直是居于主流的研究范式。西方考古学在19世纪时也曾经非常关注族源与文明起源问题。随着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退潮,同时也随着西方考古学研究的发展,逐渐转向研究古代生活,文化历史考古的主导地位逐渐为过程考古学所取代。不过,这主要发生在人类学传统深厚的北美地区,而在历史学传统深厚的欧洲,文化历史考古研究仍旧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德国[69]。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狭义的文化历史考古仅关注考古遗存特征的描述、分类、时空框架以及传播外,文化历史考古也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关注考古遗存特征的分类,注意了解史前史方方面面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就发生了这种功能主义意义上的转型,中国考古学也有类似的发展历程。文化历史考古并非不关注功能,只不过其文化观相对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而言,更多是静态特征的汇集,而很少关注文化运作机制这样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过程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带有功能主义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就文化历史考古的未来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其概念纲领的适用范围。当前国内外的批评都认为其核心理论前提没有经过充分证明,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因此失去了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实际上,其理论前提存在问题与使用范围的延伸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起初用来追溯特定民族的史前史,它立足于风格或风格组合来定义社会群体的空间范围。这种定义对于定居农业社会的合理性要远高于采用流动生计的狩猎-采集社会(不同季节或不同功能的活动可能产生不同的物质遗存)[70],也要高于那些阶级已经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阶级可能使用不同的物质材料)。文化历史考古在研究文明起源这类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工作让人看到其核心概念并不是都有问题的,而是需要限定其使用范围,避免概念的滥用[71]。
有意思的是,考古学的发展似乎呈现出一种螺旋状的形态。随着后过程考古、进化论考古等诸多新范式的出现,它们也开始强调文化特征描述。因此,张光直用“分”、“合”来表示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之间的关系[72]。当然,这种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后过程考古所强调的描述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描述体现的是关联性,进而具有阐释文化特征的意义。后过程考古视物质材料为“意义”所渗透,物质材料就如同“文本”,同样带有重要的信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能动性,能够影响到人。这种“拟人化”的文化观或许可以为文化历史考古所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普劳丁(Spaulding)与福特(Ford)之间有关类型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设定的争论[73]就可以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这里我们需要拓展对文化特征的理解,它不仅具有时空的意义,也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还是人类价值的载体。采取这种包容的方式,文化历史考古有可能融入过程与后过程考古的理论成果。
文化历史考古若能拓宽对文化特征意义的理解,那么它就可以融入到更深入的“文化考古”的范畴之中[74]。文化考古是一个分层-关联的框架,文化历史考古是其中特别基础的一环。文化考古强调考古材料作为文化的产物,可以从科学与人文两个角度同步展开研究。而在西方考古学中,莫里斯(Morris)借鉴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强调从不同层面来研究文化历史,如地理的、社会的、个体的等等,建立以事件叙事为中心(event-oriented narrative)而不是以物质材料为中心的“新文化历史”[75]。
文化历史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体,关于其发展学术争论与訾议颇多。本文采取一种注重内外关联的范式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化历史考古。它是近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个较为完善的范式,经历了至少五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文化历史考古之所以能够统合在这一名称之下,关键在于内在一致的研究逻辑。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柴尔德考古学等仍旧称为文化历史考古。我们特别强调,文化历史考古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理论前提未经证实,而在于它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的局限。从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到后过程考古,考古学家对于考古材料、人类本身的研究在不断拓展与深入,它们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实际上又是统一的,都属于考古学“透物见人”研究的一个部分。文化历史考古并没有过时,重建史前史依旧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未来文化历史考古首先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探讨,重构其概念体系。新的理论研究表明,它可以从以器物为中心转向以事件为中心,还可以回到从整体角度看待文化,发展更包容的文化概念,走向一种分层-关联的文化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Clarke D.,Analytical Archaeology,xiii,London:Methuen,1968.[3]Lyman R.L.,O'Brien M.J.,Dunnell R.C.(eds.),Americanist Culture History:Fundamentals of Time,Space,and Form,New York:Plenum,1997.[4]Willy G.R.,Sabloff J.A.,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ed,San Francisco:Freeman,1980.[5]Trigger B.,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6]Preucel R.,Hodder I.(eds.),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 y,p.6,Oxford:Blackwell,1996.[7]同[5].[8]Trigger B.,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p.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9]Trigger B.,Time and Traditions:Essays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8.[10]Webster G.S.,Cultural History:A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pp.11-27,Lanham:Alta Mira,2008.[11]Kuhn 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2]陈胜前:《考古学理论的层次问题》,《东南文化》2012第6期.[13]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14]Binford S.R.,Binford L.R.,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Chicago:Aldine,1968.[15]Swartz B.K.,A Logical Sequence of Archaeological Objectives,American Antiquity,32:487-497,1967.[16]Childe V.G.,Society and Knowledge:The Growth of Human Traditions,New York:Harper,1956.[17]同[5].[18]同[5].[19]戈登·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20]戈登·柴尔德著,安家瑗、余敬东译:《人类创造了自身》,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21]同[5].[22]Clark J.G.D.,Excavations at Star Car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23]Willey G.R.,The Viru Valley Settlement Pattern Study,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p.153,Cambridge:Winthrop,1974.[24]Chang K.C.(ed.),Settlement Archaeology,Palo Alto:National Press Books,1968.[25]同[10].[26]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7]Taylor W.,A Study of Archaeology,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69,1948.[28]Binford L.R.,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Process,American Antiquity,31:203-210,1965.[29]Renfrew A.C.,Bahn P.G.,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and Practice,London:Thames & Hudson,1991.[30]a.Bordes F.,De Sonneville-Bordes D.,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bility in Paleolithic Assemblages,World Archaeology,2(1):61-73,1970.b.Binford L.R.,Interassemblage Variability the Mousterian and the "Functional" Argument,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pp.227-254,London:Duckworth,1973.[31]同[28].[32]同[5].[33]L.A.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34]Dunnell R.C.,Evolutionary Theory and Archaeology,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3:35-99,1980.[35]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36]a.Price T.D.,Feinman G.M.,The Archaeology of the Future,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A Source book,pp.475-495,New York:Kluwer/Plenum,2001.该文中统计了不同范式的研究在数量上的变化.b.Watson P.J.,Does Americanist Archaeology Have a Future? Essential Tension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pp.137-142,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3.该文统计了美国考古学年会中相关讨论小组的数量变化.[37]Barton H.,In memoriam V.Gordon Childe,Antiquity,74:769-770,2000.[38]Binford L.R.,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28:217-225,1962.[39]Schiffer M.B.,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7.[40]Hodder I.,Reading the Past,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41]Hodder I.,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y,8:1-26,1985.[42]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透物见人”问题》,《考古》2014年第10期.[43]同[41].[44][北宋]吕大临编撰:《泊如斋重修考古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45]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46]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47]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48]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4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50]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5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2]毛泽东:《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2008年.[5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5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55]同[53].[56]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57]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58]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5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考古》2015年第1期;《杭州市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与美人地和扁担山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期.[60]高星、沈辰主编:《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学实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61]严文明:《走向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62]同[49].[63]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64]王巍:《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14年第12期.[65]陈胜前:《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东南文化》2013年第5期.[66]同[42].[67]Hodder I.,Introduction: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ebates in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pp.1-13,Cambridge:Polity,2001.[68]同[5].[69]同[10].[70]a.Thomson D.F.,The Seasonal Factor in Human Culture,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10:209-221,1939.b.陈胜前:《考古学的文化观》,《考古》2009年第10期.[71]陈胜前:《当代考古学概念的构建》,《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72]陈星灿:《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见《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2013年.[73]a.Spaulding A.C.,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ifact Types,American Antiquity,18:305-313,1953.b.Ford J.A.,Comment on A.C.Spaulding'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ifact Types",American Antiquity,19:390-391,1954.[74]陈胜前:《文化考古刍议》,《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来源:《考古》2018年第2期
- 0000
- 0001
- 0001
- 0003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