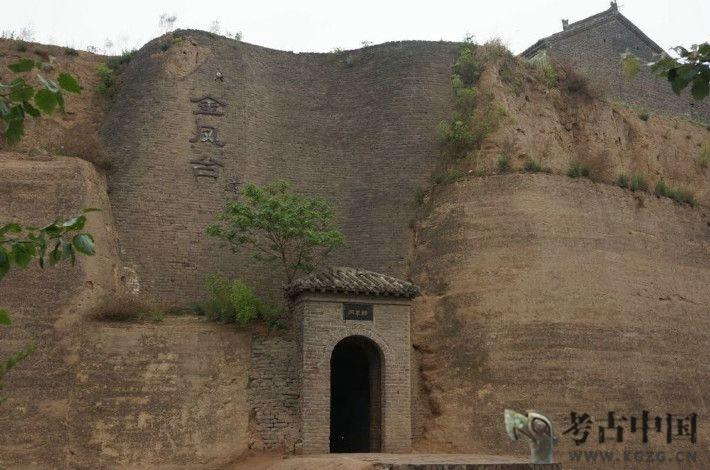张海:景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景观(Landscape)是西方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十分常见的概念,尽管不同研究者和不同的学术传统对景观的理解和解释千差万别,但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现象学和解释学等哲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渗透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大量新技术手段的推广应用,景观考古学(Landscape Archaeology)从理论方法到实践应用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考古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关心景观的概念,景观考古学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类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的文献中。然而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究竟什么是景观?如何理解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景观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即是对西方考古学文献中的景观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系统整理和讨论。
一、景观的概念及其演变
在西方文化中,景观是一个近代以来才兴起的概念,曾与艺术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角度反复理解的复杂概念。
景观概念的缘起:英文里的景观一词源自荷兰语,最初指的是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的构图方式,即采用线性透视方式构图的风景画(Olwig 1993:318)。有研究者指出,从17世纪开始发展成熟起来的景观风景画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土地风物进行透视描绘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土地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测量、分割、买卖和租赁,而景观风景画则直接从视觉上反映了人们是如何观察、理解、评估和转换置身其中的土地的价值,比如对田园农牧生活、乡村异域风情等的描绘(Cosgrove 1984:27)。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非熟悉景观的理解、阐释和重建,成为庭院、园林等景观设计的思想内容(Hirsch 1995:2)。
地理学和生态学中的景观概念:19世纪初,景观一词率先被德国地理学和植物学家洪堡德(A.von Hunboldt)引入到地理学的研究中(Naveh and Lieberman 1984:356)。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景观的概念在地理学中逐步得到系统的阐释和广泛的应用,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和核心。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德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帕萨格(S.Passarge)、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美国的索尔(C.Sauer)和前苏联的贝尔格(Л.C.Bepr)。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景观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景观是客观存在于地表,并具有一定结构的地理区域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第一是地表可见地理现象的综合,其中包括了所有的自然(地理圈、生物圈)与文化(人类活动)的格局和过程;第二是限定性的区域,景观成了用来描述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最小单位(肖笃宁等2003)。
事实上,景观在地理学中最大的贡献是与生态学的结合而促成了景观生态学的诞生和发展。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特洛尔(C.Troll)于1939年提出,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早期景观生态学关注的是区域地理学和植物学的结合,服务于土地的利用规划和决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景观生态学在全球尤其是北美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观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前沿学科。如前所述,景观是一个限定性的区域,在自然等级系统中比生态系统高一等级,而景观生态学是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关注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的空间结构,并强调这种空间结构的异质性特征(spatial heterogeneity)及其维持和发展。景观生态学在景观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理念的支持下研究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和动态变化,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大区域生物种群的保护、环境资源的管理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构成的影响等等。重要的一点是,在景观这个层次上,基础性、低层次的生态学研究可以得到有效的综合,从而为多学科交叉的生态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平台。近年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统计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大量应用到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使其迅速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热门学科(肖笃宁等2003)。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景观概念与地理学和生态学相比,景观的概念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则更加趋向于人本主义。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地理学家索尔就将文化景观从自然景观中划分出来,强调了景观概念中的人类文化行为(Sauer 1925)。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加达默尔(H.G.Gadamer)的解释学和布迪厄(P.Bourdieu)的实践理论使得景观的概念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展。这些新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推翻传统的景观概念中景观作为客体和世界图像(world image)而人类作为外部世界观察者的主客对立,从而强调了人类参与(human involvement)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景观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载体的结构性特征(Hirsch 1995)。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景观的概念在两个方向得到了新的诠释:第一,景观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即人类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文化认知。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视觉景象(vision),而人类观察外部世界的认知活动通过重复性的社会实践而被结构化和概念化,从而赋予了其符号和象征的意义(Morphy 1995),比如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第二,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载体。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要通过人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意义,从而转化为地点这个社会文化概念,而景观研究则正是对这种转化方式和转化过程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被定义为地球表面联系一系列相关人类活动地点的空间网络关系(Thomas 2001:173)。因此,Ucko认为,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景观,景观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构成,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景观结构(Ucko 1994:18-19)。
总之,景观是一个复杂且应用广泛的概念,除了上述学科之外,在经济学、建筑学、旅游学、文化遗产管理等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阐释和应用。如前所述,艺术家将景观看作是表现与再现自然风景的创作对象;地理学家将景观看作是综合自然地理区域;生态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把景观看作是社会关系网络。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体系,建筑师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将其作为建筑物的背景来处理,旅游学家将景观作为一种资源,而文化遗产管理者则把景观看作是文化遗产构成的整体而加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的学科对景观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这些概念都涉及到了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以及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关注和研究,也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景观的概念也在考古学研究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二、考古学中的景观概念
考古学对空间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史研究还是对聚落形态的考察,空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考古学家所关注空间概念的角度却有着鲜明的差别。传统的文化史研究中,空间实际上更多倾向于区域性或地域性的差别,空间概念仅仅是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遗存组合的空间分布的差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分析,更谈不上对地表空间构成要素的研究。空间分析虽然普遍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光直1986),然而长期以来聚落考古中的空间分析却多集中在对遗迹、聚落或遗址本身的分析方面,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的空间结构、不同类型遗迹之间的空间布局、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等,但却将对遗迹遗物、聚落遗址等所处的生存环境、景观生态的研究简单地置于环境考古学的范畴中,而缺乏对遗迹之间、聚落之间或遗址之间承载人类活动的复杂地表空间要素的充分关注。
实际上,与聚落形态考古中以遗迹和聚落为核心的空间分析相对应的是对地表遗物的空间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地表空间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在英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就是所谓的景观分析。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在英国Cranborne 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Pitt Rivers 1887)。20世纪中后期,在聚落形态考古兴起的同时,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并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被定义为遗址(sites)的人类活动的“热点区域”(hot spots)之外。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所谓的“非遗址”考古(siteless archaeology)(比如Dunnell 1992)、“遗址外”考古(off- site archaeology)(比如Foleyr 1981)、“分布式”考古(distributional archaeology)(比如Ebert 1992)的概念以及冠以“景观考古”(landscape archaeology)为名的研究(比如Gosden and Head 1994; Yamin and Metheny 1996)开始广泛出现。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对发生在遗址之外的人类活动的思考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是对以聚落遗址为中心的一定人类活动半径内的生计资源的考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希格斯等人早年的工作(Higgs and Vita- Finzi 1972);其二是推动了对遗留于聚落之间人类活动遗存的研究,比如聚落间的土地利用、农田系统、道路网络等等,而这也正是以遗址为核心的传统考古学研究中所忽略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使考古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活动与其所处的土地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了考古学对景观的研究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诞生。
最早在理论上对景观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因此早期考古对景观的研究更关注人地关系。从人文地理学对景观的理解出发,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点在于区域内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构成和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景观被看作是人类持续性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在不同类型的地表地物和空间要素体上的累积性的记录,是我们通往真实过去的有效途径(Daniels 1989:196)。这些研究多采用区域调查、文献检索、地图测绘和选择性的试掘等方式,力图去揭露景观演变历史的阶段过程(Aston and Rowley 1974)。从考古资料的运用上,这种研究更强调对散布于地表的人工遗物的系统考察,因此一些研究者直接将景观考古定义为一种以地表遗物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Bahn 1992)。除了人文地理学之外,生态学概念上的景观也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过去一定历史时期内区域性地貌的复原和地表植被的重建上。研究手段则依赖于考古发掘或调查取样所获取的古环境和古植物遗存,尤其是对孢粉的研究(比如Godwin 1975)。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学研究中的景观概念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景观考古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人文地理学和生态学背景下的景观考古主要从人口增减、社会互动、经济资源等方面研究古代景观,更多关注地貌、技术、资源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内容,也就是人类对土地的行为以及土地资源如何促进或是限制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人类如何认识和思考其自身所处的外部生存环境(Bender et al.1997)。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批判过程主义的景观研究的普泛化(generalisation)和其中难以避免的环境决定论倾向的同时转而强调文化象征意义、个体实践活动和社会认知、权力等的结构化过程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重要性(Morphy 1995:186-8),从而将景观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人地关系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角度。人类生活其中的土地不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自然资源,而是被看作为各种社会表达(social expression)的媒介(McAnany 1995)。从这个视角出发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空间载体,并且在个体重复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赋予具体的文化意义(Barrett 1991:8)。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景观被看作是一个需要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情境化(contextual)的概念(Johnston 1998: 56)。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将考古学的理论探索从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张海2003:16)。同样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基础,后过程主义背景下的景观考古学研究被看成对过去人类社会“在世”(Being- in- the- world)经验的复制和重建(Tilley 1994:12),而这正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景观考古学的主流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手段的空间信息综合分析和应用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大量景观考古研究的传统技术方法,如区域调查、地图测绘、孢粉分析、土壤检测等通过GIS技术得以系统地整合,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对景观分析中的诸多空间要素的描述逐步从定性转入到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景观分析的有效性。
总之,理论和方法上的成熟和进步使得景观考古学逐步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三、景观考古学
什么是景观考古学?综合上文可见,与景观的概念一样,景观考古学与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联系密切,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定义来概括它复杂的内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当代考古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回顾学科的发展历史,景观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复杂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均来自其他人文或自然学科,如艺术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因此可以说景观考古学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理论,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随着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点与聚落考古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也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与聚落形态考古等所不同的是,景观并不是古代人类的遗留,概念上它既是一种地表形态,同时更是一种文化观念。尤其对于后者而言,考古学不能直接研究古代景观。实际上,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解释问题的独特视角,一种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体,也正因此景观考古学才具有了作为考古学研究分支学科的鲜明特征。综合前文,景观考古学有如下四个重要特征:
其一,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的关注和考察是景观考古学的基础。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是一个物理概念,指构成地球表面的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既包括地形地貌、河流山川等自然地物,也包括植被覆盖、土壤矿产等自然资源。景观概念中的地表构成具有空间异质性的特点,即地表构成要素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在生态学上是生态多样性的基础,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则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自然基础。地表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这个概念上的景观可以看作是人类日常活动的载体。聚落考古在田野操作的层面上有一个“活动面”的概念,被看作是“遗址上承载一个时期内全部人类活动的地面,是一个开放的二维平面”(赵辉1998)。实际上,如果将这个活动面扩展到遗址外,并考察其表面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与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景观考古学所关心的内容了。
其二,人类的空间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是景观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由景观概念的人文主义色彩所决定的。从研究的内容来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并无差别,都关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不同的是景观考古学以景观为视角开展研究,探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如何依托于复杂的地表空间形态而进行的,以及人类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生存空间并将其纳入到不同的文化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地关系的研究不同,因为它不仅关注人地关系,更关心人的认知世界和社会关系,关心人地关系的社会化过程。
其三,景观考古学是一种区域性的研究。景观本身就是一个以区域为定义的概念。景观考古学虽然与聚落考古学一样都旨在研究古代社会,但所不同的是聚落考古研究的是遗址,而景观考古则同时更关心遗址之外。遗址是人类定居生活的集中遗留,但人类的活动决不仅局限在固定的聚落点上,聚落之间的联系也非简单的线性几何,而是会受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聚落形态考古也关心宏观概念上的区域聚落,但实际上多是区域内点的集合,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研究。一些研究者则更直接将景观考古看作是聚落考古的对立面,指出景观考古与聚落考古之间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点(place)和面(space)上的人类活动的区别(Tuan 1977)。田野实践中,景观考古学更多地依赖于区域系统调查,关注地表遗物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景观背景的空间异质性之间的关系,而通过抽样的方法获取反映区域环境历史特征的样品也是景观考古的重要田野工作之一。
其四,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景观既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内容和对象上,景观考古学所研究的是一个区域内的地理、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的综合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对特定区域阶段性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景观考古学需要广泛借助于地质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动物植物学、社会人类学和心理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制图技术、GIS技术、遥感技术、空间分析技术等多种技术手段,是集多学科、多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景观还必须要综合“遗址内(on- site)”与“遗址外(off- site)”的研究(秦岭等2010),既要研究人类活动本身,又要关注人类活动发生的空间背景,是真正意义上点面结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景观的历史演变、景观的复原和景观的社会学研究。
研究景观的历史演变也被称为“景观分析”,主要是通过“回溯式”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表景观的结构和特征。这种研究一般首先要以研究区域内当前状态下的景观为基础,寻求景观历史演变的线索。比如,地貌调查并结合以反映微地貌特征的大比例尺地图测绘。当然,通过必要的田野考古调查寻找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地表活动的线索才是进行景观回溯的最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另外,高时相、高分辨率和高光谱的遥感影像资料的分析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判断的作用。在景观考古的实践中,地貌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水系,包括河流、湖泊和海平面,因为无论是地表径流还是海平面都受到全球或地区性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河道和湖泊的变化还同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大规模的砍伐所导致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等。另一方面,河流水系的变化对人类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水既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须资源,同时河流作为视觉显著的“景观通道”也常常作为联系不同聚落的交通通道。因此,研究古水系的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景观分析中的首要问题(比如Muir 2000)。
有关景观复原的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区域特定历史时期地表生态系统的复原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植被系统。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依赖于对采集的古环境学样品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是对孢粉谱的研究,另外对考古遗址浮选的大植物遗存、植硅石等的分析也有助于进行植被景观的复原和重建。但是,在使用这些古环境学样品进行景观复原时,必须充分注意遗址内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由于遗址内的堆积经过人类的反复扰动,不能直接利用文化堆积中的古环境样品进行景观重建,孢粉分析应选取遗址外的自然地层。浮选的大植物遗存,包括炭化的种子和木炭,本身就是由人类活动所有意或无意带到遗址中,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些遗存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人类在遗址外活动的范围和活动的方式,以GIS为支持的遗址资源域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信息。
除了植被的复原之外,对地表土壤历史演变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土壤微形态的研究也是进行景观复原的重要手段。土壤微形态研究是在微观上研究土壤的组分、物像及垒结,其主要任务是将显微镜下观察、描述的土壤微形态特征及变化用来说明土壤生成、发育的演变规律,从而解释各种自然力量或人为因素对地层形成过程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土壤薄片的分析可以从微观上探讨过去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它反映人类活动特点的信息;另一方面,土壤微形态研究可以从残骸特征推断其成土条件、复原古土壤的发生特征,进而了解从古代的成土条件到现代成土条件的变化和土壤的发育历史(Goldberg and Macphail 2006)。
景观的社会学研究是近年来西方景观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实践中,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得以全面开展(Knapp and Ashmore 1999:13-19):
第一,研究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景观考古。景观被看作是记录社会和个体发展史的文化记忆的空间物化形式。在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反复的利用、阐释、修复、重建,景观不仅被赋予意义并纳入到社会的文化记忆之中,而且文化记忆通过景观的形式而突出了它的延续性(Schama 1995)。土地常常被看作是祖先的遗产,是祖先精神的延续,比如澳洲土著将祖先在同一景观中的活动看作是梦境中再现的内容(Morphy 1995:187),而新几内亚的当地社群则把土地看作是祖先的能量所在(Tilley 1994:58)。这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景观被赋予的多重社会文化意义是如何通过时代变迁而被承袭、积累、重述和再现的。
第二,研究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y)的景观考古。人类从事社会文化活动会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地点或区域,反过来这些地点或区域本身也会表达和强化已有的社会文化认同。有研究者指出,景观中的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能被不同的社会所给予特别的关注,并被赋予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含义(Bradley 1993:26)。这些重要的景观标志物或景观区域或者具有视觉上的凸出效果,或者是重要的生态区交界地带,也有可能是过去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区,既有可能为凸显的自然地貌,如山峰、河谷等,也有可能是高大的人工建筑,如神庙、祭坛等。重要的是,它们的作用都在于强化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空间认知和社会认同。比如,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关注的岩画研究就是一个实例,它们常常分布于生态区交界地带且同时视域开阔的地区,既是自然生态景观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活动边界线(Bradley 1991; 1997)。再比如对分布于世界各地高大的人工古迹(monument)的研究表明一些视觉显著的地点在营建大型建筑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社群标识为重要的“圣地”(sacred place)(Bradley 1997)。因此,重要的自然景观标志和社会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方面的景观考古研究关注的正是不同社会的文化认同如何体现在不同的自然景物上,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如何构建出了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景观的概念。
第三,研究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景观考古。任何人类社会都有自身文化结构中的空间秩序,同样不同文化结构中的景观概念也有其相应的社会秩序。所不同的是,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上看,对人类社会空间秩序的研究常常是聚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而从景观的角度研究社会秩序主要是探讨景观形态的多样性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特定文化结构中不同的自然景观形态与性别、年龄、身份、族群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划分和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组织结构、分层分化等方面的作用。例如性别考古学研究中考察特定的景观特征与性别图像或符号之间的联系,以及按照性别划分的景观区域与资源控制之间的关系等(Schmidt 1997; Jackson 1990)。而社会复杂化研究中,多样化的景观形态对人类空间位移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了早期国家对人口、资源、生产、信仰等的控制,例如海洋运输在希腊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evan forthcoming)。除此之外,我们常常谈到的聚落与墓地、不同等级的聚落与墓地在地貌景观选择上的差异等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而如果不同的景观特征与特定社会秩序结构之间构成了系统的联系,那么也就形成了景观考古学中所谓的“嵌套式景观”(nested landscape)或景观的“嵌套式特征”(nested feature)(Bender et al.1997),这正是景观反映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
第四,研究社会变迁(social transformation)的景观考古。无论是文化记忆、社会认同还是社会秩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景观考古同样关心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景观是长时段的人类活动的载体,代表了一定时空范围内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的综合体,因此景观的文化属性具有连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而景观含义的变迁正是这种稳定结构的变化。导致变化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环境的变化,如河流改道、海平面上升等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结构的自然基础;社会的变化,如人口迁徙、社会动荡等改变了原有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很多情况下,景观变化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正因为景观概念上的综合性的特征,其变化很可能预示着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农业社会的起源与景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Fuller and Qin 2009)。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成为考察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为考古学研究景观提供服务。但是,作为景观考古自身来讲,有两种最基本和最常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区域系统调查和GIS支持下的景观考古研究。
区域系统调查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是以全覆盖的形式发现遗址为主要目标。但实际上区域系统调查也是景观考古学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以景观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区域系统调查并非以发现遗址为目的,而是以观察地表遗迹和遗物的分布状态以及地表景观构成要素的现状和历史演变线索为目标,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活动与景观的关系提供一手的调查资料。区域系统调查有两种形式:全覆盖式和抽样式。无论是全覆盖式还是抽样式的区域系统调查都由数名专业人员参加,通过地表行走并纪录事先设定好的调查网格内的相关内容,完成对地表覆盖物的观察和纪录,其中地表覆盖物既包括各类人工制品,也包括土壤、植被等自然覆盖物。
以希腊Antikythera岛的景观考古调查为例。该调查项目同时采用了全覆盖式和抽样式的调查方式,全覆盖式调查重点在了解地表景观覆盖物,并确定考古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抽样式调查则在全覆盖式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地表遗物的分布模式。除了遗物之外,调查中对每个网格中的植被种类、覆盖密度、地表可视度、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型和侵蚀状况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纪录,并形成调查数据库。通过构建GIS的空间数据库,借助遥感和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调查获取的各类田野资料和已有的数字地面模型、矢量化的各类资源图、不同的遥感资料进行综合性空间分析,讨论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演变之间的关系,将人类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复杂性与景观的空间异质性联系了起来。这项景观考古调查项目取得了若干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比如调查发现的地表遗物的分布密度显然与植被覆盖的密度呈负相关,而遗物分布的模式又与土壤受侵蚀的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等等(Bevan et a.2008,2009; Palmer et al.2010)。由此可见,由区域系统调查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不仅能够为考古学研究景观本身提供直接的证据,而且也为讨论考古遗址的后堆积过程和考古工作的具体方式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以计算机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对空间地理信息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系统,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和系统工程综合发展的结果。GIS技术以空间地理数据库为基础,采用矢量或栅格两种方式存储、管理和分析计算各类地球表面的空间属性信息,具有传统的地理学研究方法所难以企及的优势,能够高效、便捷地处理海量空间数据,同时还可以对各类空间属性信息进行有效的地理综合,实现量化的空间分析、模拟和预测。正因此,GIS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在考古学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以区域综合性研究为特征的景观考古学。
GI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成熟起来(Harris and Lock 1990)。具体来讲,GIS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两大方向:其一,文物考古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层面,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管理(CRM)中的广泛应用(Box 1999);其二,考古学研究的层面,尤其是以景观考古学为基础的空间分析方面。实际上,考古学的空间分析尤其是空间定量分析的数学理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已基本建立起来(Hodder and Orton 1976),但是由于受到计算手段的限制,在考古学研究中一直颇受局限。随着GIS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考古学的空间定量分析,尤其是与复杂的地表景观结构相结合的统计分析、数学建模、过程模拟等均可以在GIS软件中方便地实现。比如,以海量计算为基础的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为复杂的空间定量分析提供了可能。这就使得诸多景观考古学研究的理念,尤其是有关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新理念得以实现,从而大大推动了景观考古学的发展。GIS应用于景观考古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景观特征分析、空间过程分析和视域分析。
景观特征分析包括对研究区域的地形、水文特征的提取和分析以及对植被、土壤、矿产等资源的综合研究。GIS研究景观特征首先依赖于建立准确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据此进一步提取坡度、坡向、地表曲率、汇流积累量等地貌信息和山谷、山脊、山顶、水网、集水域等地形特征。同时,由地质矿产和国土资源调查以及遥感影像分析所获取的各类植被、土壤、矿产和土地利用情况等的资源地图也是景观分析的重要对象。在获取这些反映地表景观特征的资料并生成相应的栅格图层的基础上,GIS利用包括多元统计分析在内的各种空间定量分析手段,讨论人类活动与不同的景观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并对这种相关性做出解释,这就是GIS进行景观特征分析的基本方法。近二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考古遗址预测模型”(archaeological site location predictive modeling)实际上就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Kvamme 1983; Mehrer and Wescott 2005)
空间过程分析是对人类以多样化的地表景观为依托所进行的空间移动的分析、模拟和阐释,是通过GIS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过程、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研究。GIS空间分析工具中常用的价值面分析(cost- surface analysis)和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都常被用来研究景观考古中的空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空间移动方式是多样化的,既可以徒步行走,也可以借助于车船之力,而这些不同的移动方式的选择及其效率又与不同的景观类型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在使用GIS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和模拟在不同条件下人类空间移动状况时,还需要充分参考实验考古学、民族志、历史文献等的相关资料。除此之外,由于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多变,采用GIS模拟空间过程的研究如果能在控制一些景观因素的情况下进行对比分析和阐释,寻找特定条件下影响人类空间过程的关键因素,那么结论才能真正合理有效。比如,Mithen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地面模型,并借助于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万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曲线和全球不同气候带的划分,利用GIS技术模拟人类多次走出非洲的过程(2002);Bevan等人通过模拟比对希腊克里特岛青铜时代徒步行走和航海运输两种情况下中心聚落对外控制力的差异,指出海洋运输对迈锡尼早期国家政治和经济统治的重要性(forthcoming)。
视域分析是GIS在景观考古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由于视觉与人类对景观的感知(perception)有关,因此视域分析常常被景观考古学看作是研究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GIS技术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视觉景观的革命:以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GIS可以准确计算出一定区域内任意两点之间是否可视,从而将点对点的视觉研究转换为由点及面的视域分析;另外,采用GIS技术研究视域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空间统计分析,以定量分析取代定性研究,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视觉景观的有效性(Lake et al.1998)。具体来讲,GIS的视域分析有两种类型:简单视域分析和累积性视域分析。简单视域分析(simple viewshed analysis)是直接计算从单个或多个观察点出发所能观察到的视觉范围和具体的景观内容,比如Lock等人研究表明英国Danebury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坟丘是不同社群之间划分疆界的视觉标志,它们的视域彼此之间完全不重合(Lock and Harris 1996)。累积性视域分析(cumulative viewshed analysis)是将从不同观察点出发计算的视域进行相加得出累积性视域,从而计算出在一定范围内从任意一点出发究竟能看到几个观察点的视域分析方法。累积性视域分析既可以计算一定范围内已知的观察点是否具有视觉上的优势性,同时也可以计算观察点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可通视性,比如Fisher等人对英国Mull岛青铜时代石冢群的视域分析,就显示出这些石冢所处的位置在当地社群中具有明显的视觉优势,从而显示出其重要的宗教意义(Fisher et al.1997)。
总之,无论是景观还是景观考古学都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景观既是对地表构成空间结构的描述,也是对人类空间认知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描述;景观考古学关注的是地球表面复杂的景观现象与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更是对社会关系的考察。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将人类活动置于时空连续且内涵丰富的景观之上而不是彼此孤立的遗址之上的研究视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综合研究。正是由于景观考古学的这些特征,以后过程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考古学理论和以GIS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空间分析技术方法才能够在景观考古学研究的范畴中得以充分的理论阐释、方法革新和实践检验,同时也使得景观考古学成为当代西方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相反,尽管近年来景观的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文献中,但整体来讲中国考古学缺乏对景观概念的充分关注。在社会研究方面,中国考古学一直强调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主要方法,在引入西方流行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同时,却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方法背后的景观考古意义,自然对其实际的效果也并不满意。人地关系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被长期置于环境考古的范畴,常常被当作是人与环境之间的机械互动,而缺乏对人的空间认知结构的充分关注。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缺乏对考古学研究的整体性思考有关,而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对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借鉴。
来源:《南方文物》
- 0000
- 0003
- 00034
- 0002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