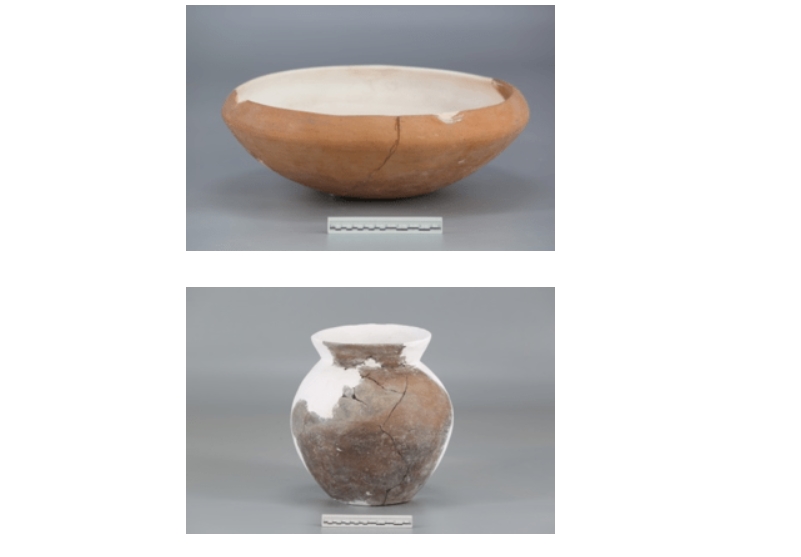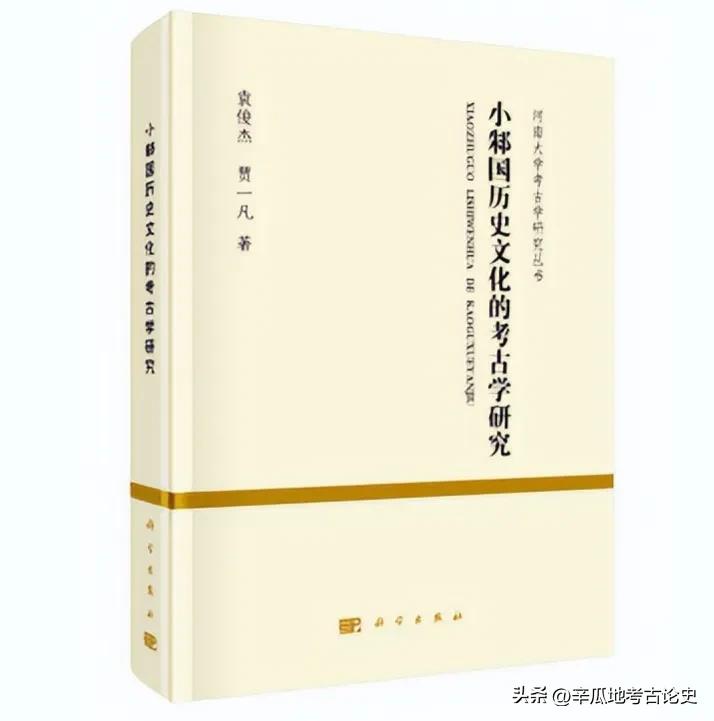李伯谦:从中国文明化历程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
由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一书所构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两千多年来未曾遭到怀疑。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运动,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①。那么中国还有没有自己的古史,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古史?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可李玄伯教授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中提出的“走考古学之路”②,即从野外调查发掘的古人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中去寻找真实的史料,才能建设可信的历史。于是继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③,1926年李济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④,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以李济为组长的考古组对河南安阳小屯的发掘[1],便开启了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化的历程。
一、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化的历程
1928年开始的小屯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成组的大型宫殿基址、多座商王陵墓、大量的甲骨文字,还有制作精良的玉器、骨器,造型奇特、花纹瑰丽的青铜器和铸铜、制陶、制玉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特别是甲骨文中商王世系的释读,证明安阳小屯就是古本《竹书纪年》盘庚迁殷“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朝最后一个国都殷的所在地,商后期历史成为了信史。
1950年早于安阳小屯的郑州二里冈商文化的发现和1955年开始的与其同时期的郑州商城的发掘[2],发现了宫城、内城、外廓城三重城垣,大型储水池和给排水设施,大型宫殿基址,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青铜器窖藏坑,铸铜、制玉、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周邻不远起拱卫作用的诸如望京楼商城等多座次级城邑。由于战国“亳丘”陶文的多次出土,以及范围广大的遗址规模和延续时间,邹衡考证此地应即文献讲的“汤始居亳”的商朝第一个国都“亳”的所在地[3],此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司马迁《史记》和不少先秦文献都记载说商朝之前有一个夏朝。1959年徐旭生以71岁高龄赴豫西进行的“夏墟”调查[4]和当年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5],开启了从考古学上对夏文化的艰难探索。之后陆续发掘了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6]、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7]。1977年安金槐在王城岗发掘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遂即召开了被称为首次夏文化研讨会的“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为研究指明了方向[8]。会上,二里头、东下冯、王城岗等考古队汇报了各自的收获,总结了围绕夏文化探索提出的各种观点,共有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等四种看法。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9]设立的“夏文化研究课题”,下辖“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夏商分界研究”“新砦期遗存研究”“商州东龙山遗址研究”等六个专题,明确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作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并拟定了需重新发掘的遗址,扩大了探索夏文化的范围,同时采集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年代测定。“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和其后的连续发掘,发现了早于小城的面积达34.8万平方米的王城岗大城[7]b、新密新砦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和含有较多东方文化因素的新砦期城[10]、巩义花地嘴有两条环壕的单纯的新砦期大型聚落[11]、荥阳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12]、偃师二里头宫城[5]b、郑州东赵新砦期城和二里头文化城等[13],参之系列C14测年结果,从而使我们得以构建起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以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为代表的夏早期文化——以新砦期遗存为代表的“夷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少康中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夏文化这一完整的夏文化发展系列⑤,夏文化也从虚无缥缈的传说逐渐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历史真实。
夏商由传说变为信史,是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收获,但事实表明,它并不是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最早源头。根据考古学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学界已将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⑥,夏商王朝只是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
“古国”阶段大体处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是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苏秉琦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他心目中的古国主要是指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等遗迹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在以牛河梁为中心50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现日常生活遗迹,而是清一色的与祭祀密切相关的充满宗教色彩的遗存[14]。本人认为,属于这一阶段的“古国”还可以举出长江下游的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15]和黄河中游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16]。三者反映出的社会状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从其身份最高的大型墓葬墓主随葬的玉器观察⑦,“红山古国”有玉猪龙、箍形器、勾云形佩、块、璜、坠及鸟、蝉、龟等祭祀用玉而不见表示世俗权力的钺等兵器,“凌家滩古国”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以宗教祭祀类玉器为主,“仰韶古国”则仅见玉钺一种。这似乎反映了三者在文明化历程中所走的道路不同:红山文化古国走的是清一色的神权道路,凌家滩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和神权相结合而突出神权的道路,仰韶古国走的则是军权、王权的道路。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崇尚神权的,因过度浪费社会财富而难以继续扩大社会再生产,逐渐萎缩消亡了;崇尚军权、王权的,因考虑传宗接代和永续发展比较简约而继承发展下来了。关于“古国”的性质,诚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它是“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显然已不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那种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但又与以后学术界公认的已是典型阶级、国家社会的商周不同,我认为它处在从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向阶级、国家社会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它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和个人权力突显的现象,另一方面还保留有强固的血缘关系,看不到显著的对抗和暴力痕迹。对这一过渡阶段,国内有学者称之为“邦国”,我则觉得它和西方学术界所说的“酋邦”比较相像,中国古代也有特指少数民族部落首长为“酋长”“酋帅”的,有鉴于此,笔者比较倾向用“酋邦”来指称这个发展阶段。
“古国”或曰“酋邦”的进一步发展便进入了“王国”的第一个小阶段,其代表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遗址⑧和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⑨。关于介绍良渚和陶寺的材料很多,有兴趣可以去查阅与之相关的发掘简报、报告、研究论著和展览图录,这里不再重复。2010年在河南新密召开的“聚落考古研讨会”上,本人曾有过一个在考古学上如何判断文明或曰国家形成标准的发言⑩,主要谈了10个方面:聚落是否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特大型聚落;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围沟和城墙;大型聚落中是否出现了大型宗教礼仪中心;大型聚落的墓葬是否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特设的墓地;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专业手工业作坊和作坊区、是否出现了大型仓储设施;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专门的武器和象征权力的仪杖;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文字和垄断文字使用的现象;大型聚落中是否出现了异族文化的因素;各级聚落间是否出现了上下统辖的现象;大型聚落对外辐射的范围有多大、辐射的渠道和手段是什么。从这些方面来衡量,良渚遗址和陶寺遗址,无疑大部分可以契合,本人和学术界不少学者都认为它们已经是科学意义上的“国家”,较之前的“古国”或曰“酋邦”有了明显的进步。
王国阶段的第三个小阶段,是以礼仪和分封制为特征的西周、东周时期。经过秦的兼并战争,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便进入了以制度化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为特征的秦至清的帝国阶段。
由以“红山古国”“凌家滩古国”“仰韶古国”为代表的酋邦,发展到以良渚王国、陶寺王国为代表的王国第一小阶段,以夏商王朝为代表的王国第二小阶段,以西周、东周王朝为代表的王国第三小阶段,再到从秦至清帝国灭亡的帝国阶段,便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11)。
二、国家起源理论的体会与认识
那么,回顾这一过程,对国家起源的理论有哪些体会与认识呢?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既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也是维持社会运转的管理机构。对国家性质的认识,既要强调它是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也不可忽视其社会管理的职能。《周礼》是记录周代官吏设置及其职掌的一部书,从《周礼》的规定可以看出,上至国家行政、司法、军事、外交、经济……下及医疗、丧葬、占卜、百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专人管理。国家的确是一部机器,它不仅仅有暴力性质的专政职能,也有关乎民生的管理职能。
国家出现的前提是社会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以及随着社会复杂化提出的社会管理的要求。而阶级则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和占有的不均而出现。不能设想,在马家浜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社会产品还较少剩余的情况下,会出现对社会财富占有不均的阶级;也不能设想,在没有利益冲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会出现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
部落之间、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土地、人口而展开的战争是国家出现和国家权力不断强化的加速器。良渚遗址、陶寺遗址大型城址城壕、大型宗教礼仪建筑、大型仓储设施、专用玉石兵器、随葬大量随葬品的显贵大墓及专用的贵族墓地等的出现,散见于遗址内的非正常死亡遗骸的存在等,便是战争频仍、国家权力不断强化的证明。
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国家政权,其形式可以是民主制的,也可以是中史集权制的。由多个势均力敌的部落或部族通过彼此斗争、联合而形成的国家可能采用以选举或轮流执政为特征的民主政体,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可能即是这种政治体制的一种反映;而部落或部族间通过兼并战争而形成的国家,则多是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至少从夏代开始,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历程是强势部落、部族不断融合、同化周边异部落、异部族的过程,也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国家的组成,既有军队、法庭、监狱等实体机构,也有法律、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精神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与之配套。良渚文化玉器上随处可见的神徽图像、陶寺遗址贵族墓葬多见的彩绘龙纹图案,都是当时两个王国最高的膜拜对象,它们在巩固各自王国的稳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应该有最基本的标准。在我看来,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的强制性机构,但它也具有随着社会复杂化而提出的社会管理和保持社会运转的职能。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国家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甚至遵循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之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文化格局中。考察中国古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引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参考和借鉴其他学科、其他学者研究的成果,从中提炼和总结出自己的认识,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此文曾提交2015年11月14日~15日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国家起源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
注释: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序言,1926年6月朴社出版;1982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②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1924年发表于《现代评论》1卷3期;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1925年发表于《现代评论》1卷10期。后两文均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下编。
③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载《地质汇报》第5号,京华印书局1923年版。又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之介绍,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④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印行1927年版,转载于《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李伯谦:《新砦遗址发掘与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提出》,此为《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所写前言,后以此名收入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⑥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后收入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初刊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8期,正式发表于《文物》2009年3期,后收入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⑧良渚遗址发掘报告如《反山》《瑶山》等多已出版,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可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⑨关于陶寺遗址基本情况请参见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一书。其后新材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7年田野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5期,200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Ⅲ区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期;《2013-2014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8期,2015年8月。
⑩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分别收入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和《感悟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1]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本文根据2010年12月1日至2日在台北“东亚考古学的再思——纪念张光直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收入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