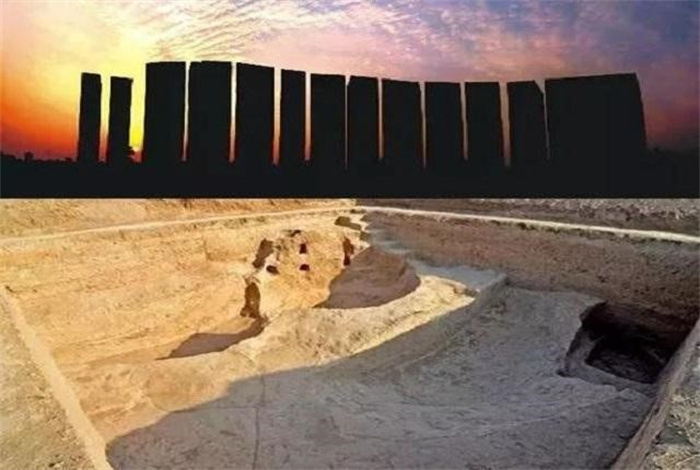董勤;鲁西奇: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
提要:历史时期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进程,可区分为三个阶段:(1)自原始稻作农业起源,至2世纪末,南方山区的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业为辅;(2)自六朝至北宋末,低山丘陵地区的河谷、山间盆地逐步被开垦成农田,局部地方形成了梯田,建设了中小型农田水利,但刀耕火种性质的烧畲仍是南方山区主导性的垦耕方式;(3)自南宋以迄于明清时期,浙闽山地、南岭山地、川东丘陵山地、粤桂山地、秦巴山地渐次得到全面开发,特别是明清时期,各省际交边山区成为主要开发对象,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经济开发 空间拓展 南方山区
我国南方地区的山区面积广大,其北部有秦巴山地、淮阳山地等,东部有浙皖山地、江南丘陵山地、浙闽山地,南部有南岭山地、粤桂山地,西部则包括四川盆地外缘与鄂、湘、黔、滇四省接壤地带的山地以及横断山地等【1】。南方山区地处亚热带,受东南季风之惠,气候温暖,湿润多雨,光热充足,有利于多种动植物生长发育,山林资源丰富;山区中小河流众多,有利于发展灌溉农业。因此,南方山区很早就成为人类栖息、生活与从事生产活动的地方,孕育了原始稻作农业;在历史时期,特别是南宋以迄于明清时期,南方山区逐步得到开发,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发展区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括历史时期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进程,可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距今l万年左右原始稻作农业起源,至公元2世纪末,南方山区的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业为辅,驯化与栽培的规模较小,且限于局部地区。第二阶段,自六朝至北宋末,南方山区农田垦辟有了一定发展:低山丘陵地区的河谷、山间盆地逐步被开垦成农田,局部地方形成了梯田,建设了中小型农田水利;但以刀耕火种性质的“烧畲”仍是南方山区主导性的垦耕方式。在采集、砍伐山林等山林资源利用方式之外,种植茶、漆等经济林木,逐步成为部分山区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开发较为成熟的地区主要是在江南丘陵山地、淮阳山地、湘中丘陵山地等低山丘陵地区。第三阶段,自南宋以迄于明清时期,浙闽山地、南岭山地、川东丘陵山地、粤桂山地、秦巴山地以及西南云贵高原山地渐次得到全面开发,山区种植农业、山林资源的多种经营、矿冶、手工业等均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各省际交边山区,如川陕楚交界的秦巴山地、湘鄂川黔边的武陵——雪峰山区、闽浙赣交边的武夷山地、湘赣粤交边的南岭山地等,成为山区开发的主要对象,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2】。
一、南方山区开发之起步
迄今为止,已发现原始稻作遗存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邕宁顶狮山、南宁豹子头、横县西津、广东曲江石峡、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遗址,均位于丘陵山地和山间小盆地、河谷阶地,说明南方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很可能起源于低山丘陵地带,特别是山间盆地与河谷阶地上【3】。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南方山区的开发很可能早于平原地区,至少不会晚于后者。当然,与平原地区相比较,南方山区的原始稻作农业遗址的规模较小,相互之间的距离较远,封闭及分散程度较高,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山区人口聚集的数量、速度和规模都远不及平原地区,其开发程度亦略为逊色【4】。就其内涵而言,山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面貌中,驯化与栽培的规模都相当有限,采集与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较之同时期平原地区更大。
先秦时期,南方山区的经济形态甚少见于文献记载。《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载夏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5】。鸟田,《水经注》卷40《渐江水》记大禹死后,葬于会稽,“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6】。其说不能解,然“鸟田”乃为南方地区一种原始的耕作方式,当无疑问【7】。“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说明越人当频繁迁徙,以选择更适宜的农耕、渔猎地点,其耕作方式当以撂荒游耕制为主。今见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间有南方民众人山采伐林木的记载。《史记》卷119《循吏传》记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前591年),孙叔敖为楚相,“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即秋冬入山砍伐林木竹材,至夏季水大时运送出山【8】,这说明“山伐”当是楚地山区民众的重要生计方式之一。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出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9】也说明采伐山林材木是山区重要的生产活动。
南方山区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业为辅的经济形态,到秦汉时期,可能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汉书·地理志》谓“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始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10】。桓宽《盐铁论》卷1《通有》引“文学”之言称:
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鱟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11】。
所言虽然都是南方的整体情形,但其中所说“山林之饶”及“陵阳之金”、“蜀、汉之材”,显然皆出自山区;“以渔猎山伐为业”,则当是南方山区的主导性经济形态;“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则反映出山区土地垦辟、种植的方式,当即后世文献中所见的“刀耕火种”,其种植作物则为谷、粟,应以旱稻、粟等旱地作物为主【12】。
据今见汉代文献记载,闽粤山地的越人、荆楚山区的诸蛮、川渝地区的巴蛮、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主要是处于以山伐渔猎与原始农业并重的状态。汉武帝时,拟发兵击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谓: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越人欲为乱,必先田余干界申,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13】。
据此,则知越人居于深山竹林之中,无城郭邑里,没有车骑弓弩。其农耕较发达之地,则在余干。余干,韦昭注:“越邑,今鄱阳县也。”在今江西东北境。越人“欲为乱”,“先田余干界”,以“积食粮”,则知“田”(农耕)在越人生活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惟“欲为乱”方为之。又,1958年,在闽北武夷山地崇安汉城遗址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内有十多件铁制农具犁、锄、锸、攫、斧、锯等【14】。但这在浙闽山区还非常稀见。汉光武时,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15】。则在此之前,九真郡民众向以“射猎为业”;东汉初年出现犁耕,但看来并不普遍,可能仅行于沿海平原地区。主要居于今湘中丘陵与湘鄂西山地的武陵蛮、长沙蛮,“好人山壑,不乐平旷……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西汉时,“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反映出蛮民或已垦辟出部分农田。然因此而激起蛮民反叛,澧中、溇中蛮皆“争贡布,非旧约”【16】,说明其田作收入还相当少。今川东、重庆地区的巴、濮诸蛮,种植农业在生计中所占的比重似较高。《华阳国志·巴志》谓巴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川崖惟平,其稼多黍”,“野惟阜丘,彼稷多有”【17】。然黍、稷等旱作物大抵皆植于较平坦之川谷或低矮的阜丘上。东汉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书请分巴郡为二,谓安汉与临江“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却没有提到粮食生产,说明其地垦辟尚浅【18】。云贵高原地区,据司马迁描述,滇与夜郎“皆魃结,耕田,有邑聚”,已有农耕与城邑;残、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以游牧为主;徙与榨都,“其俗或土箸,或移徙”【19】。可知云贵高原各地经济形态颇不一致,但大抵仍以畜牧渔猎为主,耕田、邑聚相当稀少。《后汉书·西南夷传》谓滇池周围“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两汉之际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则益州郡已有灌溉水利。然东汉初刘尚重平益州郡,“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疋,牛羊三万余头”,则知畜产仍然是西南夷最重要的生计依靠【20】。
总的说来,虽然南方山区很早就孕育了原始稻作农业,但直到2世纪末,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规模很小,河谷低地当主要采用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种植水稻;低丘岗阜及低山地带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早稻、粟、稷等旱地作物。无论在河谷低地还是低山丘陵地带,可能都以撂荒游耕制为主,连续耕作的连种制即便出现,也不普遍;农作产出甚低,在民众生计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太大;而山伐渔猎畜牧,则在山区民众生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漫长时期南方山区的经济形态概括为“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业为辅”。得到初步开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区内地势较为低平的河谷、盆地及其周边的低丘岗阜地带,呈点、块状分布,规模较小;各聚落点之间大多是不连续的,相互之间的距离也较远,封闭及分散程度较高。
二、六朝至北宋时期南方山区的持续开发与平稳拓展
六朝时期,农田垦殖发展较早且成效较大的南方山区,首先是江南丘陵山地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低山丘陵。孙吴嘉禾三年(234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负责讨伐丹阳郡西部(今皖南赣东北)的山越。诸葛恪“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21】。这些“山越”广泛种植谷物,且“自铸甲兵”,很可能已普遍使用铁农具。至于被迁移至河谷地带的“从化平民”,既受命“屯居”,自必不再可能“随陵陆而耕种”,山伐渔猎在其生计中所占的比重亦大幅度降低。《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裴注引习凿齿《襄阳记》称:
租申在上黄界,去裹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粗中【22】。
则居于山区河谷地带的蛮民,已种植桑麻,垦辟水陆良田。刘宋中期,沈庆之征伐沔北诸山蛮,谓“去岁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卒难禽剪”;他率领诸军斩山开道,“自冬至春,因粮蛮谷”;南破山蛮后,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23】。沔北诸山蛮拥有不少米粟,说明田作在其生计中已占有主导地位。《南齐书·蛮传》云:“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24】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中期,汶阳郡著籍户口为958户、4914口【25】。汶阳郡地处今鄂西北山区,田地垦辟已有如此规模,可以推知当时荆襄山区的土地垦殖已有相当发展。
六朝至隋唐时期,南方山区的土地垦辟,仍主要集中在河谷与山间盆地及低山、丘陵地带。上举伹中、临沮皆在河谷,即可为证。唐大历初(766—768年),杜甫在夔州留居数年,对夔州周围山地多所称述。《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云:“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26】《夔州歌十绝句》之六云:“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自滾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之一称:“白盐危峤北,赤甲古城东。平地一川稳,高山四面同。”【27】则东屯是夔州城附近山谷间一块难得的平地,已垦殖为稻田。唐大中三年(849年),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以“褒斜旧路修阻”,开凿文川谷道。新路成,孙樵撰《兴元新路记》志其事,其中记述自关中越秦岭至汉中沿途所经之景色甚详,如:过泥榆岭,“又平行十里,则山谷四拓,原隰平旷,水浅草细,可耕稼,有居民,似樊川间景象”。自芝田驿至仙岭,“虽阁路,皆平行,往往涧旁谷中有桑柘,民多丛居,鸡犬相闻”。自仙岭而南,“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桑柘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亩,谷中号为夷地,居民尤多”【28】。显然,聚落田地均处于涧旁山谷中,并未见有关于梯田的记载。在闽粤山地,山间盆地多称为“山洞”。《元和郡县图志》卷29记福州永泰县,乃“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诉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无行路”。此一“山洞”,“南北俱抵大山”,沿流而下,可至福州侯官,其得到开发之区,显然仅为河谷两岸之狭长地带。同书卷又记漳州龙溪县,谓其“县东十五里至山,险绝无路,西二十里至山,南三里至山,北十六里至山”【29】。则龙溪县境内得到开发的区域即在四山环抱的河谷盆地中,即以县治为中心、东西三十五里、南北十九里、沿龙溪(今九龙江)河谷伸展的狭长地带。同书卷33渝州“壁山县”条又称,“本江津、万寿、巴三县地。四面高山,中央平地,周回约二百里。天宝中,诸州逃户多投此营种”【30】,则渝州壁山县所在显然是较大的山中盆地。
在山区河谷盆地一些条件适宜的地方,六朝至唐北宋时期,逐步兴修了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六朝文献中,已见有南方山区引水灌溉的记载。《水经注》卷39《耒水》篇记耒水北过便县(在今湖南永兴县)之西,“县界有温泉水,在郴县之西北,左右有田数十亩,资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温水所溉,年可三登”【31】。然所记似为特例。《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袁州宜春县“昌山”条载:“旧名伤山,袁江流其间,巨石枕岸潺激,舟人上下多倾覆,故名伤山。按顾野王《舆地记》:‘晋永嘉四年,罗子鲁于山峡堰断为陂,从此灌田四百余顷。梁大同二年废。”’【32】则此陂当于昌山脚下遏袁江而成堰,引水灌溉。这是今见文献记载中南方山区较早的引水灌溉设施。至唐代,南方山区的水利设施渐次兴筑。《新唐书·地理志》记昇州句容县有绛岩湖,在句容县西南三十里,“麟德中,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后废;大历十二年,令王昕复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暘,开田万顷”【33】。据唐人樊珣《绛岩湖记》所记,绛岩湖乃“吴人创之,梁人通之”,则其创制或可上溯至三国时代。大历十二年(777年)重修之后,“周匝百顷,蓄为湖塘”,“开田万顷,赡户九乡”,则知其发挥较大作用乃是在中唐以后【34】。宣州南陵县之大农陂,不详筑于何时,元和四年(809年)“因废陂”重修,“为石堰三百步,水所及者六十里”,“辟荒梗数万亩”,“溉田千顷”【35】。唐贞元初(758—787年),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民岁争灌溉,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36】。民间争水灌溉,说明其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已较多。据咸通十一年(870年)抚州兵曹参军柏虔冉么新创千金陂记》载:抚州境内自上元(760—761年)以后,相继修筑华陂、土塍陂、冷泉陂等水利工程;咸通九年(868年),在抚州刺史李某主持下,于汝江之上置千金陂,引水“沿流三十余里,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37】。说明抚州境内农田水利确已较为发达。西川益、蜀、彭、汉、眉、资、绵、剑、陵等九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共有水利工程22处,尤以绵、益二州最多。其中固多在成都平原,然位于丘陵山区者亦有不少。如眉州青神县,“大和中,荣夷人张武等百余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绵州巴西县,“南六里有广济陂,引渠溉田百余顷,垂拱四年,长史樊思孝、令夏侯奭因故渠开”。罗江县,“北五里有茫江堰,引射水溉田人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北十四里有杨村堰,引折脚堰水溉田,贞元二十一年,令韦德筑”。龙安县,“东南二十三里有云门堰,决茶川水溉田,贞观元年筑”。剑州阴平县,“西北二里有利人渠,引马阁水人县溉田,龙朔三年,令刘凤仪开,宝应中废。后复开,景福二年又废”【38】。
今见文献记载中,有关南方山区开发梯田的明确记载出现于北宋后期。方勺《泊宅编》卷3记福建山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硓,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39】。从其描述看,当即后世所称之“梯田”。南宋初,袁州知州张成已称:“江西良田多占山岗上,资水利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旱嘆。”【40】山岗之上的“良田”,大抵亦属于梯田。至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春,范成大游历袁州仰山,见“岭阪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41】。显然,田地之垦辟从河谷、山间盆地向上延伸,达于山坡乃至山巅,遂逐步开垦成梯田。但根据文献中有关梯田的这些零星记载,并不足以断定南方山区的梯田即出现于北宋中后期.从上引方勺、张成己、范成大的描述中,均可见出其所见之梯田当已有悠久历史,或可上溯至晚唐五代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断定,到北宋时期,南方山区梯田的开发依然不很普遍,大约只是在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低山地区才较多一些。
在地势低平、水热条件较好的山区河谷、盆地中,当以种植水稻为主;至少在那些兴筑了水利设施、可以灌溉的地方,很可能已逐步放弃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也不再撂荒,或者采行休耕制。但在地势较高的丘陵、低中山地,仍普遍实行刀耕火种性质的畲田,也仍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42】。王建自襄阳南行经宜城渡蛮水趋荆门,途中见到“犬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43】。温庭筠《烧歌》则描写随州南部山区(大洪山区)的农事云:“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早田。”【44】在秦岭道上,薛能《褒斜道中》谓秦岭山中“鸟径恶时应立虎,畲田闲日自烧松”【45】。兴元初(784年),唐德宗南幸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称:“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稆为事。”【46】均说明在唐代荆、襄、随、梁诸州的山区,畲田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北宋中期,王禹偁在《畲田词》“序”中描述商洛山区的畲田之法称:
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畲田。虽数百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而掩其土也。掩毕则生,不复耘矣【47】。
显然,畲田乃是一种相对粗放的旱作农业方式。江南丘陵山地的情形与此相似。唐德宗时,释普愿于皖南九华山建寺,“斫山畲田,种食以饶”【48】;罗隐《别池阳所居》句云:“黄尘初起此留连,火耨刀耕六七年。……却是九华山有意,列行相送到江边。”【49】说明皖南山区仍然盛行刀耕火种。刘长卿《送睦州孙沅自本州却归句容新营所居》句云:“火种山田薄,星居海岛寒。”【50】方干途经婺州东阳县,看见“野父不知寒食节,穿林转壑自烧云”【51】。淳熙《新安志》卷2《叙贡赋》谓:“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骋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穷,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之。”【52】说明皖南山田多为旱作,亦行刀耕火种之法。南岭山地亦普遍盛行畲田。唐大历中(766—779年),戴叔伦经过道州,见到“渔沪拥寒溜,畲田落远烧”;过桂阳岭,又看到“种田烧险谷,汲井凿高原”【53】。《五灯会元》卷6《南岳玄泰禅师》记玄泰与贯休、齐己为友,“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滋甚,乃作《畲山谣》”,其中有句云:“年年斫罢仍再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54】正是畲田的形象写照。川鄂湘黔边山地的情形与此相类。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曾有诏川峡路不得造着錡刀,利州路转运使陈贯上奏反对,说:“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峡山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谓之刀耕火种。今若一例禁断,有妨农务。”【55】说明川峡诸路直到北宋时代,刀耕火种仍很普遍。上引记载虽然笼统地称述其所记刀耕火种者为“山田”,在“险谷”或“高原”,而未能区别山区的河谷地带,但结合上文有关山区河谷平原地带农耕方式的讨论,可以相信,实行刀耕火种之法的,主要是在地势高仰、没有或较少灌溉之利的丘陵、低中山地的山坡之上。当然,刀耕火种并不一定就是撂荒游耕制,还可能采用撂荒休耕制,即耕种若干年后,撂荒休耕;隔数年,再重新耕种。
虽然田土日辟,但山林采伐、渔猎在山区民众生计中仍占有相当位置。《宋书》卷47《刘敬宣传》记东晋末年,刘敬宣为宣城内史(治宛陵,辖境在今皖南),“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户”【56】。刘宋宣城郡所属广德、宁国、怀安、泾、安吴、广阳、临城诸县皆在山区,故得称为“山县”。据上所引,知凡此诸县出产山货竹木,其民则多“工巧”,以致宣城郡竟置立私屯,专事营求财货,“供府郡费用”。这说明其地民众生计多靠经营山货,砍伐竹木,并“造作器物”。至唐代,植茶逐步成为歙、宣、饶诸州部分民众最重要的生计方式。《文苑英华》卷813录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称:祁门县“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置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57】。北宋时期,歙、睦、宣诸州山内多营漆楮松杉等山林物产。方勺《泊宅编》卷5载:“青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南趋睦而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58】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范成大经过严州(治在今浙江建德东),见到“歙浦杉排毕集”于浮桥之下,故而述及:“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59】则知种杉已成为歙州山区的重要产业。在巴蜀丘陵及其周边山地,早在汉代,广汉郡什邡县即以“山出好茶”著称,南安、武阳亦皆出名茶【60】。江阳郡汉安县“土地虽迫,山水特美好。宜蚕桑,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61】。唐长庆二年(822年),曾任开州(治在今重庆市开州)刺史的韦处厚上疏概述山南风俗,谓:“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62】则知蜡漆鱼鸡等物产在山区民众生计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密弥平原的低山丘陵地带,商品作物更受到重视。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苏舜钦尝游历太湖洞庭山,谓洞庭山“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树桑栀柑柚为常产。每秋高霜余,丹苞朱实,与长松茂树参差”【63】。至南宋初,庄绰描述说:“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骑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蝴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64】柑橘桑麻,已成为洞庭山中民众的常产、生计之主要依靠。
从开发区域言之,唐北宋时期,南方山区的开发很不均衡。皖南山区、浙赣山地、湘中丘陵、四川盆地西北部丘陵山地的开发程度相对较高。唐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在氓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65】杜牧《吕温墓志铭》记唐武宗时,吕温出为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辖区“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宣、歙、池三州已得与苏、润、常、湖诸州并驾齐驱,得称为“富州”。婺、衢、睦(严)、饶、信、抚、吉、袁等以山地为主的州郡发展也较快。婺、衢二州地处金衢盆地,唐北宋时期,发展甚速。唐贞观时,婺州五县,有著籍户37819户;垂拱二年(686年),自婺州析置衢州;天宝中,二州共有212558户【66】。在百余年时间里,著籍户口增加五倍,可见其发展之速。饶州亦以富庶为称。南唐昇元二年(938年),刘津说:“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67】除祁门外,其余三县均属饶州。北宋元祐六年(1090年),余干进士都颉作《鄱阳七谈》,极言其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以及林麓木植之饶,铜冶铸钱,陶埴为器【68】,足见饶州之富饶。抚州则“号为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阛阓,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69】。开元七年(719年),抚州刺史卢元敏以“田地丰饶,川谷重深,时多剽劫”为由,奏请复置南丰县【70】。“川谷重深”的南丰县已被称为“田地丰饶”,可知赣东山区已有较好开发。信州大部分都是山区,其元和户为2891l户,宋初主客户合计40685户,熙宁户132717户,祟宁户154364户【71】,在约三百年时间里增加四倍,著籍户口之增长速度非常惊人。在荆楚地区,黄、鄂、安、荆、岳、潭诸州丘陵山地的开发相对较好。晚唐僧人齐己曾久居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其《暮游岳麓寺》句云:“回首何边是空地,四村桑麦遍丘陵”【72】,反映出潭州湘江西岸的岳麓山已遍布桑麦。《宋史·地理志》谓潭、鄂、岳、全、邵诸州“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人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概种,率致富饶”【73】。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西北部丘陵山地的开发程度较高。如蜀州有“金砂银砾之饶……即山而鼓,民拥素封之资;厥筐之华,户赢玩巧之利”【74】;绵州“处二蜀之会,人饶地腴,赋货繁茂”【75】。
相较而言,浙闽山地、南岭山地以及秦巴山地、湘鄂川黔边山地、云贵高原,则处于比较落后的后进阶段。唐代台、处、温、福、建、汀、泉、漳诸州山区,鲜有农田水利工程之记载。汉水上中游以至荆楚北部的梁、金、商、房、均、邓、唐、随、郢诸州境内的秦巴山地、大别山区、大洪山区的经济开发也较落后。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诏书丙午云:“邓、唐、隋、郢诸州,多有旷土,宜令人户取便开耕,与免五年差税。”【76】直到北宋仁宗、英宗间,唐、邓间“尚多旷土”【77】,更遑论与唐、邓相邻的商、均、襄、随诸州山区了。湘鄂西山区的峡、归、施、沅、靖、辰以及夔、渝等今川东、重庆诸州,也比较落后。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上述诸州鲜有关于农田水利工程的记载。即便是处于四川盆地中央的潼川府路,直到南宋初,仍被汪应辰称作“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而夔州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又非潼川府路之比”【78】。据此可以想见四川盆地周边山区的状况。
总的说来,自六朝以迄至北宋末的近一千年间,南方山区没有受到北方中原地区那样频繁而巨大的战乱破坏,发展比较平稳,没有较大起伏。在开发区域上,皖南山区、浙赣山地、湘中丘陵、四川盆地西北部丘陵山区的开发程度相对较高,而浙闽山地、南岭山地、秦巴山地、湘鄂川黔边山地、云贵高原,则处于比较落后的后进阶段。就山区内部农田垦辟与耕作方式的差异而言,地势较低平的河谷、盆地主要种植水稻,实施连种耕作制,可能已普遍推广牛耕;而在丘陵、低中山地的山坡上,即便已开辟出梯田,亦仍较普遍地采用刀耕火种式的畲田耕作方式,撂荒游耕或休耕制可能逐步被放弃,但连种制大约也未能得到广泛而彻底的实施。就山区民众生计来说,虽然农耕产出在民众生计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加,但山林砍伐、山区林特产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种植以及渔猎采集,在民众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局部山区,其重要性甚至在加大。
三、南宋至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的全面开发
南宋至元代,除上述在唐北宋时代即已得到相当程度开发的皖南山区、浙赣山地、湘中丘陵、四川盆地西北部丘陵山地继续发展之外,浙闽山地、南岭山地、川东丘陵山地、粤桂山地等山区的开发比较突出。台州位于浙闽山地东北部,负山滨海。嘉定《赤城志》卷13《版籍门》称其地“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也”【79】。同书卷26《山水门》又记郡属五县境内之堰、埭、泾、砩等农田水利设施,共有219处【80】。温、处二州大抵以括苍山为界,山中的冯公岭,至迟到南宋中期,已垦辟出梯田。楼钥《攻娩集》卷7《冯公岭》诗云:“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81】所描述的正是典型的梯田景象。叶适《冯公岭》句则云:“冯公此山民,昔开此山居。屈盘五十里,陟降皆林庐。公今去不存,耕凿自有余。……瓯、闽两邦士,汹汹日夜趋;辛勤起芒履,邂逅乘轮车。”【82】瓯、闽之人日夜争趋而来,说明冯公岭有大量外地移民进入。处于括苍山中的冯公岭尚且已垦辟出大量梯田,温、台、处三州山地的开发固可推知【83】。福建山区的梯田更有全面发展。《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九载嘉定八年(1215年)七月二日臣僚奏称:“闽地瘠狭,层山之巅,苟可寘人力,未有寻丈之地不蚯而为田,泉溜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84】则知福建山地梯田已有引水灌溉设施。淳熙《三山志》卷15《版籍类》“水利”云:闽地“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而水泉自来迂绝,崖谷轮吸,□□忽至”【85】。福州所属古田、闽清、永福三县辖境均属于内地山区。据淳熙《三山志》载,古田县各里共有陂、洋等水利设施27处,永福县有塘、陂8处,闽清县“村落各堰成陂,溉田种五万余石”【86】。建宁府(建州)崇安、松溪、政和二县并处大山之中。《永乐大典》卷2755引淳祐《建安志》记三县陂塘,崇安县有13处,松溪县3处,政和县10处【87】。汀州各县亦皆在重山之中,“山多田少,土瘠民贫”【88】。汀州著籍户口,北宋末(崇宁)户为81454户,庆元间(1195—1200年)增至218570户,开庆间(1259年)见管222433户【89】,已是北宋末的近三倍。开庆《临汀志》于“山川”下记有各县陂塘,其中长汀县有郑家陂、西田陂、南拔桥陂、官陂、中陂、何田大陂等7处,宁化县有大陂、吴陂等2处,上杭县有梁陂、高陂等2处,武平县有黄田陂l处,莲城县有24处【90】。南岭山地的开发,则以虔(赣)州最为突出。《永乐大典》卷2754引南宋末成书的《章贡志》记虔(赣)州各县陂塘,其中赣县有279处,宁都县有366处,雩都县有362处,兴国县有3处,龙南县有69处,信丰县有18处【91】,则知南宋时赣州境内山地已普遍兴修陂塘等农田水利,基本脱离了刀耕火种的旱作形态。大庾岭南麓的南雄州,“近岭下”,“地据上流,田有肥瘠”,在南宋之前,既已修有凌、连二陂,“千百顷亩皆藉以灌溉之利”,惜“岁月浸久,荒湮不治”。嘉定九年(1216年),郡守黄歲主持重修【92】。南岭山地西端的衡、郴、道、永诸州及桂阳军,南宋时期也已垦辟出梯田,并兴修了部分水利设施。乾道九年(1173年)春,范成大行经衡、永二州间的黄罴岭(在今湖南祁阳、祁东二县间),作《过黄罴岭》诗云:“谓非人所寰,居然见锄犁。山农如木客,上下穠以飞。”【93】则在“极高峻”的黄罴岭上已有山农垦殖。在范成大南行之前,乾道元年(1165年),张孝祥出知静江府(治在今桂林),亦经过衡、永一带。其《湖湘以竹车激水,粳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诗描述了筒车车水的情形:
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运,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94】。
按:此诗所书之能仁院在衡州。经过兴安县,张孝祥另作诗吟颂筒车车水灌溉之利云:“筒车无停轮,木枧着高格。粳徐接新润,草木丐馀泽。”【95】则知南宋时衡、永、桂诸州山区已普遍使用筒车灌溉。四川盆地东部与南部山地也有较大发展。泸州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境内大部分为低山丘陵。《永乐大典》卷2217七“泸”字韵下录南宋末成书的《江阳谱》,记泸州及所属江安、合江二县乡都保甲聚落户口甚悉,颇可见出南宋川南山地之发展状况。如泸州“衣锦乡白艿里”下原注称:“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最富。”全里有著籍户4599家,集聚村落26个,其中至少有6个称为“市”的聚落可基本确定为集市。又如清流乡沿江里,原注称:“在县西九十里,有溪连大江,地产牛乳、蔗、柑桔、盐。”其所属“怀德镇”原注称:“旧名落来镇。宣和三年安抚司状奏:据落来市乡老称:落来镇初因夷人落来归明于本镇住,遂呼镇市为落来,乞改撰。得旨,落来镇改为怀德镇。”则其地归化未久。而全里共有著籍户2196家,集聚村落15个,其中至少有5个可以确定为市镇【96】。
经过南宋至元代的长期开发,到明清时期,南方大部分低山丘陵地区已开发殆尽,进一步开发的重点乃集中在各省边缘的中高山区以及云贵高原及其周边的中高山地,特别是川鄂陕豫交边的秦岭——大巴山地、闽赣湘粤交边的武夷——南岭山地、湘鄂川黔交边的武陵——雪峰山地等。兹以秦巴山区为例。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开发大致有两个高潮:一是在明中后期,主要集中在秦巴山区东部的襄阳、郧阳、南阳地区及荆州西部山区【97】;二是在清中期,特别是乾隆至道光间,鄂西北、豫西南、陕南、川北山区均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发【98】。到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地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有客民的足迹,崇山峻岭,无不开辟垦殖。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云:“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99】土地资源条件较差的竹山县,“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100】。大巴山深处的砖坪厅地处川陕交界地带,海拔大都在1500米左右。到道光初年,砖坪厅“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101】。秦岭南坡西安府、汉中府、兴安府与商州四府州交界的地区,在清初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五郎厅(后改为宁陕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102】。至迟到道光中期,秦巴山区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武夷一一南岭山地、武陵——雪峰山地以及云贵高原山地的开发进程与秦巴山地大致相似,只是在时间上略有早晚,开发深度与广度略有差别【103】。从总体上看,主要位于诸省交边地区的中高山地,到清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均已得到程度不同的全面开发。
在汉魏六朝以迄于唐北宋时期的文献中,虽也有不少关于“逃户”、“逃人”、“流移”、“亡命”进入山区,从事垦辟、山伐、矿冶的记载,但总的说来,南方山区开发的主力应当是包括诸种被称作蛮、山越、獠的南方古代族群在内的山区土著居民。而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南方山区开发的主力则主要是被称为“棚民”、“流民”的山外移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称:兴安州及所属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104】……兼有外来无业匪徒,因地方僻严如炤则描述说: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105】。
显然,这些携带家室、络绎不绝进入山区的“穷民”构成了山区开发的主力军。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南方山区开发、经济增长的进程遂与山外流移人口大量进入山区的过程相对应,而流移人口进入较多、集中落居的地区,也就是山区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并进而成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较为严重的地区。在流移人口与山区开发的动态过程中,流移人口占据着主导性的能动作用:流移人口是因,资源开发是果,资源开发的进程与特征主要受到流移人口之进人及其特性的影响与制约。
流移人口进入山区之初,也往往会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垦辟土地。严如熠尝描述秦巴山区的开荒之法云:“大树巅缚长紐,下缒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06】但山区山林所有权既渐次明晰,流移人口实际上已不能随意烧荒垦山,亦不能随意撂荒,所以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垦辟土地之初。流移人户留居下来之后,便尽可能经营灌溉设施与梯田,实行连作制。严如熤说:“山内垦荒之户,写地耕种,所种之地,三两年后,垦荒成熟,即可易流寓成土著。偶被雨水冲刷,不能再耕,辄搬去,另寻山地。”【107】“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108】。然则,棚民起初常常是“迁徙无定”,没有固定的产业与住居;时间既久,则或“渐治田庐”,遂营治水田与梯田,连续耕种;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会轻易舍弃已开垦的田地。明清时期,山区灌溉水利得到全面发展。汉中府留坝厅,“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109】。定远厅(今镇巴县)处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110】。说明即便是在中高山区的河谷子坝,灌溉水利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这些条件较好的河谷子坝中,至迟到清中后期,无论是水田还是旱地,均已较广泛地推行了稻麦复种制。《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云:“(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稻收后即犁而点麦,麦收后又犁而栽秧,从不见其加粪,恃土力之厚耳。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兴安、汉阴亦然。”至于中高山区,“溪沟两岸及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间亦种大小二麦。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111】。虽主要采用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制,然较之刀耕火种式的撂荒游耕——休耕制,实已为极大进步。因此,虽然与平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方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总的说来,自南宋以迄于明清,南方山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已逐步脱离刀耕火种式的撂荒游耕——休耕制,而普遍推行连作制。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乎坝及部分低山丘陵地区,已普遍实行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轮作复种制,即便在中高山区,一年一熟的连种制也是基本得到保障的。
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乃是玉米、番薯、洋芋等高产旱作物的普遍引种、推广。在明中期之前,南方山区种植的旱地作物主要是黍、粟、豆、麻、荞等。玉米等作物在山区引种后,迅速推广开来,到清中期,已成为山区的主要种植作物。在秦巴山地,严如熠《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112】郧阳府各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属,“镇安、山阳寸趾皆山,绝少水利;商南、商雒间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兴安府七邑水田总计“不逮南(郑)、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资包谷杂粮”。汉中府属留坝、定远、凤县、略阳、洋县等,也“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113】。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广,比玉米要迟一些,大约是在嘉庆年间。光绪间,兴安知府童兆蓉称:“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114】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9《土产志》“洋芋”条云:“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此,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或云,乾隆间杨口仕广东,自外洋购归。”【115】则乾隆间秦巴山地已种植洋芋,嘉庆以后才全面推广【116】。
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间平坝,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兴修渠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中高山地带,则只能种植洋芋、番薯和部分杂粮。道光《石泉县志》卷2《田赋志》“物产”栏称:“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又说:“石邑水田十仅有二,稻谷无多,高山随便播种,更难概论,惟坡地须酌种麦。”【117】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也说: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荞麦、燕麦、洋芋、红苕【118】。道光《宁陕厅志》卷l《风俗》谓:“其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粱,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过山地中十分之一。”【119】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力下降,产出减少,高产的洋芋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云:“高山之民,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120】
除垦辟田地、种植粮食作物之外,南方山区木材采伐、经济林特产品的采集与加工、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冶炼也得到长足发展。福建西部的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处丛山之中,林木资源丰富,南宋以来,即有大量林木及漆、茶、蔗糖、纸等林特产品沿闽江下运,如建瓯县,“杉木遍地可以种植。……除本地供用外,岁出京筒二百余厂,……均输出省会,运售上海、宁波、天津等处”【121】。在秦巴山地,严如熤描述说:“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122】。
总之,自南宋以迄于清中后期,南方山区的开发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深化,大部分中高山区均得到程度不同的开发。与六朝至北宋时期南方山区的相比较,这一时期南方山区的开发主要有五个特点:(1)山区开发在空间上不断向中高山区拓展,到清中后期,各省交边的中高山区均已得到程度不同的全面开发;(2)山区开发的主力以自山外移人的诸种流移、移民为主力;(3)山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已逐步脱离刀耕火种式的撂荒游耕——休耕制,而普遍推行连作制,河谷平坝及部分低山丘陵地区已逐步实行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轮作复种制,中高山地则普遍实行一年一熟制;(4)南方山区均普遍引种、推广玉米、番薯、洋芋等高产旱作物;(5)山林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扩展,利用方式越来越多样性,特别是林副产品的加工与再生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四、结语与讨论
综上所论,结合我们近年来的田野考察与思考,可以对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形成几点初步认识:
首先,南方山区经济开发虽然以农田垦辟、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线索,但山林、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一直是南方山区开发的重要方面,在很多山区,采集渔猎、山林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多种经营一直是较长时期内山区民众最重要的生计依靠。实际上,充分利用山区林木与矿产资源,很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倾向”,并不一定是进入山区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形成人口压力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上引《宋书·刘敬宣传》记东晋末宣城郡民众生计多靠经营山货,砍伐竹木,并“造作器物”。刘宋中期,宣城郡著籍户口为10120户、47992口【123】,其晋末实际户口即使倍于此数,也无以形成人口压力。又如:唐代饶州乐平县东北境有银山,出产银、铜。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隶江西盐铁都院”【124】。显然,邓远与百姓,都不是因为受到人口压力而人山采矿的。《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条下引牛肃《纪闻》称:“江东采访使奏于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125】其时今闽赣粤边界地带人烟稀少,木客人山伐木,亦非受人口压力所驱使。因此,考察南方山区的开发进程,需将山林、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土地垦殖、种植农业的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其次,有关山区开发及其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模式,即:山外流移人口进人山区,山区人口增长一采取原始粗放的垦殖方式,从事农业生产一水土流失逐步加重,山区环境恶化一土地生产能力下降,农业经济衰退。这一认识模式固然揭示了山区经济开发及其经济、环境影响的重要方面,但实际上却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更未能站在山区民众立场上看待山区的开发。问题的关键有二:第一,如上文所及,在南宋以前,南方大部分山区开发的主力应当是山区土著居民,山区人口的增长也主要是这些土著居民的增加;只是到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山外流移人口才成为山区开发的主力军。第二,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原始粗放的垦殖方式”,即撂荒游耕或休耕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山区旱地垦殖的主导性方式,即使是在平原河谷地带已普遍使用犁耕、广泛采用连种制乃至轮作复种制之后,山区民众仍然顽强地保留其“原始粗放的”垦殖方式。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撂荒游耕——休耕制很可能是与山区资源与环境条件较为适宜的农作方式!实际上,山区环境的总体恶化,正是在连种制与轮作复种制在山区逐步推行之后。换言之,很可能正是连种制与轮作复种制的推行,打破了数千年来撂荒游耕——休耕制下山区人地关系的相对平衡与稳定,从而成为山区环境恶化的动因之一。
最后,有关山区开发的研究,一般将山区视为整体加以考察,很少讨论山区内部农田垦辟与耕作方式的差异。我们知道,山区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垂直分布是山区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对山区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演变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受到历史文献记载的局限,我们很难具体分析山区开发在垂直方向上的差异,但至少可以区分出河谷、山间小盆地(平坝)与山坡、山体两种类型。从空间角度看,山区的开发,一般表现为两个方向上的拓展:(1)由河口溯河谷(或山谷)而上,以纵向的拓展为主,地势缓慢地抬升,河谷越来越窄;经济开发在这一方向上拓展主要是垦辟河谷平地、种植水稻等作物。(2)由河谷底部沿两边的山坡而上,以横向的拓展为主,地势抬升比较明显。这一方向上的拓展主要表现为山林砍伐、林特产品的采集与培育以及梯田的开发、种植旱地作物等。显然,河谷地带的开发与山体、山坡的开发是山区开发中同样重要的两个方面,也很难确定其孰先孰后,二者很可能是同步展开、互为补充的。选择历史文献记载较为丰富、较适宜开展田野考察的山区小流域,展开全面深入的综合研究,探究经济开发在上述两个空间方向上的拓展过程,分析其在山区民众生计与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山区社会的建构,将是我们未来若干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注释:
【1】山地(mountain)是指具有一定海拔、相对高度和坡度的地面。广义的山地包括高原、山间盆地和丘陵;狭义的山地仅指山脉及其分支。丁锡祉和郑远昌认为,相对高度在500米以上的区域都为山地(丁锡祉、郑远昌:《初论山地学》,《山地研究》,1986年第3期,第179—186页);肖克非则将起伏高度大于200米的地域均归人山地,并指出起伏高度是指山地脊部或顶部与其顺坡向到最近的大河或到最近的平原、台地交接点的高差(肖克非主编:《中国山区经济学》,大地出版社,1988年,第17—19页)。一般所说的“山区”大致与广义的“山地”概念相一致,即指起伏的相对高度大于200米的区域,它不仅包括高山、中山、低山,还包括高原、山原丘陵及其间的山谷与山间盆地。广义的“山区”概念实际上包括了平原之外的全部地区。据此,我们可将“南方地区”区分为平原与山区两大地理区域类型。实际上,历史时期人们观念中的“山区”比现代地理科学所界定的任何意义上的“山地”都可能要广泛得多,举凡地形崎岖、山岩遍布、可耕地较少的地区,均可称作“山地”或“山区”,而无论其起伏高度是否超过200或500米。本文讨论的“南方山区”,即在从广义的山区角度理解的。
【2】学术界有关历史时期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研究,在时段上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在区域上主要集中于秦巴山地、浙闽山地等地区(参阅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5l页,以及下文所引述之相关论文),而对明清时期之前则甚少涉及。因此,本文在作者近年研究与思考之基础上,对汉魏六朝至唐宋时期南方山区的开发与空间展布作了较详论述,而于明清时期的情况,则主要结合作者及学术界相关研究,加以综合概括,故相对简略。
【3】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杨式挺:《谈谈石峡文化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参阅李根蟠:《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考》,《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孔昭辰、刘长江等:《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与原始农业》,《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陈文华:《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等。
【4】裴安平:《中国原始稻作农业三种主要发展模式研究》,《农业、文化、社会:史前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7—83页。
【5】《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l986年,第85页。
【6】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40《渐江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09页。
【7】游修龄先生谓“鸟田”可能是汉人对“雒田”的越语意译,雒田则是越语的音译,所以也可写作骆田,骆田即是稻田。见游修龄:《中国稻作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36
页。
【8】《史记》卷119《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99页。
【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6页。
【10】《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6页。
【11】[西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1《通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42页。
【12】我们认为,先秦至六朝乃至隋唐文献中所记南方地区的鸟田、雒(嘐)田等,都可能是指平原地区的水田,其垦殖方式是所谓“火耕水耨”(关于火耕水耨的解释,请参阅[日]西嶋定生,冯佐哲等译:《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l984年,第132—167页;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l989年,第9—31页),种植水稻;而在丘陵与低山地区,则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包括旱稻在内的旱地作物。此点涉及南方地区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诸多方面,考另详.
【13】《汉书》卷64《严助传》,第2778—2781页。
【14】林蔚文:《福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15】《后汉书》卷76《任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2页。
【16】《后汉书》卷86《南蛮传》,第2829—2833页。
【1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l987年,第5页。
【1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第20页。参阅张泽咸:《汉唐晋时期农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88—593页。
【19】《史记》卷116《西南夷传》,第2991页;《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所记与此大致相同。
【20】《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第2844—2847页。
【21】《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1页。
【22】《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赤乌五年,征祖中”句下裴注引,第1307页。
【23】《宋书》卷77《沈庆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97—1998页.
【24】《南齐书》卷58《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08页。
【25】《宋书》卷37《州郡志三》荆州“汶阳太守”条,第1121页。
【26】杜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全唐诗》卷22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47页。
【27】杜甫:《夔州歌十绝句》,《自滾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全唐诗》卷229,第2507、2501页.
【28】孙樵:《兴元新路记》,《全唐文》卷79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8327—8328页。
【29】《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福州“永泰县”条,漳州“龙溪县”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8、722页。
【30】《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渝州“壁山县”条,第855页。
【31】《水经注疏》卷39《耒水》,第3216页。
【32】《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袁州宜春县“昌山”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96页。
【33】《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江南道昇州“句容”县下原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7页。
【34】樊殉:《绛岩湖记》,《全唐文》卷445,第4540页。
【35】《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江南道宣州“南陵”县下原注,第1066页;韦瓘:《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全唐文》卷695,第7140页。
【36】《新唐书》卷143《戴叔伦传》,第4690页。
【37】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全唐文》卷805,第8468页。
【38】《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眉州通义郡、绵州巴西郡、剑州普安郡,第1081、1089—1090页。
【39】方勺:《泊宅编》(十卷本)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40】《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十六至四十七,“水利”,(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4928—4929页。
【41】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
【42】畲田乃是山地陆种之旱田,通常是以刀芟去草木,不用耕犁。雨前,焚烧草木,播种于暖灰中,生出的苗不用中耕,不施肥。因此,数年后,畲田便不可复种,只好任它荒废,再去其它地方
耕种。参阅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2—677页。
【43】王建:《荆门行》,《全唐诗》卷298,(北京)中华书局,l999年,第3379页。
【44】温庭筠:《烧歌》,《全唐诗》卷577,第6763页。
【45】薛能:《褒斜道中》,《全唐诗》卷560,第6555页。
【46】《旧唐书》卷117《严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06页。
【47】王禹偁:《畲田词》,王延梯选注:《王禹僻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l996年,第28—29页。
【48】赞宁:《宋高僧传》卷11,《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6页。
【49】罗隐:《别池阳所居》,《全唐诗》卷656,第7602页。
【50】刘长卿:《送睦州孙沅自本州却归句容新营所居》,《全唐诗》卷149,第1487页。
【51】方干:《东阳途中作》,《全唐诗》卷653,第7504页。
【52】淳熙《新安志》卷2《叙贡赋》,《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624页。
【53】戴叔伦:《留别道州李使君》,《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分别见《全唐诗》卷273、274,第3080、3110页。
【54】普济:《五灯会元》卷6《南岳玄泰禅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4页。
【55】《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二六至二七,“刀制”,(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239—7240页。
【56】《宋书》卷47《刘敬宣传》,第1412页。
【57】《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296页。
【58】方勺:《泊宅编》(十卷本)卷5,第30页。
【59】范成大:《骖鸾录》,乾道九年正月三日,《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页。
【60】《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2《蜀志》,广汉郡“什邡县”,犍为郡“南安县”,第166、175页。
【61】《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2《蜀志>,江阳郡“汉安县”,第180页。
【62】《唐会要》卷59《度支使》,(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17页。
【63】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3.《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据康熙三十七年震泽徐氏刻本影印),第6册,第364页。
【64】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原避祸南方者遭遇之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
【65】[唐]韩愈撰,马其昌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序”,《送陆歙州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
【66】《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婺州、衢州,第1592—1593页;
【67】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全唐文》卷871,第9116页。
【68】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6,“鄱阳七谈”,(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92页。
【69】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全唐文》卷819,第8626页。
【70】《太平寰宇记》卷110,江南西道抚州“南丰县”条下,第2238页。
【71】《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信州”条,第678页;《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信州”,第2148页;《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信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6
页;《宋史》卷88《地理志四》,江南东路“信州”,(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87页。
【72】齐己:《暮游岳麓寺》,《全唐诗》卷845,第9628页。
【73】《宋史》卷88《地理志四》,“荆湖南北路”后叙,第2201页。
【74】张方子:《乐全集》卷32《蜀州修建天目寺记分,《宋集珍本丛刊》(第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596页。
【75】文同:《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卷23《绵州通判厅伐木堂记》,《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233页。
【76】《旧五代史》卷80《晋书·高祖纪》天福七年二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58页。
【77】《宋史》卷173《食货志》,第4165页。
【78】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北京)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79】嘉定《赤城志》卷13《版籍门一》,“田”,《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389页。
【80】嘉定《赤城志》卷26《山水门八》,第7483—7477页。
【81】楼钥:《攻媿集》卷7,《冯公岭》,《丛书集成初编》(第200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页。
【82】叶适:《冯公岭》,《叶适集》,《水心文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页。
【83】关于浙南山区的开发,请参阅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84】《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九,嘉定八年七月二日臣僚奏,第2096页。
【85】淳熙《三山志》卷15《版籍类泠,“水利”,《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05页。
【86】淳熙《三山志》卷15《版籍类》,“水利”,第7922—7923页。
【87】《永乐大典》卷2755,“陂”字韵下引《建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407页;又见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71—1172页。
【88】《永乐大典》卷7890,“汀”字韵引开庆《临汀志》,第3622页;又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227页。
【89】《永乐大典》卷7890,“汀”字韵引开庆《临汀志》,第3621—3622页;又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225—1227页。
【90】《永乐大典》卷7891,“汀”字韵引开庆《临汀志》,第3628—3632页;又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250—1270页。关于宋代福建山区的开发,请参阅郑学檬《论宋代福建山区经济的发
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91】《永乐大典》卷2754,“陂”字韵下引《章贡志》,第1403—1405页;又见《永乐大典方志辑秩》,第2037—2051页。
【92】《永乐大典》卷666(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无此卷),引《南雄府图经志》所录寅亮撰《重修凌连二陂记》,《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550—2552页。
【93】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
【94】[南宋]张孝祥著,彭国忠校点:《张孝祥诗文集》卷4,《湖湘以竹车激水,粳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40页。
【95】张孝祥:《张孝祥诗文集》卷5,《前日出城苗犹立槁,今日过兴安境上,田水灌输,郁然弥望,有秋必成。乃知贤者之政,神速如此。辄寄呈交代仲钦秘阁》,第60页。
【96】《永乐大典》卷2217,“泸”字韵下录《江阳谱》,第632—633页;又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3150一3153页。
【97】参阅樊树志:《明代荆襄流民与棚民》,《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钮仲勋:《明清时期郧阳山区的农业开发》,《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马雪芹:《明中期流民问题与
南阳盆地周边山地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l期,吕卓民。《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巴山区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5—201页。
【98】参阅李蔚:《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萧正洪:《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第6期;《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荷兰]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期;陈良学:《清代前期客民移垦与陕南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巴山区为中心》,第242—466页。
【99】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29号,据同治四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l976年,第248—249页。
【100】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23号,据同治四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l975年,第164页。
【101】卢坤:《秦疆治略》,“砖坪厅”条,《中国方志丛书》本(华北地方第288号,据道光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l970年,第127页。
【102】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本第56册(据道光九年刻本影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103】关于明清时期闽赣粤边武夷一南岭山地的经济开发,请参阅徐晓望:《明清闽浙赣边区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l987年,第193—226页;刘秀生:《清代闽浙赣的棚民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l期;陈支平:《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刘永华:《九龙江流域的山区经济与沿海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芳:《明代南方山区的水利发展与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关于湘鄂西武陵一雪峰山地的开发,请参阅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朱圣钟:《鄂西南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关于云贵高原山区的开发,请参阅方国瑜:《清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分,《思想战线》,1976年第l期;施宇华:《明代云南的山区开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陈国生等:《清代贵州的流民与山区开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何萍:《玉米的引种与贵州山区开发》,《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5期。远,易于匿迹潜踪,出没无定”。
【104】毕沅:《兴安升府奏疏》,严如煖:《三省边防备览》卷17《艺文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据道光兴安府署刻本影印,第3页上、下。
【10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2《策略》,第19页上、下。
【106】《三省边防备览》卷12《策略》,第19页下。
【107】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卷17《艺文下》,“会勘三省边境拟添文武官员事宜禀”,第54页下。
【10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2《策略》,第41页上。
【109】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本(据民国十三年刻本影印),第50册,第293页。
【110】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第4页。
【111】《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第12页下一l3页上。
【11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2页。
【113】《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第5页下一6页上.
【114】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3《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宁乡童氏桂阴书屋藏板,光绪末刊本,第6页。
【115】光绪《续修平利县志77卷9《土产志》“洋芋”条,《中国方志丛书》本(华北地方第275号,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55页。
【116】关于玉米、红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引种与推广,请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
与环境演变——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中心》,第293—322页。
【117】道光《石泉县志》卷2《田赋志》“物产”栏,《中国方志丛书》本(华北地方第278号,据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52、54页。
【118】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本(第56册)(据光绪八年补刻本影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119】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本(第56册)(据道光九年刊本影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120】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北地方第270号,据光绪五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57页。
【121】民国《建瓯县志》卷25,《实业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南地方第95号,据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82页。关于闽江上游林木资源的开发及其外销,请参阅陈支平:《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22】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2—23页。关于秦巴山区经济林特产与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以及竹木铁盐资源的开发,请参阅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中心》,第376—465页。
【123】据《宋书》卷35《州郡志一》,扬州“宣城太守”条,第1034页。
【124】《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德兴县”条,第2146页。
【125】《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条,第2034页。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04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