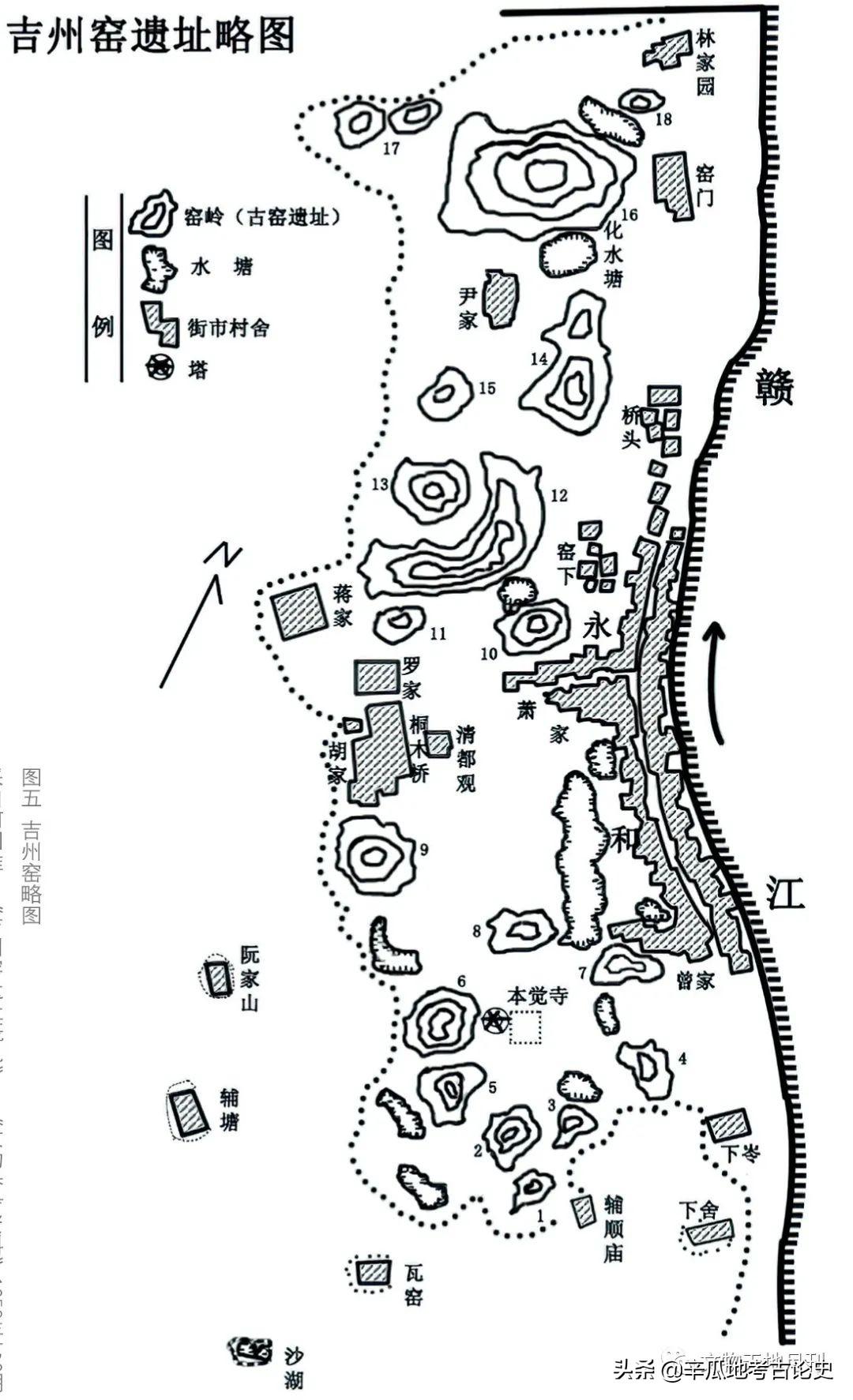陈淳:考古学文化与族属——《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认同》
一、前言
在我国的考古研究的范式中,考古学文化仍然是一个关键分析单位。它被用来分辨史前期和古史阶段物质遗存的时空分布,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就是这一范式的典型代表。文化也被看作某特定人群的物质装备,在欧洲诸如史前期几个主要族群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都是以特定的考古学文化来对应。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基本上也被视为某族群的物质遗存。这种范式就是用分类和类型学来处理大量的材料,用考古学文化来组织这些材料,将其看作是民族学文化一样的研究单位,以便能与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族群单位相对应,从而构建一种类似编年史学的区域文化发展年表。从积极方面而言,这种范式能将海量的出土文物从时空上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会将类型学建构的图像与具体的经验事实混为一谈;也即认为考古学家今天根据器物整理和分辨的分析单位如考古学文化等同于史前人类的社会或生活单位。其危险在于将历史事实大体等同于一种类型学构建,因为这很容易将用类型学方法漠视和排除大量差异而抽取的共性,看作是远古族群和文化的共性[2]。
伦福儒(C.Renfrew)和巴恩(P.Bahen)指出,用考古学文化来重建古代的人群和族属有点危险[3]。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采用少数几种代表性器物的分布来确定文化单位的界线是极其困难的,不同的器物类型在时空分布上往往界线模糊、混杂并呈渐变趋势。因此,定义某分界和单一的同质性文化单位并指认其为某族群的遗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学者主观的判断而已。而且用静态分类所构建的文化单位难以探究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原因,并会囿于传播论的单一思维来重建文化历史。英国学者希安·琼斯(S.Jones)《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一书以现代人文科学的族属理论全面梳理了文化与族群的概念与关系,对考古学分辨过去族群的方法做了全面的评估,为考古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提供极具价值的见地。本文择其精要做了简单的介绍,以期为这本书的内容提供一份导读。虽然在当下的欧美考古学界,考古学文化只是一种材料处理和分析的方法,不再是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概念。但是在我国,文化仍然是史前研究的核心单位。因此,了解本学科关键概念的发展以及国际学界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对我们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无疑助益良多。
二、概念与范式的回顾
从考古学史而言,这门学科就是在欧洲民族主义大背景下诞生的。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指出,考古学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能够为直接与过去相联系的意识提供物质材料。欧洲考古学的初衷就是要将历史从所知的文献记载追溯到更加遥远的过去。19世纪初,英国摧毁了丹麦的海军,使得丹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激起丹麦人对他们伟大过去记忆的渴求。为了策划丹麦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陈列,促使汤姆森发明了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方法,从而成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9世纪末,欧洲对民族身份日益增长的兴趣,使得考古学越来越多地采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因此,将特定器物或纪念物赋予某种民族身份,自考古学诞生以来一直是这门学科探究的核心[4]。
考古学文化作为这门学科方法论的核心概念是在德国最初创立的。德国语言学家和史前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na)采用器物类型来分辨文化,而将清晰可辨的文化区看作是过去部落和族群分布的反映。他还建立了一种所谓的直接谱系学法(direct genealogical technique),以便将见之于史的人群追溯到其史前的源头。科西纳在其1911年出版的著作《日耳曼人的起源》一书中,定义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即分布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里与各遗址相伴的物质文化特征。在一本通俗著作中,他声称德国考古学是“一门最具民族性的学科”。科西纳利用考古学来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服务,以支持雅利安人是杰出人种的神话。战后,科西纳的种族主义观点受到批判,他所倡导的谱系学方法也大体上被摒弃。但是德国考古学家仍沿袭了基本的族群范式,将物质文化用考古学文化来进行人群的分类[5]。
考古学文化概念由英国考古学家家柴尔德(V.G.Childe)的努力而在20世纪20年代发扬光大,影响遍及全球。他的《欧洲文明的曙光》被认为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开山之作,书中他首次利用文化概念整合考古材料,对欧洲史前史做出了全面的历史综述。他对考古学做出的最伟大的创造性贡献,就是用器物类型来建立物质文化的时空关系,并分辨考古记录中特定族群的历史。通过这本书,考古学文化成为所有欧洲考古学家的一个研究工具,并被格林·丹尼尔(G.Denial)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6]。柴尔德在其1929年的《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的序言中,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为“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的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7]。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进行了优化,并将其对应于人群的做法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产;它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共同社会机构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这群人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某人群(people)……于是,考古学家能够将一种文化对应于那个人群。如果用族群来形容这群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史前考古学完全可望建立起一部欧洲的民族史。”[8]不过,柴尔德虽然强调在考古学文化的描述中所有物质遗存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文化都是根据少数几种典型器物来定义的。我国的考古研究基本承袭了柴尔德的方法,以建立区域考古学的文化年表和关系为鹄的,这便有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甚至还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20世纪60年代欧美兴起的新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学偏好描述和经验主义的范式发起了挑战。新考古学主要关注对经济和生计策略、交换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设法运用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等理论,对社会变迁提出普遍性的阐释。新考古学并不关心文化与族群的关系,并拒绝承认文化能够简单地等同族群,并将这种研究看作是一种过时范式的产物。
20世纪末,后过程考古学对政治、社会和个人关注,开始重拾对族属和多元文化的兴趣。世界考古学大会(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成为探讨族属、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考古学伸张自身诉求的主要论坛,聚集了一大批代表不同背景、兴趣和理论视角的学者。世界各国的考古学与当今族群身份认同的交织也非常复杂,考古证据常被原住民用来提出土地和文化遗产归属的诉求,牵涉面广,常常明显带有政治性质。然而,由此产生的潜在问题该如何解决,也成为考古学学科内的争论之源。面对相互矛盾的历史解释,考古学家往往需要充当纷繁和对立的历史阐释仲裁者[9]。于是,考古学家不但面临分辨古代族属的难题,而且身不由己地卷入为当今民族身份和利益诉求提供历史证据的困境之中。由此可见,今天考古学并非仅仅重建历史。这门学科所探索的物质文化与古代民族,对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重建和政治利益显然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三、文化概念的原理
早在考古学文化概念形成之前,欧美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就有对文化概念的探讨。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作为社会成员中个人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一种复杂综合体”[10]。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也认为,文化是一批共同和独特规范的集合[11]体。特里格指出,将时空分布有限而形式上相似的考古材料组合起来标以各种文化或文明,对于许多考古学家来说是独立产生的。这一发展最初大体发生在北欧和中欧,在那里一直有持续的兴趣用考古材料来追溯族群的身份,但是当时这种取向并未成为考古学的范式[12]。
将考古学文化概念作为研究的核心与科西纳和柴尔德的工作相连。这两位学者与一些早期考古学家如蒙特柳斯和莫尔蒂耶出身地质学背景不同,他们有很深厚的语言学功底。而语言的谱系研究往往和族群密不可分,因此他们两位将考古遗存看作是语言一样的文化表现,用物质文化异同来进行族属分析是很自然的推演。
将考古学文化与某特定族群相对应是基于文化的一种标准化观念,好比同一族群的成员讲的是同一种方言。该范式基于这样的预设:在某特定人群中,文化实践和信仰惯于遵从统一的观念准则或行为规范。于是,文化是由一套共享的思想与信仰所组成,并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世代传承,结果就形成了传承与累进的文化传统。柴尔德指出:“代复一代,人们遵循社会的规训,他们成千上万次生产并复制社会认可的标准类型。一种考古学类型指的就是它。[13]”克里斯多弗·霍克斯(C.F.C.Hawkes)精到地概括了文化概念的原理:“将考古学所能理解的人类活动与一系列规范相对应,这些规范能够在文化的名称下整合起来。”他还指出:“在标准的幅度内,分类的界线无论怎样精细地对应差异,类型的概念必须是一致的。而从一种规范到另一种规范的变化必须遵循类型的变化,以及能够推断规范产品标准幅度的变化。”[14]
考古学概念在应用时有几项特点:一是考古学文化是分界或地理上不连续的实体,也即文化区的思想,它们具有由特征随机形成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因此,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彼此独立或分离,能够从时空上分辨它们的存在与分布;二是考古学文化内部是同质性的实体,共享同一文化的人群会在物质文化上表现出同一性或相似性,因此可以从文化特征定义各种考古学文化;三是物质文化的同质性被认为是历史传承或传播接触的产物,而物质文化分布的不连续则是由于社会或自然条件疏远之故。于是,过去人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就能通过考古学组合的相似程度来进行“衡量”。考古类型学的操作原理就是“相似即相近”,即不同的器物群要么反映了社会和地理上的距离,要么是不同人群或不同时代的产物,而相似的器物和器物组合是某同一群人在某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历史学和类型学的断代中,这些观念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5]。
虽然考古学文化是用物质遗存定义的静态实体,可以罗列具体特点和比较它们的亲疏,但是它们也被看作是流淌的实体,即所谓的“文化的液态观”。文化特征被认为从其起源地——某处文化中心——像涟漪一般扩散开去。用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的话来说,考古学的“目的是要表现不同文化源流的发展、互动和融合[16]”。从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实践而言,就是力图构建一个个彼此分离和同质性的考古学文化单位,并用传播迁移论来追溯它们的源流。分辨考古学文化的要义在于确定“典型遗址”,这类典型遗址被认为含有某特定“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分析中,学者们往往只关注某特定区域内“典型遗址”与其他遗址之间的共性和连续性,而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与断裂。在较宽泛的历史重建上,基本是关注各个文化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17]。
四、分辨族属的原理与途径
在人文学科中,分辨族属存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是主观还是客观或主位(emic)或客位(etic)的问题。“主观派”采取主位优先,认为族群是文化上的构建,根据被研究人群主观的自我认定来定义族群。而“客观派”倾向于采用客位的视角,根据分析者对社会和文化异同的观察来定义族群。过去几十年里,客观性的理想在人文科学中一直饱受批评,认为无论主位和客位的视角都掺杂着主观因素。二是究竟是采用一般性视角还是特殊性视角来分辨族属的问题。换言之,我们分辨族属究竟是采用普遍性也即统一的标准,还是特殊性或具体的标准的问题。这两种标准各有其道理和优点,但也有缺陷,即普遍性标准会因过于宽泛而难以解决具体问题,而特殊性标准因过于狭窄而只能用于描述。
采用“客观”还是“主观”方法而造成的抵牾,在纳罗尔(R.Narroll)和摩尔曼(M.Moerman)对泰国北部泐族(Lue)定义的争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纳罗尔采用语言、文化、政体和领地等多项特征来定义一种文化单元(cultunit),他的文化单位是建立在传统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可供比较的文化单位。与此相反,摩尔曼声称,泐族不能根据这类客观和相同的界线来定义,根据民族志的情形,这种界线难以识别。摩尔曼认为,族属定义必须考虑族属的自我认定,或泐族人的自我归属。摩尔曼的主观方法开启了族群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巴斯(F.Barth)为族属的主观派方法建立了一套纲领性理论模型。他认为,文化差异对于分辨族群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尽管分辨族群需要考虑文化差异因素,但是族群单位与文化单位并非对等的关系。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帕坦人(Pathans)自认为同属一族,但是彼此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很大。于是,族属作为一种“自我定义系统”开始集中在族群的认知范围。比如,沃尔曼(S.Wallman)指出,族属是对差异的认知,族群差异就是对“你们”与“我们”之间差别的认识[18]。
尽管“主观派”占主流,但有学者仍按照文化和历史的具体特征,坚持一种客观的族属界定标准。这些学者认为,尽管自我认定十分重要,但是某族群的本质是由真实的文化和语言要素所组成,自我认同也包含了长年累月形成的许多共同“客观”特征,如语言、信仰和价值观等。近几十年来,将族属定义为一种自我界定系统的主位方法十分流行,将族属看作是一种非吾族类的认同意识,一种“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对立。
对于分析族属的成因也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并对如何界定族属具有很大的影响。一种途径叫做“原生论”,由希尔斯(E.A.Shils)提出,目的是为了分析亲缘关系内在的特质[19]。这种“原生观”采取主位途径,将族群的认同意识归咎于与生俱来的依附感,由血缘、语言、宗教、地域和文化等纽带所造就和维系。这种原生依附感并非个人自愿,而是外来强加的。这种强大的依附感源自所有人都有一种归属和自尊的要求,是一种人性之本。因此,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长久不衰。原生论也得到了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的支持,认为群体内成员有一种友善的共同情感,而对异族则有一种敌意。这种族群间的竞争具有一种生物学的基础,并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部落性和民族中心论的由来。
原生论的优点在于关注民族依附感的感情功效以及文化的象征作用,而从这种视角看待考古学文化,两者有十分契合之处,就是族属的原生论有助于解释物质文化的独特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但是,原生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它将族群认同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心理倾向,具有朦胧和返祖的特点。其二,原生论无法解释个人层次上的族属游移性,也即个人会在不同情况下利用其族属的不同表现,甚至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其三,从人性来解释族属,使它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自然现象。其四,原生论漠视族属的社会和历史基础,将血缘关系看作是民族性的根本[20]。
分辨族属成因的另一种途径叫“工具论”,将族属看作是随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而变的一种动态群体认同,并采取客位视角,关注族属在协调社会关系和协商获取资源中的作用。科恩(A.Cohen)强调族群是保护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种集体性组织策略,并利用文化使社会行为系统化,追求经济和政治利益是族属形成的基础[21]。工具论将族属看作是一种可变物,其主要特点随不同背景而变化,并取决它在构建社会互动中是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视角克服了原生论的局限,为了解族群的形成和族群政治化的过程做出了贡献。
但是,工具论也有其缺陷。其一,它将族属的实质简约为利益群体的文化与政治策略。其二,强调族属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漠视它的文化方面。其三,漠视族属自我认同的心理学基础。其四,将族属的利益观看得过分简单。其实,同一族群内的成员在利益和认同方面未必完全一样,并会以不同方式行事。其五,从利益和政治来定义族群,会难以与其他的利益群体相区分。
原生论和工具论在族属成因阐释上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又具有互补的方面。麦凯(J.Mckay)试图糅合两种观点,将它们纳入统一的阐释模型。这一模型构建了一个行为类型学,其中包含了一定原生论和工具论因素。比如,他认为犹太人对原生性的关注远胜于对物质的关注;美国白人的“假族群”对原生性和物质都不在乎;还有“族群好战分子”如巴斯克民兵组织和现在的“伊斯兰国”,他们对族属原生性和工具性的关注都很强烈。麦凯指出,他的模型主要是描述性和经验性的,并不想解释群体的出现、延续或消亡,或为什么原生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各有千秋[22]。
克服主位与客位、原生论与工具论两难境地的桥梁,是布迪厄(P.Bourdieu)实践理论中的习性(habitus)概念。他认为,习性是由某些观念和实践的持久积淀所构成(比如劳动的性别分工、伦理、品味等),它从小就成为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能在不同背景中变换。习性包含了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其中新经验会按照老经验产生的结构来构建,而早期经验仍占有特别的比重。以这种方式体现的力量,导致了某种积淀(认知和行为方式的结构)会潜意识地影响实践。用布迪厄习性概念开发一种族属理论,提供了一种手段来将族属的原生论和工具论整合到人类能动性的一种连贯理论之中。因为认识到族属从某种程度上源自共同的习性,因此可以这样说,常与族群认同和族群象征相伴的强烈的心理依附感是由这样一种关键作用产生的,即习性塑造了个人的社会自我意识和行为方式[23]。
五、物质文化与族群的关系
对考古学文化与过去族群相对应的反思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考古学文化是否能对应特定的族群;其二是考古材料分布的性质与考古学文化作为分析单位的地位;其三是分界和同质性的族群和文化实体是否真实存在。
对第一方面的思考是认识到,考古学文化用类型学“相似即相近”的单一参照框架所做的阐释是不够的。除了规范性原理之外,还要考虑考古材料的分布的异同还可能反映了过去人群的不同活动或行为。因此,考古材料的异同不能简单地用来分辨或衡量族群的关系。这一反思突出表现在博尔德与宾福德对莫斯特文化的争论上。博尔德根据类型学差异分辨的四类莫斯特文化群体,在宾福德看来只不过是同一群体从事不同活动留下的不同工具套而已。
除了质疑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外,考古学文化本身是否真的存在也受到了质疑。正如戴维·克拉克(D.Clarke)所言,实际上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考古学文化,因为“没有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组合能够包括所有的文化器物”[24]。柴尔德很早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觉得每个考古组合不可能包含某特定文化的所有类型,因此他强调用反复共生的类型来定义一个文化。在具体操作上,柴尔德将并不重复出现的类型从典型器物的级别上降格,以此来清除凌乱的数据和材料,以求保证文化典型特征的相似性[25]。于是,就如戴维·克拉克所言,这种方法出现了两套系统,“在阐释的理论层面上主张严格的一致性归组,而在操作层面上则根据直觉评估从较为宽泛的近似度和相似性来归组”[26]。还有学者批评,考古学文化的确立是根据漠视一些差异而将某些现象归到一起,如果用其他分类方法归组的话,这些现象之间是无关的。还有人指出,考古学文化并非界线分明的实体,而是处于一种渐变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文化实体纯粹是考古学家自己想象的东西[27]。
还有就是对是否真的存在分界族群的质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接受族群是动态和因势而变的看法。物质文化可以被积极操纵来维持群体关系,而族群认同和物质文化在经济和政治压力下也分别会发生强弱和不同的变化。希安·琼斯指出,物质文化是多义的,它的意义因时而变,取决于它特定的社会历史、特定社会参与者的立场,以及它所直接使用的社会背景。而且,物质文化不只是含义累加的仓储,带有它在不同社会背景里的生产与用途和因势而异的参与者的印迹。她指出,考古学家不应认为,物质文化的异同可以提供一种族群亲疏关系的直接证据[28]。
用考古学文化代表民族学意义上的具体族群或他们的物质文化表现,是建立在文化规范理论上的固有想法。像民族学研究一样,考古学根据少数几种代表性特征的分布来分辨这类文化和族群单位的界线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不同器物类型的分布界线存在模糊、混杂、重合、交融以及式样渐变的情况,因此人们意识到,过去被解释为行为上的(交流或入侵),谱系上的(历史传承)和沉积上的(混杂)文化现象,其实是采样和类型学分析存在偏颇的结果。而且,在方法论上仅采用少数几种代表性类型(如标准化石、关键类型和标志性类型)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单位,并在区分文化单位时偏好有或无的质量标准,而非数量统计,使得文化的异同其实只是人为的一种错觉而已。比如福特(J.A.Ford)指出,当用来定义考古学文化的选择样本范围较小的时候,类型和文化性质看上去会十分真实和自然,但是当样本覆盖面扩大时,它们会开始重叠和模糊,类型的规范或平均值会发生变化,归于同一文化的各种组合和亚类型也会变得面目全非[29]。
六、结语
考古学文化概念是19世纪末随着对民族身份日益增长的兴趣而产生的,并在德国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成型,最后由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奠定了作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随后,柴尔德自己也对考古学文化是否能够等同于过去族群表示怀疑。随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这一范式的概念和类型学方法持续受到质疑,转而从文化功能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文化的运转系统。于是,考古学文化概念退出了范式的核心概念。虽然在操作中这一术语仍然会被作为某种时空分析单位来应用和某种人群的物质表现来指称,然而分辨和确立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学科的终极目的,而是处理材料的一种途径以及需要做出解释的现象。希安·琼斯撰写的《族属的考古》是在20世纪末族属与民族主义再次成为考古学热门话题的背景中撰写的,目的是希望考古学家采取一种逻辑步骤来反省考古学是如何解释群体身份认同的,对文化与族属的关系做一番彻底的清理,并为考古学为当今族群的争议做出贡献。
根据人类学的观察和学界的反思,没有单一类型的社会单位可以对应于一种考古学文化。用文化来定义社群,犹如用语言来建立族群认同一样,是一种高度主观的构建。无论语言和器物类型,与族群或人们共同体的分类并没有一对一的相伴关系。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Hodder)的一个研究案例显示,社会群体所使用的不同器物有着不同的生产背景和分布范围,它们并不重合。他在对肯尼亚巴林戈湖地区三个不同部落妇女耳环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耳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部落群体之间的界限,但是它和其他器物比如陶器的分布范围却不重合[30]。其他研究也显示,陶器的分布在不同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原因和机制,它并不一定和民族群体的范畴相合。比如,美国亚利桑那霍比印第安人的陶器形制随居住点地形的不同而异,并不与聚落、血缘群或宗族关系相对应。墨西哥塔拉斯坎陶器的形制分布则和陶工的交往有关,并不反映群体之间的界限。于是,考古学界不再认为事情有那么简单,可以根据标志性特征或相同器物组合把一批遗址归入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中,然后认定,每个“文化”代表了某一社会群体或人们共同体[31]。
现在我们意识到,物质文化的多样性是有各种原因造成的。除了族群差异之外,它们有的可能反映了时间上的差异,有的则是环境背景、可获资源、当地手工业生产和装饰传统、贸易方式、地位竞争、性别身份、群体间通婚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在考古学研究中仍拘泥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运用,只注意类型的异同,文化的差别,并试图以此来重建已逝的历史,解释纷繁的历史现象,几乎成为难以企及的目标。根据特征罗列描述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定义和解释,无疑是考古学者本人的一厢情愿和一己之见,即便是考古学界的共识也未必就是真理。目前,文化单位只不过是考古研究的一种概念和分析工具,它必然会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变化。目前,考古学文化概念在国际上已经被文化系统和聚落考古学等新概念所取代或涵盖,这表明半个多世纪来的考古学发展已经从物质文化表面的分析转向更深层次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探讨。虽然这一术语仍不时见于一些西方的研究报告中,但是它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已经大为淡化。这是因为学术界意识到,用器物类型这种人为确定的单一标准难以衡量和研究由多元变量和复杂因素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现象。
从社会角度来审视考古学文化概念,有两个主要的缺陷。其一,考古学文化概念比较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似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会,比如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由于这些社群规模较小和相对独立,所以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稳定性。对于流动性很大的狩猎采集群,比如我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和极地的爱斯基摩人,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和不同群体之间存在频繁接触,使得广阔地理范围内分布的文化遗存看上去十分相似,难以确定和研究群体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其二,考古学文化概念不大适合研究内部分化明显的复杂社会。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分化会造成文化差异和多样性,比如玛雅帝国贵族和平民所表现的物质文化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亚文化”或两类族群。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比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不同社群在对外交往上日趋频繁,特别当贸易和交流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特点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和差异从文化特征上观察时就会变得十分模糊,比如,族群众多和国家林立的苏美尔从物质文化上观察是同一类考古学文化。特里格指出,商文明、商时期、商民族、商代、商国和商文化是范畴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不能互换。商代国家也要比考古学定义的商文化范围小得多[32]。普罗塞尔(R.Preusel)和霍德指出:“描述某地区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将遗址与器物归入能够比较和断代的文化单位的范畴。对文化特征发展、传播和流动的描述,就能建立起一个时空体系,并成为一个新地区进行研究的基石。”[33]加里·韦伯斯特(G.Webster)指出,文化历史考古学真正想做并仍然在做的事情,是想将主位与客位联系起来,将学者的考古学文化的构建与古代遗存的创造者联系起来。这是困难的,也许是做不到的。它被公认具有双重的难度——双重解释学的问题,即考古学家必须在他们的物质分析框架与对象人群框架之间进行转译[34]。
希安·琼斯的著作,对于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学者的有关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对应关系的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并为我国考古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带来了某种启示,这就是需要对我们习用的学术概念和范式保持探索精神,不应将范式在实践中看作是深信不疑的公式而进行照章办事的操作,并密切关注国外同行的学术进展。我们只有对习用方法的不足保持理性的头脑,对国际学界的进展保持一种取长补短的态度,我们的研究水平才能精进,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
(作者: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教授)
注解:
[1] 复旦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项目编号:12&ZD152。
[2] Webster,G.,Cultural History:A Culture-Historical Approach,in R.A.Bentley,H.D.G.,Maschner and C.Chippindale eds.,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Lanham:Altamira Press,2008:11-27.
[3] [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 [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5] Jones,S.,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London:Routledge,1997.
[6] [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Childe,V.G.,The Danube in Prehistory,Oxford:Clarendon,1929.
[8] Childe,V.G.,“Is Prehistory Practical?”,Antiquity,1933,7:410-418.
[9] 同[5]。
[10] Tylor,E.B.,Primitive Culture,London:John Murray,1865.
[11] Durkheim,E.,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8th edition),Glencoe IL:Free Press,1938[1895].
[12] 同[4]。
[13] Childe,V.G.,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6.
[14] Hawkes,C.F.C.,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 from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4,56:155-168.
[15] 同[5]。
[16] Steward,J.,Review of “Prehistoric Culture Uni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Northern Arizona”,by H.S.Colton,American Antiquity,1941,6:366-367.
[17] 同[5]
[18] Wallman,S.,Ethnicity Research in Britain.Current Anthropology,1977,18(3):531-532.
[19] Shils,E.A.,Center and Periphery:Essays in Macrosociology.Selected Papers of Edward Shils,vol.II,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7:111-126.
[20] 同[5]。
[21] Cohen,A.,Introduction:The Lesson of Ethnicity,in A.Cohen(ed.)Urban Ethnicity,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4:ix-xxiv.
[22] McKay,J.,An Exploratory Synthesis of Primordial and Mobilizationist Approaches to Ethnic Phenomen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82,5(4):395-420.
[23] Bourdieu,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4] Clarke,D.,Analytical Archaeology,London:Methuen,1968.
[25] 同[13]。
[26] 同[25]。
[27] Hodder,I.,Simple Correlations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ety:A Review,in I.Hoddered.,The Spatial Organisation of Culture,London:Duckworth,1978:3-24.
[28] 同[5]。
[29] Ford,J.A.,On the Concept of Type:The Type Concept Revisited,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4,56:42-53.
[30] Hodder,I.,Symbol in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见[3])
[31] 同[3]。
[32] Trigger,B.G.,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1999,1:43-62.
[33] Preusel,R.and Hodder,I.ed.,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ry,Oxford:Blackwell,1996.
[34] [美]加里·韦伯斯特:《文化历史考古学述评》,陈淳译,《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来源:复旦大学博物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文化遗产研究集刊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 0002
- 0000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