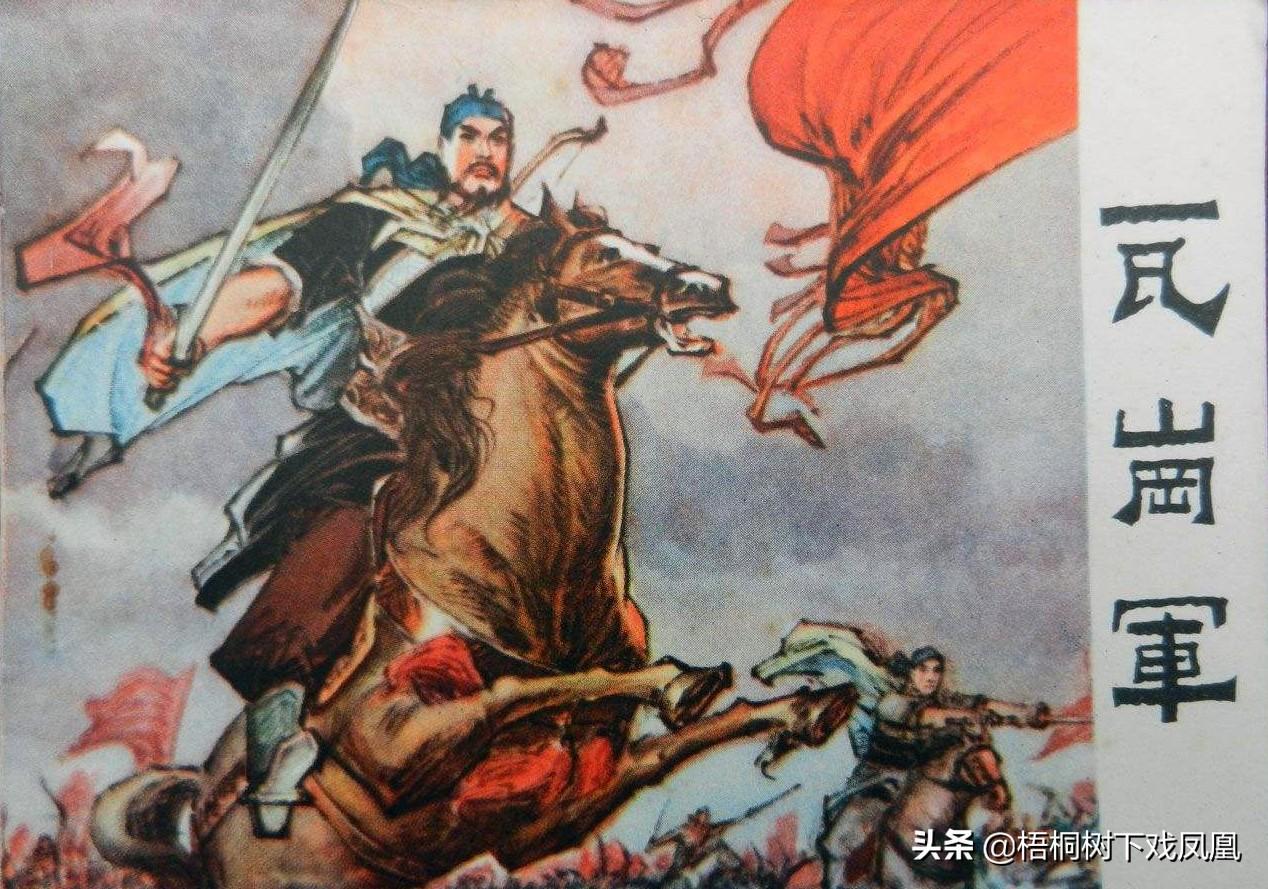何炳棣|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四)
四、人本主义哲学的形成:周公、孔子
研究哲学思想,商代卜辞用途不大。诚如前辈思想史家侯外庐所指出:“卜辞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39]因此,笔者二十五年前即注意最古文献的史料价值,去年秋冬之际对《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的《商书》再度做了认真的外证内证工作,说明它除了小处难免周初史官润色之外,应可确认为商代传世最重要的文献。由于《盘庚》历史真实性的肯定,所以我们可以较有信心地说,前此海外汉学界的看法——“帝”是商人的至上神,“天”是周人独有的至上神,“天命”的理论是周人所创建,与商代的宗教观念大相径庭——是错误的。事实上至晚从盘庚起(迁殷是在公元前1300年),帝与天已是同义词,周人的宗教是由商引进的。《盘庚》篇中已有雏形片段的天命、勤政、去奢、恤民等观念的存在,但就观念的深度和理论体系而言,与周公所阐发的天命论是无法比拟的。
研究周公思想的宝贵原料是《尚书·周诰》诸篇。天命论有三个组成部分:商代享国五百年,最后坠失天命之故;周以蕞尔小邦数世即能承受天命代商称王之故;和周公一再对周人的警戒,天命难恃,一切还是要靠人的努力。理论精华在第三部分。
商代之所以能享国久长主要是因为一系列先王“罔不明德慎刑”、“不敢荒宁”、“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等美德。坠失天命是由于商末诸王耽于逸乐,荒政失德。周族之所以能代商承受天命为天下主大都由于文王敬天、恤民、勤政、恭俭等等美德。这些都是学人所熟知的,毋庸赘述。
周公对周人谆谆训诫之语是古今中外研究天命论者所特别注意的,倒有较详列举的必要。为便于参考,以下也选录《诗经》中周初类似的箴言:
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诰》)
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尚书·大诰》)
惟〔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
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尚书·君奭》)
天不可信。(《尚书·君奭》)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
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诗经·大雅·文王》)
天难忱斯,不易维王。(《诗经·大雅·大明》)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诗经·周颂·敬之》)
前辈学人中,周公天命论的重要诠释者是郭沫若和傅斯年。先引郭说[40]:
……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像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周人……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礼记〕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
另引傅说[41]:
〔周公〕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无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憸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如是之天道即人道论……周初人能认识人定胜天之道理,是其思想敏锐处,是由于世间知识饱满之故,若以为因此必遽然丧其畏天敬天之心,必遽然以为帝天并无作用,则非特无此必然性,且无此可然性,盖古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存心虔敬,信人是其心知,信天是其血气,心知充者,血气亦每旺也。
如果仅就《大诰》及专对殷人讲话的《多士》、《多方》三篇而言,郭沫若对周公权术玩弄面的剖析无疑义是犀利而又正确的。古今研究《尚书》史实功力最深的顾颉刚先生即指出,文王和《大诰》中的周公都曾“为了笼络人心……装神作鬼,说是在占卜上承受了天命……”[42]。傅斯年认为这是次要的,他得出周公对天命虔诚的结论,也正是郭氏所讥讽的。笔者认为人类史上自始信仰的强弱即与事态发展结果的吉凶分不开的。《大诰》前后的周公处境殆危,除背水一战外,别无良策以保文、武造成的基业。发动东征的前夕,周公对天命之兆内心未尝不是疑信参半的。经过“破斧”、“缺斨”三年鏖战险胜之后[43],对天命在周的信心虽然加强,而对生死斗争不断反思之后,益觉胜利得来之不易,因此才屡度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等言,并一再强调政治军事的成功,无一不靠举族上下,戮力同心,竭尽所能,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努力。“周公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正是傅说肯切深刻之处。但他对周人成功的总释——心知血气两旺——似乎有点神秘。事实上,天命和人事本是从一系列斗争之中才能融为一体的。
对《周诰》诸篇一再细嚼反思之后,笔者觉得《君奭》篇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在这篇里,周公不但最坦诚无隐地道出“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天不可信”等语,而且开头第二段的谈话最中肯要:
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
权衡中外各家之说,试以白话力求把原义解释明白[44]:
你已经对我说过:〔凡事要〕靠我们自己。我对天命不敢十分放心,也不敢不从长远处去观测天的威严和我们人民〔的意愿〕;〔人民之所以〕没有抱怨和不服从,〔正是由于你我了解关键〕在人〔不在天〕。
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全人类第一次出现人神关系里关键性的改变——人的理性和政治实践使天秤倾向人方。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历史透视:周公把上古中国思想引进了人本理性的新天地;后继者终于替他脱去宗教的外衣。历史的公道正在不断筛去糟粕,保留弘扬精华。更须一提的是:周人是在周公领导艰苦斗争中才培养出勤朴武健、果毅敢为、居安思危、慎始慎终等后代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德。
周公至孔子五百年间文献有阙,但人本(较小范围是“民本”)理性思想的发展可由当时智者之言窥测梗概。为便于参考,早于周公的名言也按时代先后并加号码征引如下:
(1)《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案:周公、成王等所谓之“古人”至晚亦应系商代哲人。《史记·殷本纪》:“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可见历史上极少有百分之百的神权国家,商国祚能维持五百年之久,立国必有其“民本”理性的内核。
(2)《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据《书序》,应系武王伐纣誓师之辞。
(3)《国语·郑语》:“《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4)《左传·僖公五年》引《尚书·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5)《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6)《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7)《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传》(前662):“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8)《左传·僖公十九年传》(前641):“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9)《左传·昭公十八年传》(前524):“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
以上所引诸语皆出自政治领袖或高级知识分子。最足以反映当时这种人本理性思想已深入民间的,莫如《左传》所记成公五年(前586)晋国一个押送载重大车的“重人”的言论和见解。此年晋国发生梁山崩的“灾异”,国君召大夫伯宗回京都绛城商讨处理办法。伯宗所乘的传车与一载重大车狭路相逢,交谈如何让路时发现重人是绛人,伯宗故装不知,问他京城有何大事。重人说:“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伯宗问他应如何处理,重人回答: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
开头说山崩是由于岩土松“朽”,是自然现象,人又有何办法?原辞中“不举”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从简之意,“降服”就是不穿邦君平常的华丽衣服,“乘缦”就是所乘的马车上去掉装饰品,“彻乐”是不奏音乐,“出次”是离开宫室暂去郊野小住,“祝币”是由专管通神司祭仪的祝去陈列献神的礼物,“史辞”是由史官撰拟朗诵祭神文辞。在遵守当时礼制与无法确知人神之间是否真有交互感应的前提下,国君所应做而又能做的也只有表示自省的诚心和对神的敬意而已。孔子诞生前三十五年,平民中居然能产生连子产和孔子都无法超过的理性和智慧!
一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照例以孔子为起点,本节的讨论却以孔子为终点。孔子的哲学体系是中外治中国思想史者所熟知的。本节收尾部分只扼要讨论孔子的宗教观、道德观、社会观中甚有意义而又似未曾受到普遍注意的几点。
先谈孔子的宗教观。第一应指出的是孔子对天与天命的看法。《论语》中天凡十七见,内中有几次是出于他弟子的谈话;但帝字却仅出现三次,而且都在全书之末《尧曰》篇所征引的成汤的古话。这似乎反映自西周开国至孔子的半个千纪间,天、帝混一近祖文王式“具体”的至上神已演变成代表抽象至高的道德裁判者。如: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论语·子罕》)
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对中国影响最大、最能引起西方人文主义者赞扬的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与处理原则: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樊迟问知(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大多数中外学人都认为以上保留在《论语》里的话代表孔子高度的理性、智慧和他“不可知论”的基本立场。
笔者认为当代多数学人的意见颇值得商榷。主要是因为他们事先并未把孔子及其他智者(如子产等人)所受西周开国以来礼制的影响及其全部宗教观加以深广的探索,并且在解释《论语》中极为简略的原辞时,不知不觉地就把近代的观念注射进去。最懂“祭神如神在”的真义的是《礼记·祭义》。此篇开头就说祭祀先人之前斋沐期间即须“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这样致斋三日之后,才能把受祭亲人生前的容貌衣着、言行举止活现在心里。祭的时候,更须尽量使自己进入恍惚的境界“以与神明交”,这样才能在庙室中仿佛能看见亲人“入室”的模样,祭终“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样从几天前就开始逐渐把自己“催眠”到祭祀时候的半迷惑的状态,才配称为孔子所说的“与祭”的情感状态和心灵境界。孔子如果不能把自己引进到这种意境,就不如根本不参与祭祀,这才是“吾不与祭,如不祭”的真义。“与祭”与宗教心灵境界实在是非常接近的。
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和“未知生,焉知死”这类话虽然代表了他高度理性的一面,但其真正意涵远较近代多数学人所诠释的要复杂得多。如《论语·述而》[45]: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可见师生都不以祷告为迷信。知道子路已经按照礼俗为他曾向“上下神祇”祈祷之后,孔子马上就坦白自招已经自行祷告好久了。当然,孔子曾经按照礼俗做过祈祷绝不能过于简单地被释为迷信鬼神者,但他显然也不是《天演论》作者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首创自称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者[46]。
此外,孔子也不是如弟子们所说完全不谈“怪、力、乱、神”中之“怪”与“神”的。由于华夏宗教从很早就有神之人化与人之神化的双向发展,所以内容复杂的周王室与列国的祀典一向杂糅神话、传说、史实于一炉。这些都是博闻强记如孔子者必备的知识的一部分,也是各国当政者不时要向孔子请教的历史掌故。孔子既以尽力恢复周初礼制为一生最大使命,祀典既是礼制的主要部分,所以孔子有正面忆述回答有关祀典掌故的义务,而并无辨析掌故的理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意愿和责任。祀典内外的种种掌故当然含有不少非理性怪异的成分[47]。
孔子一生言行都说明他对周代(特别是周初)文化、制度、以祖先崇拜为重心的宗教都有极大的敬意。他对生死鬼神的几句所谓的“怀疑主义”的名言,是出自他绝对诚实的认识论(详下文),并不足以证明他对宗教本身的怀疑。相反地,他对宗教的社会教育功能有深刻的了解。《孔子家语·观思第八》保存了以下的故事[48]:
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者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子贡之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死者有知无知是认识论中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为社群、国家的安定着想,祭祀祖先以延孝道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因为这是社会人伦教育的起点[49]。所以在《孝经》开首,孔子就对曾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孔子死后2,080年在北京开始定居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所洞悉的祭祀祖先的真正用意——不是相信祖先之灵真需要食享,而是为了后嗣的基本人伦教育——与孔子初衷正相符合[50]。
正确了解孔子的宗教观就势必涉及孔子的认识论。《论语·季氏》言及知识之来源: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初看之下,“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在认识论上是一种矛盾,而且《论语》中对前者毫无例证。根据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最近极富原创性的《说“格物”》[51],远自传说时代很多部族都相信他们始祖是上帝派到人间“生而知之”的圣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其曾孙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帝舜生而精于制“陶”和“什器”。《史记·周本纪》中言及周族始祖后稷自幼即知稼穑。其他先秦典籍又述及只有像黄帝和禹这类圣王才能为万物命名,并能以德致物。如舜“致异物,凤皇来翔”。由于“生而知之者”既能知物、名物、致物,而致和“格”古义相通,所以最后构成《大学》中最重要的语句之一“致知在格物”,以格字代致,完全是由于修词方面需要避免在一句中重复两个致字。所以20世纪三代新儒家认为程朱等理学家“格物致知”含有科学精神的说法,是与“格物致知”最初的意义恰恰相反的。
孔子接受“生而知之”的说法与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尊敬是一致的,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认识论的重心。孔子认识论的精华正在“学而知之”这方面。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自己回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终身学习不断。同篇中更说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和反思的同等重要。在《论语·述而》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自己承认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不断从尽可能广博的闻见之中评价和吸取知识者,而且绝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不真懂却凭空造作之人。所以孔子认识论的中心就是《论语·为政》篇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名言。此中真义,《荀子·儒效》略有阐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换言之,其中永恒的价值就在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这种绝对诚实。同样可贵的是在绝对诚实的原则下,只有禁得起事物、理性检核征验的才能被认为是知识。这正解释了何以孔子对祭祀的心理、政治、社会、教育的功能虽具深刻的了解,但仍是对弟子们做出“未知生,焉知死”的结语。
处理了孔子的宗教观及认识论之后,他其余的主要贡献就可极简括地说明了。如果说周公把古代中国哲人的思维引进了人本理性的新天地,并且已经对“德”的意义做了较深刻的阐发,那么孔子就是全部人伦关系价值及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把人群所有的社会及政治关系“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仁”字。孔子“仁”说绝不是自始即系统化的,而是逐渐积累不断阐发而成的。早在1930年代初,冯友兰先师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中即讲得很清楚,“仁”几乎包括所有的“道德”,如礼、义、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孝、勇等,是一切内在道德动力的总汇。三十年后冯先生把孔子的“仁”视为孔子的“精神世界”[52]。重要性仅次于“仁”的“礼”,则居于从属地位。但笔者觉得“仁”和“礼”这对整体与部分的哲学范畴应该加以深索。“仁”作为一个整体是至高至大;“礼”仅仅是“仁”的一个部分。但最堪注意的是就二者关系而论,部分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整体,有时还高于整体。如《论语·颜渊》篇,颜渊问如何实践“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的具体细目时,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既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礼”作为“仁”的一个部分,竟能控制、界定“仁”这个整体实践的范围。这是由于“礼”的最原始意义是祭祀的仪节,宗教仪节照例是具有顽强保守性的。但“礼”是多维度的,自始即具有维系稳定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多方邦国,夏、商、周三代王国的演进,这些由小而大的政治单位不得不越来越缜密地发展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等分,物资分配制度、习惯法、行为规范、雏形成文法,以及早期零散、后期逐渐系统美化的礼论,以为意识形态的重心。孔子建立“仁”说时,广义的“礼”已经存在、发展、演变了好几千年了。由于孔子的经验世界无法超越广义的“礼”,所以“仁”的施行对象处处必须受“礼”的限界。这正说明何以作为“仁”这整体的一部分的“礼”,竟不时居于主宰的地位[53]。
除了构成以“仁”与“礼”为重心的道德哲学体系以外,孔子还是国史上第一位人文大师,以类似小组研究班(seminar)的方式来讨论知识、修养、政治、伦理等问题,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案:六艺有两说。一是指六种著作:《礼》、《乐》、《书》、《诗》、《易》、《春秋》。一是孔子自述“游于艺”的六艺,是指消遣、练习、实践性的“礼、乐、射、御、书、数”[54]。这种人文教育的性质与内容,足堪媲美古代希腊和罗马,要比中古欧洲丰富多采。
孔子以“仁”与“礼”为重心的道德哲学在过去两千年的人伦社会实践上的影响深而且巨,有如摩西十诫和《新约》之在欧西。此外,孔子又为两千年人文教育奠下深厚的基础。孔子代表渊源悠古的人本宗教、思想、文化及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综合与结晶。
注释
[39]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一册《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79—80。
[40]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页20。
[41]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页287—293。
[42]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页49—50。
[43]《诗经·豳风·破斧》,此诗之前的《东山》述及东征战士终于回家,说明:“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44]译文大体根据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与底注。参阅The Chinese Classics, vol.3, The Shoo King,原序1865(台北翻印本),页175。案:理氏从事中国经典汉译工作自始即与王韬合作,《尚书》为最早英译对象。详见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页142—144。笔者对理氏相关译文仅作一必要的句标纠正。
[4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82,注释:“诔,本应作讄,祈祷文。和哀悼死者的‘诔’不同。”
[46]参看Bernard Lightman, The Origins of Agnosticism: Victorian Unbelief and the Limits of Knowledge(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亦可参考以下几种百科全书中Agnosticism专文:“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1961;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1969;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68。
[47]《国语·鲁语上》,柳下惠(展禽)于鲁文公二年(前625)谈制祀原则:“……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凡有大功大德者,死后皆应被祀为神。《鲁语下》即保留下孔子所忆述的三个古代掌故和怪异,原文长,兹不赘。但我们应附带一提,一再拒绝为火灾和不平常天象而举行祭祀的,能讲出高度理性“天道远,人道迩”的子产,还是相信“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的。见《左传·昭公七年》(前535)。
[48]刘向,《说苑·辨物》亦有此故事,文词有修饰,不如《家语》文词近古。R.p.Kramers, K'ung Tzu Chia Yü: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Leiden: Brill, 1950),对版本源流考证甚详。结论:书内虽有若干部分经王肃修改以为批驳郑玄之用,其书大部分应是传自阙里,保存不少孔子弟子所记孔子轶事及谈话。考证较《四库全书提要》为精审。
[49]《礼记·祭统》:“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伦焉。”十伦包括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所以祭祀涉及全部宗教、政治、社会、人伦关系。
[50]Louis J. Gallagher trans,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p.96.
[51]裘锡圭,《“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卷1。此文简要,但极富冲击力,对今后研究宋代理学家“格物致知”真谛及其可应用的范畴,大有裨益。
[5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3]参阅何炳棣,《原礼》,《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02—110。关于《论语》仁、礼关系中礼限界仁或在理论层次上高于仁的词句及其诠释,请参阅何炳棣,《答孙国栋教授“克己复礼为仁”争论平议》,《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特别是页132。
[54]《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591)大夫申叔时所述太子应该学习的是以天时纪人事的“春秋”、记先王之世系的“世”“诗”“乐”、先王官法时令的“令”、治国足供参考之“语”、记前世成败的“故志”和远古记述族类的“训典”。内容与孔子的六艺很相近,代表春秋贵族所受的是当之无愧的人文教育。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