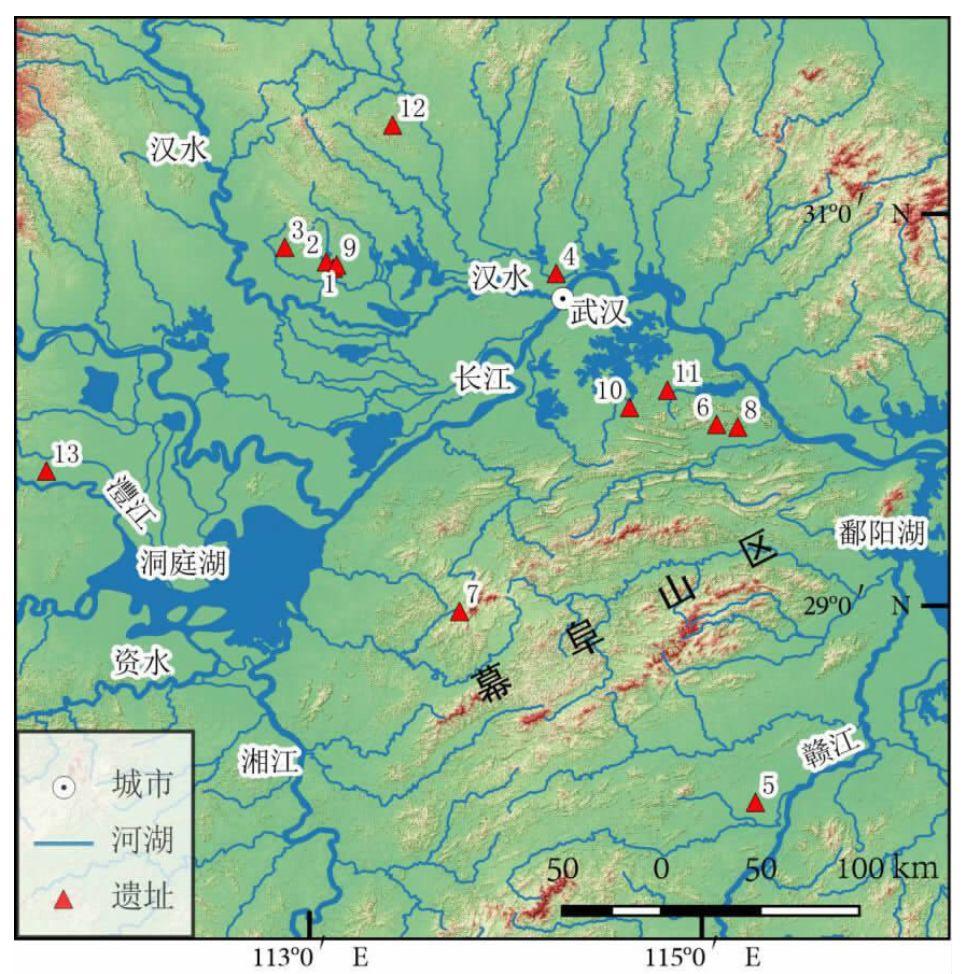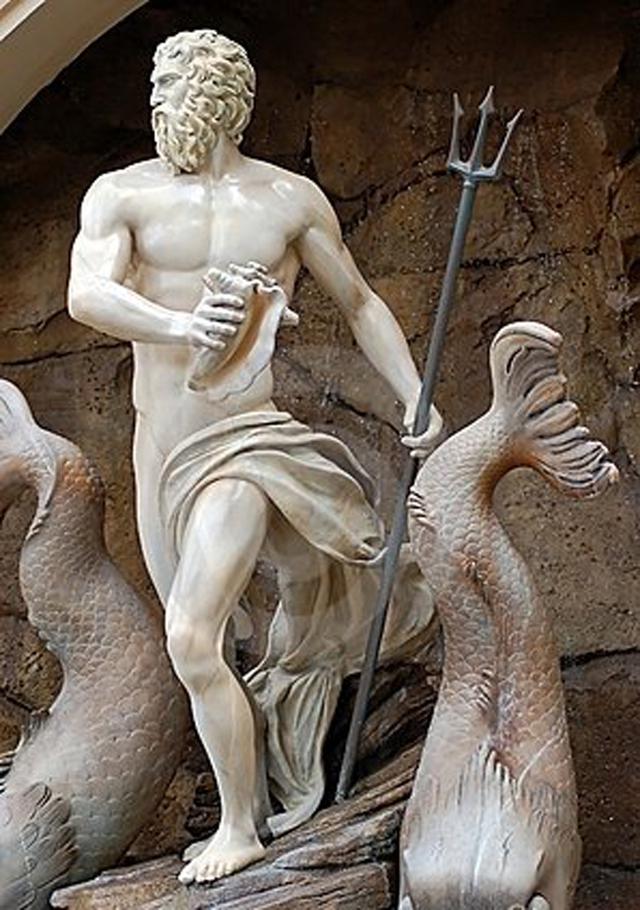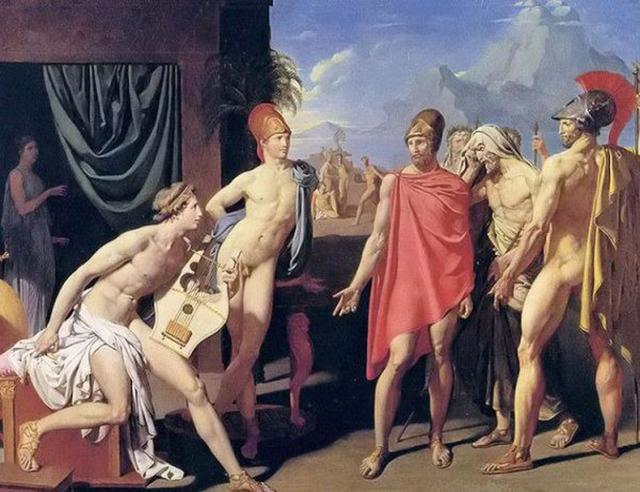我和李零先生的一些接触——《丧家狗》改了七八个月
作者:黄海龙(《丧家狗:我读论语》责编)
来源:深圳晚报 2008.05.05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微妙得有点奇怪的事情。有些人可以和他一起喝酒,而有些人则只能和他一起喝茶。酒是热闹的亲密的,茶是清静的淡然的;喝酒时粗糙一点更有气氛,喝茶时则需要点儿客气谨慎。
因为责编《丧家狗:我读论语》和《放虎归山(增订版)》两本书的缘故,我和李零先生前后有过一些接触。就我所接触到的一面来看,我相信李零先生就是适合和他一起喝茶的一类。
李零先生的文章,那是确实漂亮,不服不行!这里我继续说说我对于李零先生的一些私人印象。
印象中第一次和李零先生比较近的接触,是2006年春节后。北京,大雪,在一家山西菜馆午宴,除李零先生外,还有张鸣、李亚平、余世存等六七位先生都在座。那天最有趣的一幕是,好几位先生都每人要了一瓶山西老醋在喝。李零先生是山西人,喝醋品醋尤胜一筹。而我偏是恶习不改的南方人,吃饺子都不用醋,第一次看到一堆人拿着醋瓶子往自己嘴里灌,觉得很是稀奇、好玩。印象中只有余世存先生和我在喝白酒,并且主要是余先生一个人在喝,我是后生小辈,属于“沉默的少数 ”。尽管如此,余先生还是端着酒杯一个一个地和大家碰杯,看得我甚至有一点点紧张:知识分子在饭桌上,喝起酒来都是温文尔雅的,敬酒已是难得,更何况是举着酒杯去敬别人的醋瓶子!我也很清楚地记得,李零先生在文章里说过是不喜欢“轮番敬酒”的。当余先生的酒杯敬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底一片歉疚:让人给我敬酒已属大不敬,而我连回敬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敬酒就要敬完一圈,我是不大有勇气闯这个连环阵的!
后来和李零先生的较亲密接触,就是出版《丧家狗》的时候了。这本书的初稿很早就完成了,那时候论语还没有热起来,我印象中记得是《丧家狗》的修改快接近完成的时候,于丹的《论语心得》才在中华书局紧张赶制出来。而李零先生的这次修改,差不多就改了三个月之久,接下来的编辑工作又花去了近四个月的时间。所以有读者若以为《丧家狗》是跟了谁谁谁的风,那实在是莫大的冤枉!
做李零先生图书的编辑,要说容易也特别容易,但要说困难,却也比较困难。这里先说容易的部分。容易之处在于,编辑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做做校对:校校文字,并尽量按照通行的出版规范对数字、排版格式等作些统一而已。所以有时我向朋友开玩笑说:等我将来老了,“德高望重”的时候,我也可以哈哈大笑着告诉围坐身边的小青年们,想当年,在我还是一名校对人员的时候,我曾经校对过李零先生的著作;在李零先生家里工作过,看先生为了一个字、一处引文,在他那一排满是大部头书籍的书架上抽出一部书来,戴上眼镜慢慢地查找、核对;还和先生一起单独共进过lunch,不过只是喝粥,吃一小碟豉汁排骨而已……
这里说的“只是做做校对”,是因为编辑只需要做校对,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李零先生交来的书稿,每一篇文章、附录、图片资料,乃至全书的目录,都总是处理得干干净净,编辑无事可为;二是李零先生会取标题,所以豆瓣网上有人说“零公是个标题党”,确确实实,在李零先生取的标题面前,再优秀的编辑恐怕也只会觉得汗颜。《花间一壶酒》、《丧家狗》和《放虎归山》,三部书里所有的标题都是李先生自己做的,编辑只有学习的份。不能要求每个作者都很会做标题,但作者交稿时的文字干净,对编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幸福。在我过去五六年的图书编辑生涯中,有两位作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文字干净得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之一就是李零先生。我想李零先生的这种作风,应该是和他做学问时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一脉相承的。《丧家狗》一书改来改去改了七八个月之久,也有这个原因。有时候我提出来某段引文中有个句子不太通,李先生就立马找出来原书,翻到引文的出处细看一阵,好像在思索似的,然后告诉我:原书就是这样的呀!
其实我是属于比较“敢”改作者原稿的那种编辑,尤其是绝大多数作者都并不能像李零先生这样,把自己的文稿处理得干干净净,让编辑无事可为;而现行的图书出版规范又不允许一本书里犯太多的错误,所以编辑界前辈如王云五所谓“不改作者一个字,错别字也不改”的古训,我是遵守得很不好的一个。不过在与李零先生的接触中,我可是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另一种严苛:改动任何一处字词,都需要经过作者本人的审阅、同意。好在我是一个感觉还算敏锐的人,在进入《丧家狗》一书的编辑流程不久,我很快就发现了原来心存的那种作者交完稿后、由编辑大包干的意愿,是多么的傻!所以很快我也学会了对于“的、地、得、了”这样的简单问题,或者明显的别字,都在清样上标出来,请李零先生定夺。后来读到李零先生的《南白与北白》,说是最怕南方编辑给他改文章,不由得心里暗笑,尽管我倒不是有经常给别人的文章乱加“的、地、得”的毛病,但这种“最怕”,确实是李零先生最真实的心声。
说过了“容易”,再说说“困难”。现在回想,整个《丧家狗》的编辑过程里,印象最深的似乎就是标点符号的间距问题:双引号或者书名号和其他标点之间,间距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排版软件在这上面总是处理不好,李零先生就会以他一贯的严谨,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提出来。偏偏这本书双引号用得又比较多,实在不是个容易对付过去的问题。李零先生以他的做学问的态度来要求编辑处理好书的每一处细节,比如封面、版式、标题的字体、注号(圆圈还是方括)、引文的格式、数字的用法,等等。这对编辑是个挑战,然而对于读者,是个福音。亲爱的读者,一本书里,每一处可都是凝结着作者和编辑的多少汗水啊,呵呵。我还记得,李零先生在交代改稿的时候,会突然轻轻而不失严厉地问一句:你在听我说话吗?把我投放在书稿上的目光收回到他的眼睛上。或者是在改稿清样上,以特别工整的行书标明:不要乱加“的”字(其实那个可有可无的“的”字是录入人员不小心加上的)。
最后给大家露一点八卦消息:我感觉李零先生,生活方面有点像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村青年,虽然很早就进了城,但也一直学不会玩;不管是演讲、出席会议,李零先生都总是拎一个布包,发言也都是念提前准备好的讲稿,如果只是闲聊,那他思索的时间肯定比说话的时间要长得多;还有,李零先生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书,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初版之后,《丧家狗》重新改了不下100页,《放虎归山》重新改了35页,通常都是些特别小的改动,比如一处标点,一个“的、地、得”……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