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刘威:从族群边界理论看考古学文化的边界—《族群与边界》
自古以来,我们都认为夏商周是在年代上接续未断的三个历史朝代。自新史学与近代考古学产生后,有学者认识到,夏商周还是以三个族群即夏族、商族与周族为主体的王朝,但所谓三个“王族族群”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长期共存。因此,可以说过去关于夏商周学术焦点问题的探索,基本上可以用“族属与文化”这一核心词汇来指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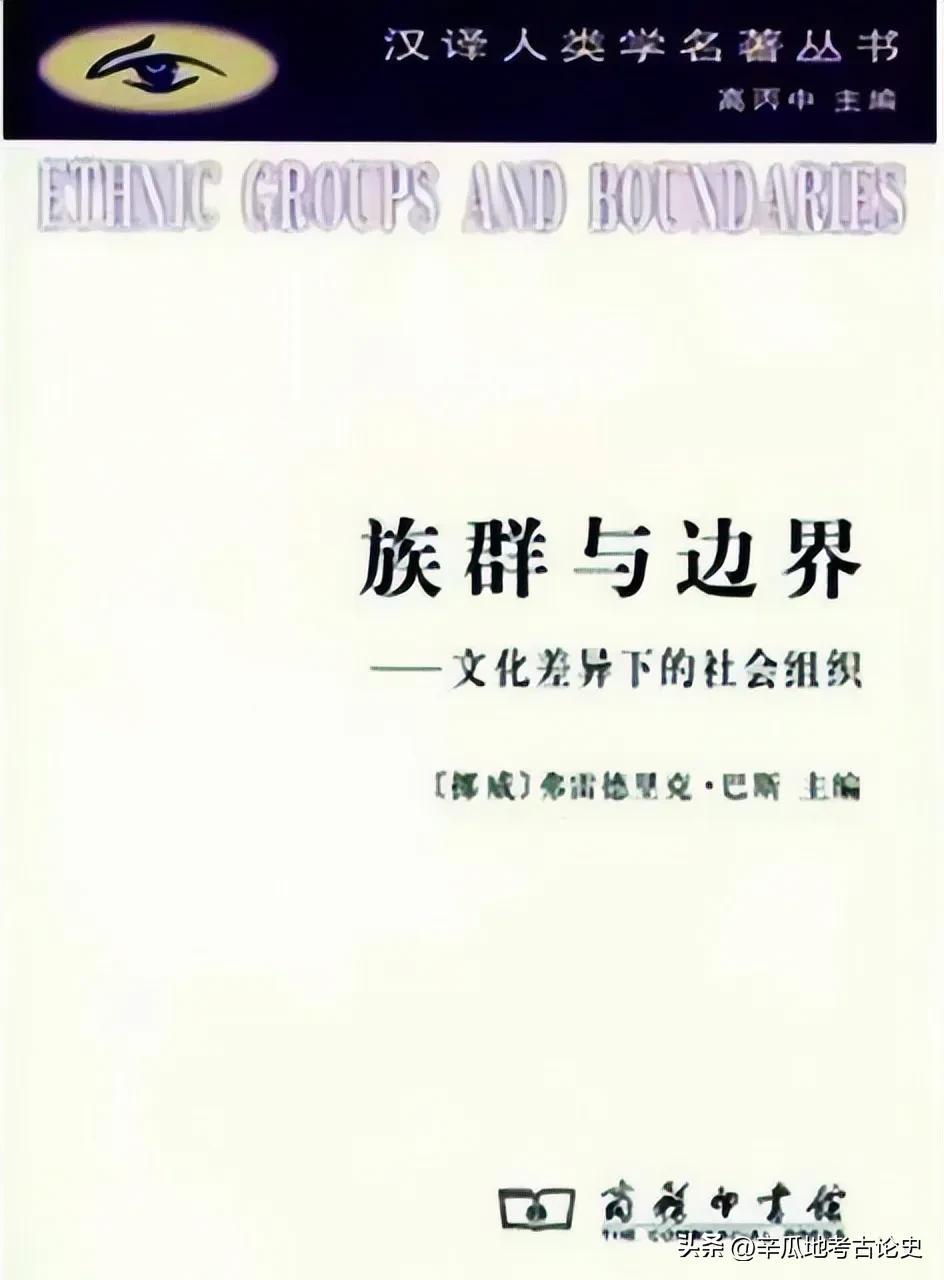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北平研究院在陕西的周秦古迹调查与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等在河南豫西的调查,可以看作是考古学上探索商族、周族、夏族文化的经典工作。近年来,伴随着夏文化讨论热潮的又一轮兴起,学界关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对应思索愈加深刻。然而,我们至今也未能在这一思索上得到一些公认的结论,夏商周三个族群与夏商周三个时代的考古学遗存的对应,任重道远!学术探索陷入僵局,使得不少人开始思考所谓的“族属与文化”是否真的可以对应?我们旧有的学术方法是否能够突破瓶颈?探索族群与文化对应的思路是否需要改变?
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知道,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向来是极其复杂的,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却极为单薄。因此,探索族群与文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向其他学科借鉴理论与方法,并将之运用于考古学文化及其背后人群的对应问题。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下称《族群与边界》)一书,该书基于不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个案,集中讨论了近现代的族群与边界问题,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为我们思考考古学文化的边界及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提供了新思路。
一、差异的建构——族群边界理论
《族群与边界》包括七个人类学个案研究报告和弗雷德里克·巴斯的一篇导言,导言其实早在上世纪末就已为国内所熟知。七个个案讨论的具体问题并不相同,但都在讨论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即族群边界是如何形成的。族群到底是什么?弗雷德里克·巴斯对此给出了自己的标准:A组成个体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性,B共享的文化与价值,C构成一个联系与互动的范围,D拥有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定的成员资格。
四个标准至少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标准A,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概念,它强调的是体质特征,一般而言隶属于同一族群的个体具有相同或极为相似的体质特征。第二个层次是满足A和B,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这个层次是在体质特征的基础上,还着重强调文化特征,比如生活方式、生计模式、显性特征(语言、房屋类型、武器……)、行为评判标准等等。虽然在跨学科认知上,种族和民族还具备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学意义,但不妨碍我们界定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第三个层次即族群,需要同时满足A、B、C和D四个标准。
巴斯对族群的阐释可谓深入人心,以致几乎整个人类学界都认为族群的核心是认同(即D),认同又包括表达技巧、价值体系和自我认同三大方面。与族群息息相关的另一常用术语是族属。什么是族属?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它的认知似乎仅停留在血缘关系层面上。比如《礼记·大传第十六》中说“同姓从宗,合族属……正义曰:同姓从宗者,同姓,父族也。从宗,谓从大小宗也。合族属者,谓合聚族人亲疏,使昭为一行,穆为一行,同时食,故曰合族属也”。
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宗族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并非绝对的血缘网络。从这一点看,周代社会所谓的宗法制度,实际上也是社会组织制度,至于其是否能与《族群与边界》讨论的社会组织相符,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周代宗法制并不能代表文化差异,而只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等级关系。那么,人类学概念中的族属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比较简单,从字面意思出发,族属其实就是族群身份的归属,比如所谓汉人与满人的差别。因此,反过来看,所谓族群实际上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一个族群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族属。由此,如果我们将族群的核心认同归之于族属上,其实所谓满人、汉人的差别,也是身份的认同而已。那么,族属的核心也就是认同。这一认同相比族群的认同而言,更为直接与彻底,尤其是在族群边界上。
关于族群边界的确定,《族群与边界》给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认识。所谓边界,也没有明显的边界,族群的边界大体上可以看成是至少两种族群交汇杂糅、杂居情况频繁发生的地带,这种地带往往是族属认同常常容易发生变化的地带。如果某族群中发生了族属认同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的并不是整个族群,而是发生变化的族属。如何确定族属认同的变化,才是确定族群边界的核心问题所在。
在《族群与边界》中给出的思路是研究差异,他们认为趋同性并不能判断族群,反而要求异,要在文化差异下建构不同族群的个性特征,而文化差异的地带就是所谓族群边界。简而言之,族群边界理论强调在文化差异明显的边界地带构建不同族群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集合体反映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族群核心认同。据此,我们就能辨识出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特质。一旦族群的文化特质发生了变化,就意味着其中至少有某些族属的认同发生了变化,边界也就会随之变化。
二、共性的叠加——考古学文化
而这一种研究思路,恰恰与考古学文化的辨识思路相反。考古学文化是建构史前文明体系的核心概念,它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龙山文化这一考古学的概念曾经滚雪球般地从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浙,再到长江中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会有如此情况,原因就在于考古学文化是根据物质遗存的共性特征而建构的。我们知道考古学文化有三个特质,一是时空,二是地域性,三是物质趋同性。过去将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相对应都是基于这三个特质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的。
比如李伯谦先生就曾提到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一般大家都把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因为上文已指出族属的范围相对族群更小)对应的五项“指标”,包括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文化关系(《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其中前四者均要与文献记载相符,实际上就是变相地使用“二重证据法”判断族属,这种方法对没有或者缺乏文献记载的史前及青铜时代的族属判定几乎不起作用,它是为适应历史学研究而设定的,显然是中国考古学在探索族群上的史学倾向表现。
如果回到考古学文化本身,就会发现考古学文化实际上还能反映物质文化的变化过程,而在《族群与边界》中强调地族群认同也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就目前而言,学界对族群认同的动态变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动态变化如何对应的研究,展开的远远不够。更何况,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本身并没有强调判定族群认同和体质特征的标准,这与《族群与边界》中巴斯倡导的族群概念没有相互对应。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认为,从认同的动态演变角度看,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一种考古学文化能与(某)族群(族属)对应?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三、新的想法
我们以为,考古学文化对应族群的前提是发现认同稳定情况下的族群所遗留下来的较为稳定的物质文化遗存。如果能像人类学家根据文化差异确定族群边界,考古学者也从物质遗存的差异来确定考古学文化的边界,那么边界以外的所谓“核心区”或“非边界带”就可能存在着单一、稳定的考古学文化(物质遗存共同体)。这时,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就能一一对应了。实际上,考古学文化只能解决稳定的族群对应问题,如果说文化因素分析法可以分析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动态变化情况,那么就要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去思考族群认同的变化在物质上的变化情况。
如何研究认同与物质的变化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而且又涉及到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对应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并非可以使用族群边界理论将任何考古学文化都去和族群进行对应。可以举夏文化的对应为例。我们知道,夏文化的概念定义虽有多种,但其中核心都包括夏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很明显是一个“杂交概念”,既不是考古学文化,也不属于族群。针对这样一个全新学术概念的探索方法,却从来没有超出考古学的学科范畴,所谓夏都法、夏墟法、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方法,都是从考古学角度讨论一个非纯粹的考古学问题,在方法上就显得“先天不足”。
从理论上看,两种极大差异的物质遗存共同体可能代表了至少两种不同的物质认同。在两种极大差异的物质遗存共同体交界地带,其物质遗存应该是杂糅交错,族群(族属)认同可能处于反复变化的状态。如果充分理解这种交界地带的形成与演变,显然有助于我们分析出这一地带不同阶段物质遗存来源的变化情况,还能由此看出其他较为稳定地域的物质遗存表现形式,那么就有可能发现那些较为稳定的物质文化遗存共同体,而这一较为稳定的物质文化遗存共同体可能就对应着一个单一的、稳定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族群。
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缺陷,这一缺陷也源于考古学文化概念本身。考古学文化不适于研究社会复杂化较强的族群,历史上的夏是作为国家而存在,其社会复杂程度必然达到了考古学文化无法阐释的状态。以目前多数学者认同的作为夏代都邑的二里头遗址为例,其遗址面貌反映出来的物质文化来源多样性极为复杂,显然无法找出其中呈稳定、单一的族群文化遗存。
因此,关于考古学文化边界的研究,应该回到简单社会组织并行的时代,比如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知道,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发展的阶段产物。放在有充分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实际上不同族群的边界差不多等同于王朝国家的疆界。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法区分出历史时期准确的文化遗存边界或族群边界。边界向来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带,它时刻在变动。这一点与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期段遗存分布范围的变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重要的是,考古学文化本身是一个根据遗存共性建构的概念,我们常常根据一个遗址发掘出土的部分遗物所代表的特质来命名该考古学文化,并以之衡量其他遗址是否与之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这种范式本身存在前提漏洞,是需要改变的。如何改变,从差异出发是否能建构?不得而知。但至少值得去尝试,当然也只能在社会复杂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尝试。除此之外,族群与考古学文化是两个学科的不同概念,单纯以考古学方法是难以解决二者的对应关系。
我们需要尝试寻找联结人类学族群理论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桥梁方法。在方法尚未健全的情况的下,我们排斥所谓夏文化这类“杂交型文化”概念的使用,它本身造成了我们对探索二里头文化或这一时期物质文化之间关系的难度与复杂性。简单地说,夏文化本身是考古学方法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如果试着从族群边界理论出发,强化对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边界地带的研究,由此发现边界地带以外可能存在着的单一的、稳定的物质文化共同体,再将其与族群加以关联。总而言之,要在确立差异性的最大限度基础上,再去寻找稳定的物质文化共同体。
- 0000
- 0000
- 0001
- 0002
- 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