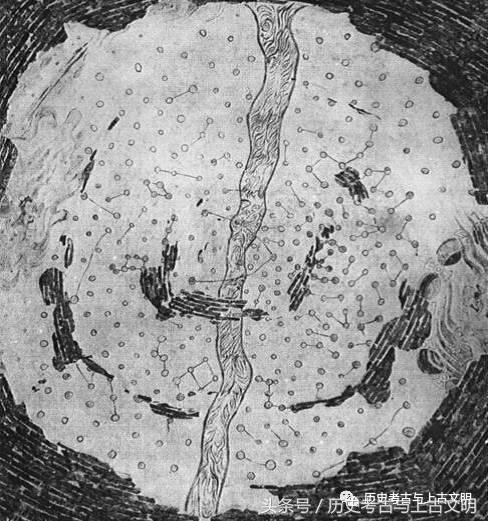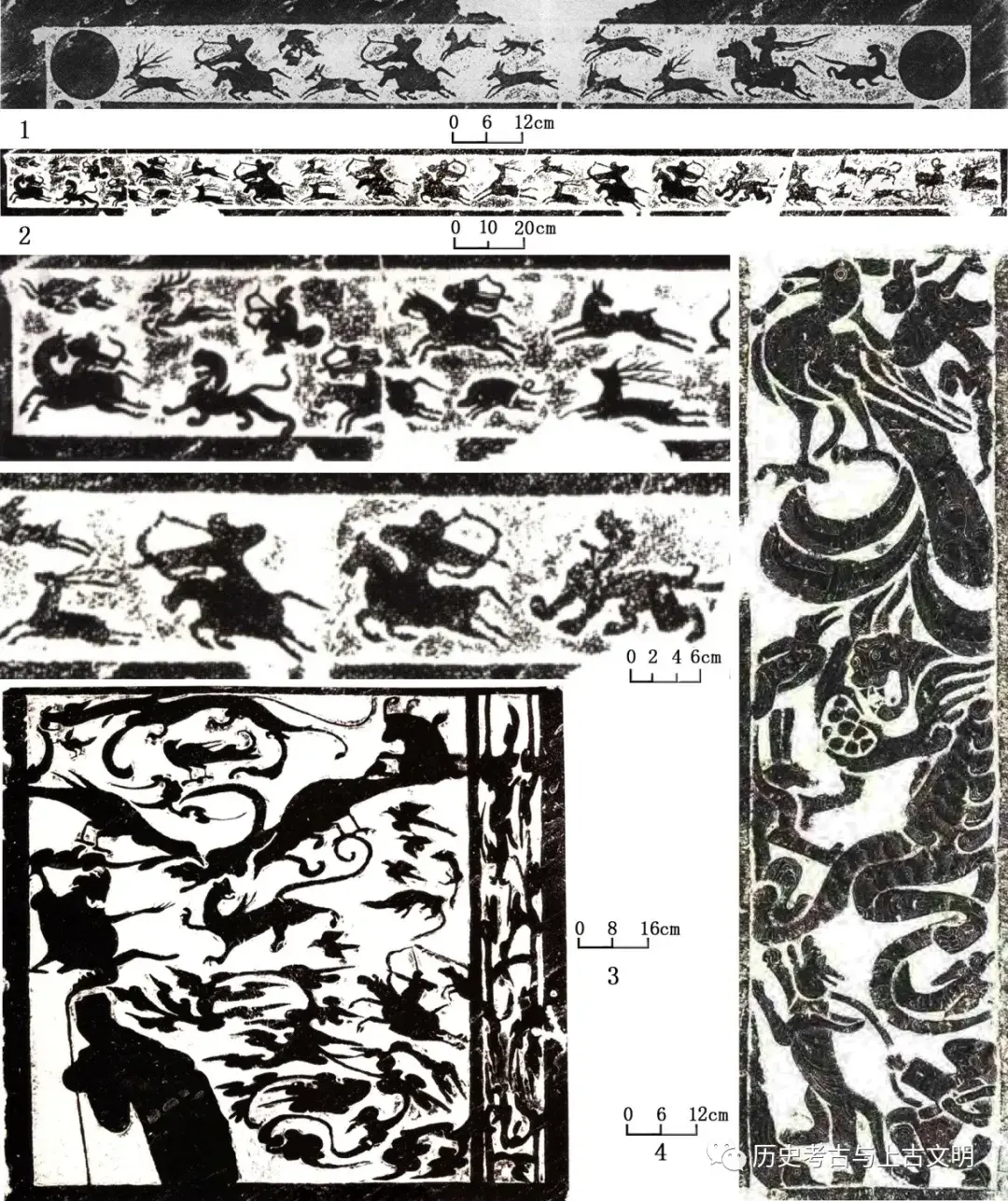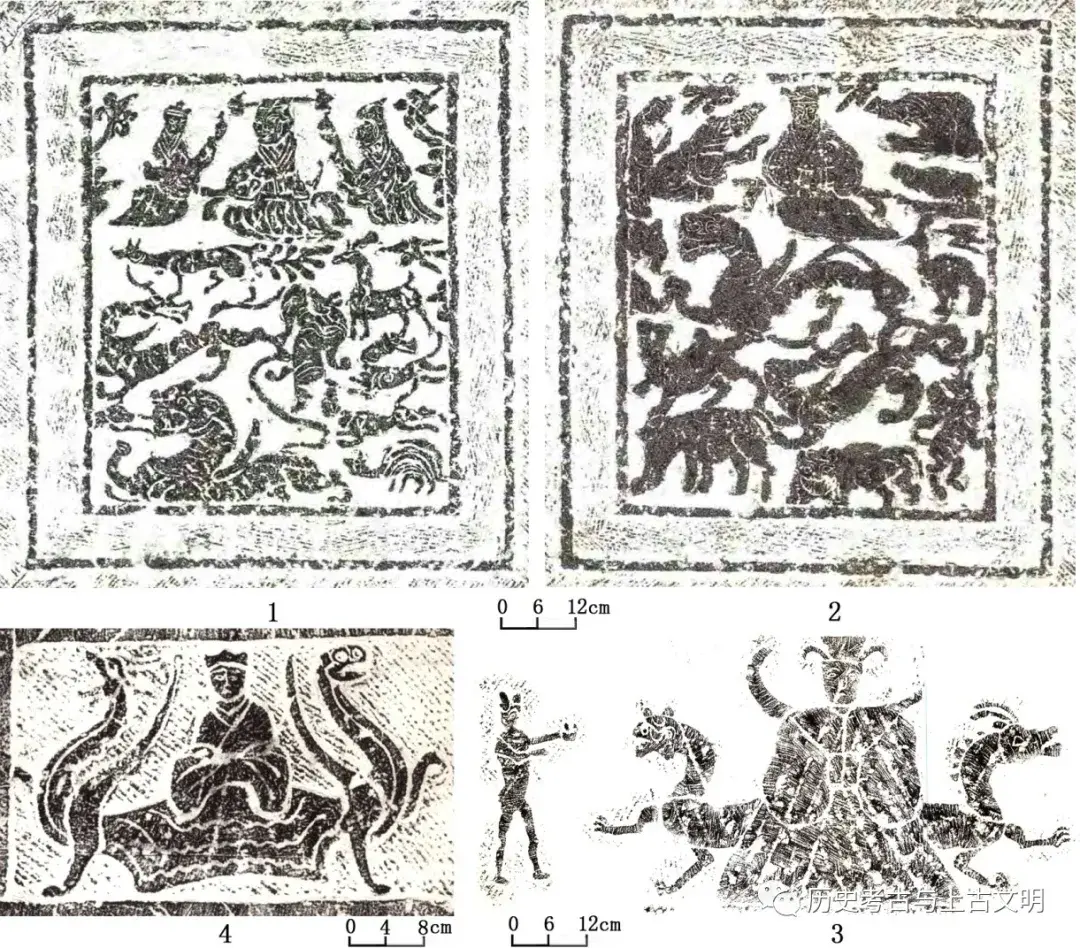特里·欧文:柴尔德的冷战之殇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的柴尔德,已广为学人所知。他提出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至今仍是讨论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革命”的主题贯穿其一生的学术生涯。无论是柴尔德早期倾注大量热情的劳工运动研究,还是后期以考古学为手段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探索,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柴尔德的这一思想立场,使其与左翼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紧密关系,他的离奇去世或与此有关,虽然相关报道否定了这一联系。澳大利亚学者特里·欧文《政治的致命诱惑》一书,讲述了政治观念与参与在柴尔德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他对这种政治所带来的历史理论的贡献。本文即选自本书的前言和后记。
冷战之殇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出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在人类文化演进论研究中“位列最重要的理论进步”。他出版过21本专著,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此书面世的头15年就在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售出30万册。他还撰写过281篇论文或论著章节,在99种期刊上发表了236篇书评。他的声望并不局限于英语世界。他的书被翻译成21种语言,而他本人也足迹甚广,曾亲赴欧洲、俄国、土耳其和印度,以及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讲学。
在他去世后的30年里,由各大出版社发行的作品,还要多于他30余年职业生涯发表量。最近一次专门评价其成就的学术会议举办于2007年。他的名字甚至在学术界之外也广为人知。2008年的电影《夺宝奇兵4:印第安纳·琼斯和水晶骷髅王国》(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中,男主角骑着摩托车闯入大学图书馆时一个学生认出了他,并请他讲解文明的传播。这位男主角是一名考古学家,兼职拯救文明(尽管他刚刚才严重破坏了一件文明成果),当即重执教鞭,建议学生去“查阅戈登·柴尔德的著作”。
 ▴这是柴尔德希望他那些1920年代的朋友们记得的他的样子。
▴这是柴尔德希望他那些1920年代的朋友们记得的他的样子。
电影的故事发生于1957年,正值冷战高潮,也恰是柴尔德逝世之年。整部影片带有一丝颇令人意外的颠覆意味,揭示出大学之中也不乏麦卡锡分子(McCarthyite)的打压。男主角印第安纳·琼斯在闯入图书馆前,曾被几个破坏美国原子研究站的苏俄人俘虏。在经历了一次离奇的逃亡之后,他重新站上讲台(我们听到他在讲授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柴尔德最著名的发掘工作),但旋即被大学解雇,因为联邦调查局(FBI)认为,他既然与苏俄人士一起出现过,就意味着他是个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在大学里的好友因为同情他而辞职,这暗示着FBI的干涉影响颇广,柴尔德对此一定深有体会。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pacifist)、反帝国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柴尔德受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甚至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监视长达40年。这样的监视曾多次干扰或阻碍他的事业。而当他的尸体在悉尼西部山区的悬崖下被找到时,甚至有人猜测他的死既非自杀也非事故,而是一次谋杀。
柴尔德经久不衰的声望既源于他广博的思想,也来自他在考古学和史前史领域的影响力。但是他对社会进化、知识理论以及历史阐释的兴趣,不仅显示出他思想的广度,也将他置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并认证为左翼知识分子。将柴尔德的政治与事业的联系,是本书研究他生平与思想的起点。这一研究试图将柴尔德置于左派异见知识分子(dissenting intellectuals)的传统之中,并据此理解他的人生、考察他的思想,从而理解20世纪上半叶紧贴这一传统的政治思想。柴尔德在学术上的声望基于他自1920年代中期起在英国所从事的工作,是可以被称为他的“第二人生”的成就。他在33岁时出版了第一本有关史前史的著作,35岁时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学术职位。因而在此之前,他有充足的时间去体验他有趣的“第一人生”;事实上,他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的阶段,曾经打算投身政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在悉尼大学读本科时,他就一直活跃于工党、社会主义、反战和激进民主等左翼政治阵营。与此同时,他在悉尼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业也表现出色,然而,当他在澳大利亚申请相应的学术职位时,大学当局却与商界精英和澳大利亚联邦军事间谍通力协作,确保他无法成功获得聘任。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寻找工作,在1918到1922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里,都受益于工党的资助。他在“第一人生”中所实现的成就不在大学,而在接地气的工会大厅(Trades Halls)和政党办公室;不是对着人文科系的大学生讲课,而是与政治宣传者和工党议员们交换意见。
 ▴柴尔德在1930年代,一位衣冠齐楚的教授(安德鲁·斯旺·沃森[Andrew Swan Watson][爱丁堡]拍摄)。
▴柴尔德在1930年代,一位衣冠齐楚的教授(安德鲁·斯旺·沃森[Andrew Swan Watson][爱丁堡]拍摄)。
柴尔德在“第一人生”中所获取的政治哲学和工人阶级政治知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这将影响他关于“历史发生了什么”的看法。对于有考古学思想的历史学家来说,柴尔德在其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领域(那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压根没有把他视为同侪)。对于柴尔德“第一人生”的研究揭示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他的思想,那么提出的问题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他的考古学研究中意味着什么”,而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柴尔德如何把史前史研究作为他政治使命的一部分,这始自他的“第一人生”并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柴尔德写信给他英国的一位学术导师,表示他打算回到那里“以逃离澳大利亚的政治的致命诱惑”。十年后,英国的学术生涯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但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政治持续诱惑着他。的确,政治也牵涉到他的死亡。柴尔德早年受政治吸引,这与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政治行动之间有直接联系。本书关注社会主义政治在柴尔德的生命及其历史理论贡献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也关注社会主义政治内部激进的革命民主(revolutionary democracy)与议会社会民主(Parliamentary social democracy)之间的冲突,因为柴尔德认为“政客主义”(politicalism,他对后者的命名)对社会主义有致命的伤害。
 ▴1955年,柴尔德在汉普斯特德的伊索孔公寓建成二十一周年庆典上(拍摄者未知)。
▴1955年,柴尔德在汉普斯特德的伊索孔公寓建成二十一周年庆典上(拍摄者未知)。
但就柴尔德的政治而言,我们这群校园激进分子仅有最模糊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我们之中有谁听说过柴尔德的第一本书《劳工如何执政:澳大利亚工人代表制研究》(How Labour Governs:A Study of Workers’ Representation in Australia,1923)?这本书已经绝版,而且在澳大利亚的历史课程中鲜被提及,因为在战后那个热火朝天的繁荣时期,我们所了解的澳大利亚只不过是大英帝国历史的一个外围话题。……然而,变化终将到来,几年后,人文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彻底的转向,1960年,《劳工历史》(Labour History)杂志第一期问世;1964年,《劳工如何执政》第二版以平装书的形式发行。与此同时,冷战压力下的舆论和从众效应,又使我们对自己的劳工史和曾经激进的历史一无所知。
在1957年(4 月 23 日)的一次采访中柴尔德曾提及,他在1920年代担任工党州长约翰·斯托里(John Storey)的私人秘书。斯托里是谁?我们粗浅的劳工史知识中并没有这个名字。令人费解的是,右翼杂志《公报》(The Bulletin)报道说柴尔德曾为州长威廉·霍尔曼(William Holman)工作,这似乎不太对劲,因为霍尔曼是工党的叛徒,因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兵而被工党开除。此外,我还发现这个讹传有另一个奇妙的出处,即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ASIO)1957年汇编的柴尔德档案。……六个月后(1957 年 10 月 21 日),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在悉尼以西的蓝山(Blue Mountains)一座观景台下1000英尺(约合305米)深的地方,发现了柴尔德的尸体。此前一天的清晨,一辆出租车载着柴尔德从他在卡通巴(Katoomba)常住的卡灵顿酒店(Carrington Hotel)出发,来到格罗斯河谷(Grose Valley)西边的戈维特飞岩(Govett’s Leap)。出租车司机一直等他,到中午去寻找他时,只在巴罗观景台(Barrow Lookout)的栏杆外发现了他的帽子、指南针和眼镜。司机呼叫无果,于是开车到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报警。警长莫里(Morey)与司机一起返回戈维特飞岩,并走下山谷寻找,但不得不在黄昏时暂停搜索。第二天,柴尔德的尸体在新娘面纱瀑布(Bridal Veil Falls)附近的岩石边缘被发现。这则新闻出现在悉尼《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头版:“17个人花了5个小时把尸体运到谷底,然后踩着峭壁上的6000级台阶才把尸体运到戈维特飞岩顶端”。

布莱克希思的戈维特飞岩与格罗斯河谷。瀑布左侧的高处即巴罗观景台,柴尔德的尸体就发现于巴罗观景台下的谷底。(图片来源:Museum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Sydney, Tyrell Collection, 85/1284–1589;Kerry and Company, Sydney, c. 1884–1917)
……讣告在各地正式发布,但内容并不尽如左派所愿。在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上,拉贾尼·帕姆·达特(Rajani Palme Dutt)抗议说,柴尔德的讣告没有提及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达特有充分的理由把马克思主义与柴尔德联系在一起。1917年,他在牛津大学与柴尔德是室友,“在共用起居室狭小逼仄的空间内,我们探讨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深夜”。达特写道,柴尔德之所以“走在我们同时代考古学家的最前沿”,正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考古学本质上一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马克思的方法,从工具和物质记录中构建文明史”。达特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但他并没有宣称柴尔德是党员,只是坚持柴尔德“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心脏和灵魂”。达特还在讣告中发现另一处漏洞:对柴尔德第一本著作《劳工如何执政》(1923)一书的忽略,“这本书对改良主义工党政府的局限性进行了极为发人深省的分析”。
在澳大利亚,日常新闻没有发布柴尔德的讣告,只有左派在纪念他,这恰好暴露了冷战意识形态对澳大利亚史学界的影响。自20世纪初以来,劳工出版和工人教育运动滋养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写作传统——反帝、激进并关注阶级。这一传统造就了一段重要的学术历史,赫伯特·维尔(伯特)·伊瓦特(Herbert Vere [Bert] Evatt )、劳埃德·罗斯(Lloyd Ross)和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学术史上有所开拓,成为戈登·柴尔德《劳工如何执政》这部开创性作品杰出的继任者。1940到1950年代,这种激进的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在高校历史学界得到了认可,罗宾·戈兰(Robin Gollan)、鲍勃·沃尔什(Bob Walshe)和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发表的作品可为明证。……那些受到攻击的学者觉察到彼时政治形势,其中两人还不失时机地在柴尔德的讣告中强化了自己备受攻击的境遇。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因其经济史研究中的反帝观点而饱受保守派历史学家批判,他在左翼文学杂志《陆地之上》(Overland)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现在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正如我在去年九月为表彰柴尔德所做的一个小型演讲中提到的,伊瓦特博士和我很自豪地发现,那些劳工(labour)运动的诋毁者及相关历史学者向大学的考官提交他们的劳工(labor [sic])学硕士和博士论文时,把我们称为柴尔德的同伙。
菲茨帕特里克写过一本劳工运动简史,同时也是《理性主义者》(The Rationalist)的长期撰稿人,他提醒读者注意柴尔德的“理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他先称赞了柴尔德致力于普及人类进化史的努力,随后总结了柴尔德的学术生涯,并在文末讥讽墨尔本的几家日报竟然都没有刊登柴尔德——“澳大利亚最伟大的人之一,对知识做出过重大贡献者”——的讣告。拉塞尔·沃德在海伦·帕尔默(Helen Palmer)的独立社会主义刊物《展望》(Outlook)上发表了一篇讣告:
他的工作将永远引起社会主义者的特别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特定问题的珍贵范例。柴尔德终生都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批判的方法,而从来都不是一套僵化的符咒或神圣的教条。
这篇讣告大体就是这些内容:声称柴尔德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和其他真正的一流学者一样”,发现“没有必要用那些自命不凡的专业大词,遮遮掩掩地把自己的工作隔离在公众视野之外”。沃德撰写这则讣告,背后还有个未曾明言的个人动机,来自他亲身遭受的一次与柴尔德相似的不公正待遇。对于生活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冷战的主要事件之一就是苏联间谍。一系列关于英国和美国公民向苏俄传递情报的惊人消息占据着头版头条。至于ASIO,据其官方历史记载,它接受政府指令,同时也是一个深度的保守组织,将共产党等同于苏联利益。它认为,所有共产党人在心理上都具备成为间谍的潜质,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或曰“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事实上,这些人更危险,因为他们可以隐藏在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许多艺术家和学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作攻击目标。因而,ASIO一直被描述为公民自由的公敌,妨害个体行使权利。……这就是1957年柴尔德回到澳大利亚时的局势。戈登·柴尔德早已习惯于被监视。打从1917年,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MI5)就为他立了档。他本人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那一年他从英国经转美国回澳的申请被拒签。而当他(转过好望角)终于抵达澳大利亚,对他的邮件的审查就立即开始了,MI5已经将他的反战活动告知澳大利亚军事情报部门。他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在信件中直接拿此事开玩笑,还公开抨击审查制度。1921年,他一回到英国,他在MI5的档案立即被重启并保持更新,直到1957年初他离开英国回到澳大利亚。1940年代,他拒绝了去美国讲学的邀请,因为他估计美国国务院会拒绝给他签证。就在登上返回澳大利亚的轮船之前,他还表示过:一想到将在自己的家乡被监视就感到恼火。果不其然,ASIO为他建立了档案。在柴尔德的档案中,有一份备忘录清楚地揭示了ASIO构陷革命者为间谍的冷战思路。然而,媒体报道试图将柴尔德的死亡解释成一起意外——随后的调查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柴尔德从没当过间谍,甚至不是一个有意识地与苏联势力合作的影响特工。我们在后文会看到,他深刻质疑权力对科学和自由的影响。但是正如他的ASIO档案所指出的,在英国,他是几个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成员,而且他的“近期言论与共产党的既定路线大体一致”。在1957年的冷战背景下,这足以令一名ASIO的领导、一位深受政敌和安全部门迫害的工党政治领袖的妻子以及一个嫁给了统治阶层外交官的保守派小说作家都怀疑他与反叛势力有牵扯。然而,他们每个人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柴尔德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投身的事业,是探讨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及革命在历史中的作用。
柴尔德的革命与致命诱惑
在柴尔德的一生中,革命——正如他在1935年时所写,这是一个影响“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真实”现象——曾经出现于三个时刻。在他生命的尽头,这些时刻似乎形成了一个单一现象,但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这些时刻可以理解为一种逻辑秩序。首先,是他所期盼的发生在澳大利亚的革命,无产阶级民主;其次,是他从远处观察到的革命,共产主义;最后,是他在史前史中所发现的变革进程,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进程,他称之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柴尔德刚刚从牛津回到悉尼。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他痛恨的战争仍在继续,他参与了本地日益强烈的抵抗,而俄国远在天边。他几乎没有注意到约翰·里德(John Reed)所谓“震撼世界的十天”所带来的震动。直到次年加入悉尼激进分子出走布里斯班的队伍之后,他才与同情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混在一起。但他并非同情者;他说,澳大利亚人不会容忍托洛茨基的工人阶级专政。他在布里斯班所关注的重点,是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民主传统,即“提交给人民的问题也必须由人民来决定”。他认为这一传统能够在既回避行会社会主义蓝图的复杂性,又避免工团主义忽视消费者利益倾向的情况下,产生革命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选出一个“真正的”工党政府,在“新工会主义”的压力之下,致力于国有企业工人的自我管理,这一“新工会主义”的萌芽是他在激进产业工会中发现的。这样的承诺将是澳大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当他在布里斯班给友人写信,署下“你的,为了革命的”落款时,他心中所想并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
他是什么时候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兴趣的呢?《劳工如何执政》中尖刻的语调表明,他对不同的革命政治模式持开放态度。但是,有没有可能想象议会制度之外的无产阶级民主呢?在为斯托里和杜利工作时,他曾亲眼见证议会制度未能代表工人利益。1920年代他在英国生活时,有两个因素使他转而关注俄国的实验。首先,他在无党派共产主义环境中与进步知识分子们混在一起,苏维埃利用英国人对俄国革命和政府的同情经营这一政治文化。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包括达特和波兹盖特,走得更远,加入了当时新成立的共产党。其次,在完成《劳工如何执政》的过程中,他重新评估了自己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工人阶级政权中的经历,更清楚地看到其失败和缺点。其结果是诞生了世界上首次分析议会社会主义的尝试。他写的这本关于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历史的书,揭示了其结党营私和腐败的破坏性影响,以及议员们“向工人灌输”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从而削弱其社会主义目标。他随后又发表文章驳斥澳大利亚劳工所依赖的社会主义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的冥顽不化,劳工运动的领导人无力改善其追随者的工作生活,更不用说执掌一个可以没收资本家并推动澳大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了。他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发展立即产生了效果。他的写作在1920年代越发清晰地投入阶级分析之中,包括意识到革命不仅涉及意识形态战争,还涉及暴力行动。到1931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遭受另一次经济萧条的影响,他才开始谨慎地接受革命共产主义。他说,澳大利亚是实施苏维埃制度的理想国家,但需要一个“超级列宁”(super-Lenin)来使之实现。柴尔德治学严谨,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采用的煽情手段一贯持嘲讽态度,这些都令他不会对俄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几次到访那里,但从未支持过其极权主义政府体系;事实上,他私下称斯大林主义为独裁统治。在他看来,苏联的革命性在于,这是一次运用科学理解并改变社会的实验。他认为这可能是历史上一个新的共产主义阶段的先驱,由无产阶级和理性价值观主导,但他预计创造这一阶段的过程需要持续若干世纪。同时,发展唯物史观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尤为欣赏苏联博物馆的布展工作,因为他们的展览能够以实物展示唯物史观。他曾推广苏联考古学,直到他发现那是误解的(“马尔主义”[Marrism]),而且是极其草率的——也就是说,不科学的。他允许自己通过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和前线组织而与之牵扯,但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事实上,他对之持批评态度,有时是在公开场合,但大多是在私下。当我们把柴尔德置于左翼命运变化的故事中,分析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思考时,他与共产主义扑朔迷离的关系史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但是还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理解。革命共产主义是柴尔德的世俗信仰,共产党是他的教会,苏联是他的应许之地。他明白这一点,还对此开过玩笑。考虑到他的英格兰教会成长背景,在信仰上实现这一飞跃并不令人惊讶。考虑到他父亲在圣托马斯期间,在崇拜仪式和性灵观上与悉尼教区的分歧,他把自己当作这一世俗信仰中的异教徒也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此,他在这一世俗信仰中,像在官方宗教中那样,有可能不同意其机构和领导人的行动,并质疑其意识形态是否能有效地让解脱之日更早到来。柴尔德将革命思想和行为重建为世俗信仰的支柱,这样的做法绝非特例。左翼作品中一向充满基督教意象。劳工的“知识之树”——摘自《创世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葛兰西在描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形成时指出,他们在转向左翼之前都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学术训练,尤其容易将自己视为世俗信众。他们需要与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达成伙伴情谊,而这样的情谊只能通过界定他们与革命机构的从属方式后才可寻获。他们可能会在技术层面上尽量疏远这些机构,还大声宣称他们与之不同,但在那一刻,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找到革命运动中的基列(Gileads),即安全的见证之所,他们可以在那里确认与自己信仰的持续联系。
因此,他们为左翼内部刊物撰稿,赶场出席历史性劳工斗争的纪念活动,并在“友好”组织中担任名义上的领导职务,就像柴尔德所做的那样。柴尔德世俗信仰的神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就发现了它,在悉尼时代,视之为阶级和国家的社会学;之后的牛津时代(与达特的讨论中),则以之为结构与断裂之间的辩证哲学。革命一直在他最早两本著作的背景中盘旋。在《劳工如何执政》中,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改变”。在《曙光》中,是青铜时代“食物采集者世界的几个转变阶段”——这是在他将之命名为“史前革命”之前的说法。他已经作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进行思考,结构性的思考。同样的思考也出现在《远古的东方》和《远古东方新探》(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1934)中,后者提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两次大革命”。第一次是他在1935年史前史协会主席就职演讲中命名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第二次被称为“一个经济革命”。之后,他在《人类创造自身》中,使用了如今已经众所周知的术语——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并将之作为章节标题。
所以说,在他发现这两次革命的故事中,不曾出现受到马克思主义启示的时刻。他对社会结构变革的兴趣源于他更早时候参与的革命政治。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他思想的特征,而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使用,要记住,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传统是一种批判哲学,而不是一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编纂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他承认给他的马克思主义“包裹了糖衣”(sugar-coating)——避免使用行话——以便让他的读者更容易接受。关于柴尔德参与革命的讨论引发了最后的思考。在他人生早期的某个时刻,政治有可能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致命诱惑。但如果政治是他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不妨问一问,他的政治是否也受到了学术的致命诱惑。毫无疑问,更为正统的英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他的书时,是这样认为的。由此可见,柴尔德的革命政治经历对于理解他的遗产具有双重意义。既提醒我们注意他对人类文化进化研究的学术贡献,同时也突显了所有激进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将学术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为改变社会结构服务。
- 0000
- 0005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