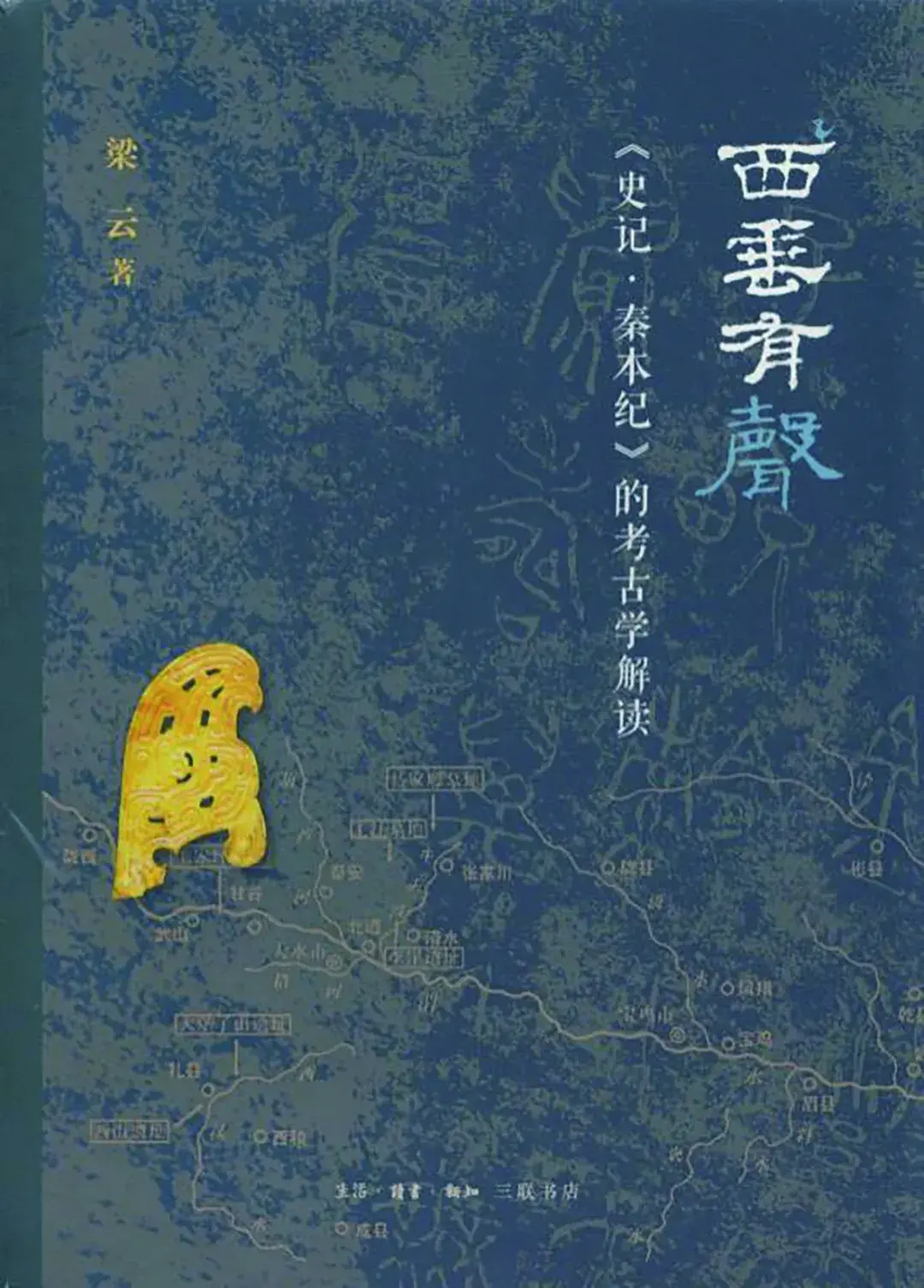孙庆伟:牢记学科使命,重建夏代信
本书是在“历史语境下”探索夏文化的一次尝试,在此可以对一些关键性认识和结论做一总结。
第一章是对夏代社会和若干史事的考察,我们所获的认识有:
(1)大禹治水包含了传说和神话的内容,但其核心是历史事实;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的改进,而是以“德”政为基础构建了治水所需的社会组织机制;大禹因治水成功而获“赐姓”,成为姒姓部族的首领,同时被确定为禅让体系中的法定继承人。
(2)禅让是大禹嗣位和夏王朝建立的制度保障,发生在尧—舜—禹—皋陶(伯益)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君长推选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夷夏联盟下的轮流执政;启攻益而自取君位,禅让制崩溃,世袭制确立;启、益之争是纯粹的权力争夺,却被战国儒家刻意曲解为特殊意义上的“尚贤”,这实际上反映了战国知识阶层企图通过和平方式攫取权力的心声。
 孙庆伟
孙庆伟
(3)“赐姓”和“命氏”相结合是夏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姓是血缘关系,氏是地缘关系”,夏王朝正处于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通过“命氏”方式建立的氏族国家是夏王朝最主要的政治单元,这些氏族国家的首领在血缘上又分属为若干大的部族集团,并通过“赐姓”的方式确立部族首领;部族联盟是夏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夷夏联盟则是其政治基础;在这个联盟中,夏后氏是华夏集团的代表,皋陶伯益所属的少皞氏则是东夷等泛东方集团的代表;有夏一代,东夷剧烈分化,部分夷人华夏化,与夏后氏结成政治同盟,这是理解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
(4)夏后氏是夏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部分,夏代都邑的变迁,实际上反映了该族势力的消长。大体而言,在少康中兴之前,该部族的控制区主要是豫西的颍河上游地区和洛阳盆地,可能涉及晋南的局部地区;少康后期到帝厪时期,不仅巩固了豫西、晋南等传统势力范围,更向东拓展到豫东、豫北和鲁西地区;孔甲之后,夏后氏则退守豫西,广大的东方被以商族为代表的东方集团所占据。

(5)在夏代都邑中,阳翟(夏邑)最为重要。夏都屡迁,但阳翟始终存在,堪称夏代的圣都;由于夏王朝的统治模式是部族联盟,导致夏代都邑居民成分复杂,文化多元,这也是正确认识夏代都邑遗址考古学遗存的重要前提。
(6)《史记·夏本纪》所载夏后世系基本可信,古本《纪年》记载的夏代积年471(472)年说不容轻易否定。依此积年数,则夏代始年至少应在公元前21世纪;研究者对于夏代世系及积年的质疑,必须以全面系统的文献研究为基础,而不能为“疑古”而“疑古”。
依据上述认识,可以将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锁定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故本书第二、三章对河南中西部、豫北、鲁西、皖北和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其要点是:
(1)应以统一的标准对不同遗址的考古学遗存进行文化属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所获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在当前条件下,最容易获得的“统一标准”就是每类遗存的核心器物组合。本书对相关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期正确认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内涵。
(2)核心器物组合的确定应基于典型单位出土器物的统计数据,而应尽量避免“大量”“较多”或“较少”一类的模糊概念;在判断文化属性时,不同文化因素或者不同器类应该占有不同的权重,本书在进行具体研究中,特别突出了炊器在文化属性判断上的决定性意义。
(3)按此标准,本书将上述区域龙山时期遗存划分为:汝颍河上游地区的煤山类型、伊洛地区的王湾类型、豫东鲁西的造律台类型、豫北冀南的后冈类型、豫西西部和晋西南(东段)的三里桥类型。上述类型均以夹砂罐为主要炊器,可归入河南龙山文化系统。而同时期晋西南(西段)是陶寺文化分布区,皖北地区则是文化因素极其复杂的花家寺类型。从文化面貌的相似性来看,上述遗存形成了三层文化圈:第一文化核心区是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第二核心区是造律台类型和后冈类型,第三核心区则是三里桥类型、陶寺文化和花家寺类型。(4)通过对居址和墓葬出土陶器的统计分析,本书将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确定为以下14种,即炊器类的深腹罐、圆腹罐、鼎;食器类的豆、三足盘;酒器类的觚、爵、盉;盛储器类的深腹盆、平底盆、刻槽盆、捏口罐、大口尊以及器盖。
(5)以上述标准来审视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发现两者在炊器和酒水器上缺乏相似性,但在盛储器和食器上则比较接近。据此可以判定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而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6)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砦期的种种争论,归根结底在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模糊性。要彻底解决“新砦期”的问题,必须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以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联系起来考虑,必须要确定一批没有争议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以及“新砦期”的典型单位,然后归纳对比各自的核心器物群,在此基础上方可得出合理的判断。分析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一脉相承,无疑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但新砦二期遗存缺乏不同于其他两种文化、且占主导地位的一组独特的文化因素,因此,新砦二期遗存不宜独立为“新砦二期文化”或“新砦文化”。在“新砦期”地位未定的情况下,测年学者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为确切的考古学年代序列来拟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并以此构建新的夏商年表,无疑是极具风险、极具误导性的。

本书第四章旨在融合前述内容,在夏文化的论证上做到逻辑自洽。本书关于夏文化的最终认识包括:
(1)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应有广狭二义:广义夏文化实际上就是夏王朝文化,而狭义夏文化则是指夏后氏的文化。在当前的夏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忽视和模糊了夏文化的族属主体,混淆了广义和狭义层面的夏文化,由此造成了概念和认识上的混乱。
(2)从时间、空间和文化面貌三方面综合分析,前述第一核心区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晚期阶段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夏文化——即以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核心区内的诸考古学遗存的晚期阶段则可归入广义夏文化范畴。
(3)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这一特定时间范畴内的文化,但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准确区分夏王朝建立之前和覆亡之后的物质文化,因此需要将夏王朝的始终转换为某些可视的考古学现象。因此,能够充当这种“转换器”的是那些在夏王朝建立和灭亡等关键时间节点附近,能够触发物质遗存发生变化的特殊历史事件。
(4)“禹征三苗”是夏王朝建立前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豫西南、豫南和江汉平原普遍出现的河南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是这一事件在物质文化上的直观反映,这是证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早期夏文化的关键证据。
(5)“禹赐玄圭”是夏王朝建立、夏代礼制确立的标志性事件,而学术界所习称的“牙璋”正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玄圭在中原腹心地区的兴起并大幅扩张,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就是夏王朝的文明输出,因此玄圭的出现是证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进入夏纪年的又一关键证据。
(6)在有文字证据之前,企图以成汤亳都来界定早商文化,从而确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纷争之中,夏商文化的区别只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来获得;偃师商城西亳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瑕疵,严格来讲,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只是确定了夏商分界的年代下限,因此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更不是夏商分界的唯一界标。
(7)器类统计表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是一个连续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其中不存在物质文化上的突变;在此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比较明显的变化分别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以及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但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并不能直接解释为王朝更替的结果。豫西地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所表现出的一脉相承、渐进式演变特征反而促使我们反思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否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最早发现在不同遗址而被分别命名,而非文化面貌实际上的泾渭分明。因此,以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去对应虞夏商周等历史王朝,是需要极其慎重的。
(8)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郑洛地区最大的变化并非物质文化,而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以及大师姑和望京楼城址的改建。在二里岗下层阶段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商人同时兴建两座大型城址并对两座二里头文化城址进行改建,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城市建设异动的最大可能就是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了王朝的更替,换言之,夏商分界应该就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不排除两者略有重叠)这一时间节点上,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由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就深感困扰,并由衷感叹,“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与之言五帝。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不但五帝时代更为渺茫,夏代的信史地位也屡遭冲击。中国考古学本就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奋发向上,追慕太史公之遗风,为建设真实可靠的信史奉献学科的力量。
本节为《鼏宅禹迹》结语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