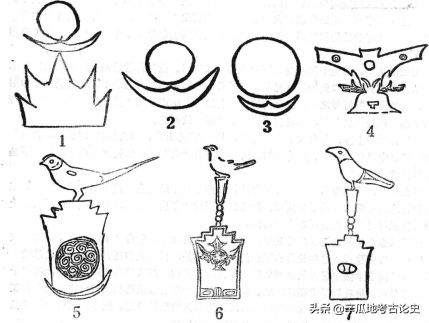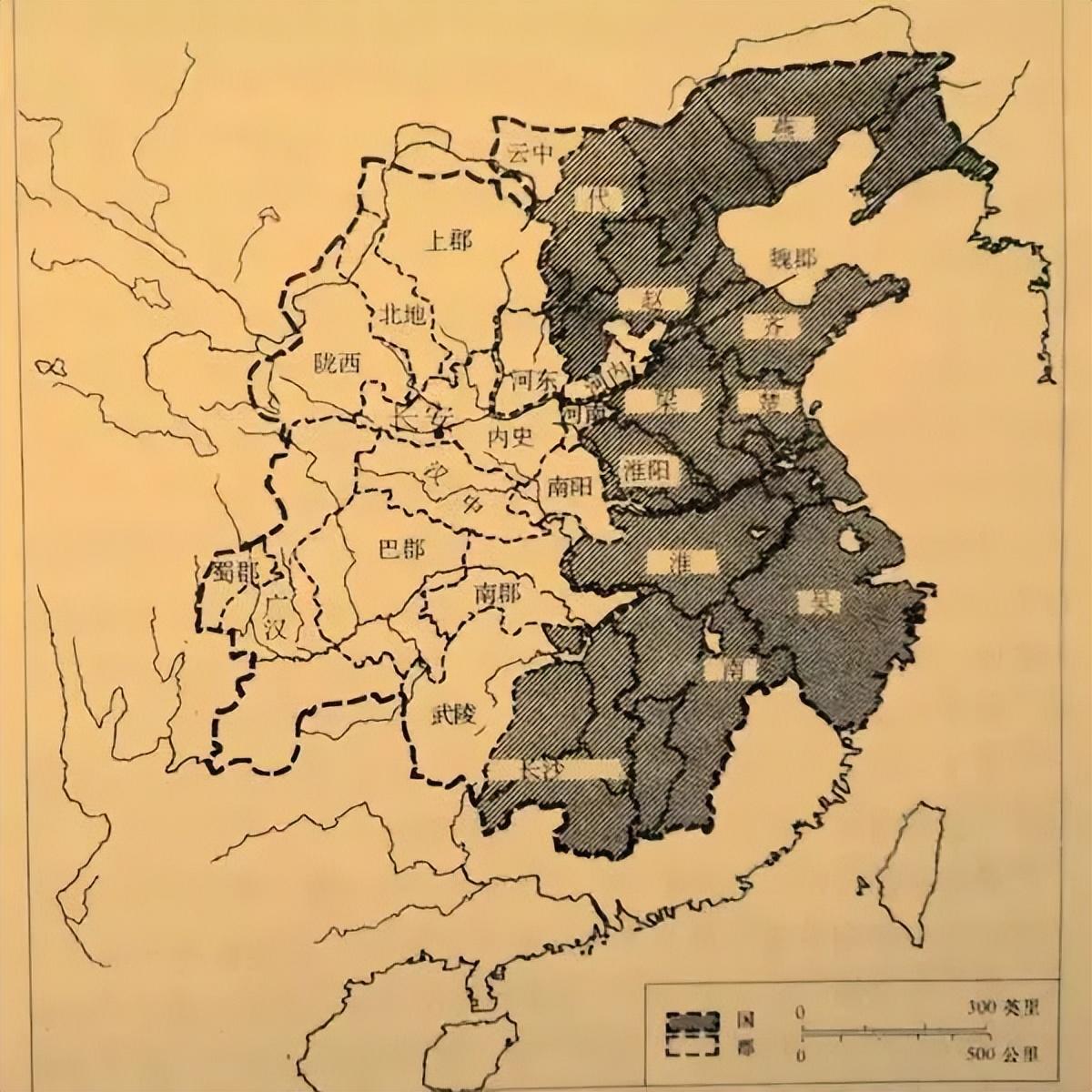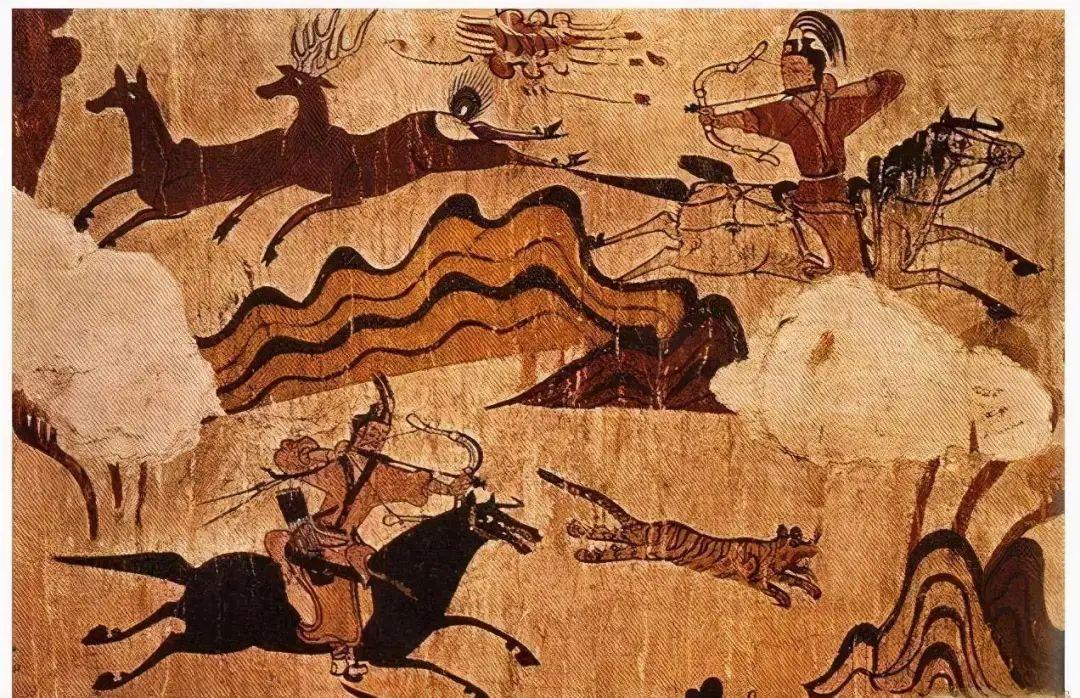张忠培: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
编者按: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做很多事情一无经费,二无待遇。在高等学校中从零开始创办一个全新专业,建立一个学科,是何等艰难。每每面临的,是一个个非常复杂的困难。在这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张忠培先生凭着坚定信念,精心谋划,呕心沥血,一步步闯出来、干出来,不仅创立了吉大考古专业,而且带领吉大考古专业发展成为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特色专业,逐渐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吉大模式。这一过程曲折跌宕,颇具传奇色彩。
《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一文是创始人、奠基者张忠培先生在庆祝吉大考古专业成立20周年之际写就,今年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立50周年,重刊此文,以志纪念,愿年轻的朋友们在中国考古事业上再创辉煌。
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身上
张忠培
一
吉林大学在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是始于1972年,1973年开始招生。从招收第一届考古专业学生至今,已入冠礼之年了。站在这成年之期,回顾以往,确有几分喜悦。一是因为已基本实现了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为模式的办学道路的初衷;二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参与办学的同事忠诚于教育事业,实现了团结、奋斗的精神外,重要的是得到了学校及历史系历届负责人及同仁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为考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北、河北、山西、甘肃、青海、辽宁、内蒙古、北京及吉林、黑龙江诸省市的文物、考古机构的鼎助。
设计和动手写这篇文字之时,那些走出学校而又行进在成长之路上的中、青年考古学者的形象,从我回忆的脑海中蹦出,还匆匆不停地在眼前闪现,想起他(她)们,想着以往的路,使我难以抑制对那些曾给予我热情关怀、指导和友谊援助的诸师友的感激之情。
二
要办好考古专业的条件是:
1.要在一个好的政治环境中,有一条正确的教育路线、方针及政策;
2.专业负责人对学科的历史及现状应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能较正确地把握学科未来前进的方向,重要的是认识到进入学科的门路和掌握人才成长的规律;
3.应有一支学科门类齐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并具备相当的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
4.一定的图书、照相及绘图、测量设备和掌握相关技术的人才,以及可以借用的科技力量。
1968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表面现象已有所认识,把被卷入到运动的经历视为“历史的误会”,“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演戏”,成了我做人处事的格言。1969年,悄悄地和历史、考古书籍又打交道了,1971年以顾问身份参加了珍宝岛考古,1972-1973年被借在北大修改元君庙及泉护村发掘报告。在北大时,收到吉林大学任命我为新成立的考古教研室副主任的任命书。
吉大据上面指示要办考古专业,我早有风闻,认为这是奉献自己才能的极好机遇,因而感到十分兴奋,在接到任命书前,对中国考古学的以往历史,以及北大办考古专业的曲折历程,包括哪些班出人才和人才成长的主、客观条件,都进行了认真的回顾,而且,得出了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认识。办考古专业方案的思考已经成熟。同时,在那难以表达个人思想且教师被“管、改”的时期,要办好考古专业是相当困难的。这样,我抓住了文革中稍松弛的政治环境,给学校回了一信: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客观世界的,而我又是一个顽强表现自己的人,在当前情况下,难以胜任组织上的委托。并将任命书随信退回学校。大概是出于当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吧,最后学校还是要我承担没有主任而以副主任名义办考古专业的这一工作,同时,我也得到了校、系默认我按自己的思想办考古专业的权力。
三
通过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的教学,使学生具有独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在文革中作为修正主义而遭到反复批判的教学方针,被我们重新捡了起来,并认为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必须具备认识遗存的基础知识,掌握层位学与类型学的基本理论,能做田野工作,具有发现、分析和解决遗存、时、空三者关系中所显示的矛盾的初步能力。要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需要配备一定的课程,安排好教学环节与程序,启动学生求知向上的内在潜力,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及自觉精神。最重要的是得到同事的理解。
在疯狂时代经历了疯狂高潮的教师,通过反思对上述教学方针、目标的认识,虽然在理解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别,同时,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及个人经历、地位的不同,在实践中的坚持程度也存在一些区别,但基本方面却达到了共识。这使我们团结起来,朝向一个共同目标走去。对那些在不同阶段共患难的同事,我一直留有甜蜜的回忆并充满感激、敬佩之情。李木庚同志是我国较早研究现代史的一位学者,由于工作需要,文革前一直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一开始,就遭受迫害,后期被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考古专业成立后,他兼任党支部书记。即使是被降职使用,他仍充满热情,一心投入考古教学工作,为搞好考古实习,他长期深入工地,于1974-1977年间,在大安汉书、突泉及科右前旗、江陵纪南城、易县燕下都和东宁团结等地古代遗址及城址上,洒下了汗水,留下了足迹。他一贯以善意度人、待人,言简务实,在师生中最富吸引力,最具威信。他虽已离开人世,却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使我必须在这里写下这几句话。
尽管有这么一些好同志共事,在当时形势下,仍需走着崎岖的、曲折的路,才能前进:打着时髦的旗帜,走自己的路,例如“上、管、改”,则说“上”是第一位了,只有上好了大学,才能作好“管、改”;对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则强调其中的“以学为主”;带学生实习搞考古发掘,除提出在实践中学的口号外,还因时因地打出“反修”“评法批儒”及配合“农业学大寨”等旗帜。文革中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校的环境不如我们能把握的实习工地,为了实现“以学为主”,我们干脆在工地搞起了课堂教学。1976年,当我们把学生从工地带回学校后,学校正开展批“三株大毒草”,批“右倾翻案风”,撤销教研室,组织连队下乡,批“三项指示为纲”。我对此极为反感,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刚从社会实践中回来,又要下乡去,到底搞不搞“以学为主”!结果是我被调离学校,去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去了。不过,我从“批三项指示为纲”之中,进一步悟出“文革”这只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三株大毒草”批不倒,她将重新回到中国的大地!
四
确定了专业发展方向及与其相配套的课程之后,建设什么样学科和质量的教师队伍,就成了首要而关键的问题。考古专业的骨干课程至少七门,当时能上这类课程的教师只有两位,缺乏考古专业教师,是摆在初建专业门口的第一道难题。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的是,当时的形势,迫使我们只能一边招生,一边建设教师队伍。
尽管专业教师奇缺,但决不滥竽充数。建设教师队伍,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转专业派到北大进修;二是调入学过考古学的人员。后者除个别人员外,亦无上专业课的经验,也得在我的指导下,在校进修备课。规划教师队伍,可说用心良苦。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个萝卜长得不壮实,我就心急如焚,大有功亏一篑之感!
1973年,李如森和魏存成两同志从历史专业转过来,分别派到北京大学跟俞伟超和宿白两先生学习,随后,当时在古文字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姚孝遂同志,为了担任商周考古课,走进了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工地。同时,林法被调回学校了,接着又先后调进了匡瑜、史学谦及段一平三位同志。这才基本上配齐了中国考古学及东北考古学诸课程的教师。此后,我们才能较主动地从专业发展方向,或从办有自身特色的考古专业的角度来建设教师队伍。
从1976年开始,才走上了选择毕业生留校培养教师的道路。从此,教师队伍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到1982年,这些留校的学生,基本上是通过送出去进修培养成教师的。张文军、许伟分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学习;林志纯教授帮助我指导杨建华;陈全家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学习;徐光辉、滕铭予和朱泓分别派进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进修。滕铭予在北大进修期间,还在北京钢铁学院学习冶金史。
派出去进修的教师,分别得到宿白、邹衡、徐苹芳、俞伟超、吕遵谔、张森水和潘其风这样一些著名学者的指教,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1982年春季起,考古专业才招收考古学硕士生,自1984年春季始,才开始从硕士生中选择教师。
如果满一点估计,至80年代中期,考古专业才形成一支学科配置较为合适、有一定质量和特色的教师队伍。在此,首先应感谢那些为培养教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导师。
选择、培养教师的工作,相当细致,甚至是十分艰难的。
为了能留下许伟,李木庚同志去山西联系,碰上唐山大地震阻隔在北京,晚上露宿街头。
为了培养陈雍搞古文字,在他上大学期间,姚孝遂同志就带他研究汉简。
在杨建华、朱泓上大学时,发现他们或有较好的英语,或在卫生学校教过解剖学,就注意创造条件,让他们日后各自走上西亚考古和人类学之路。
1975年,我到江陵联系考古实习,走到江陵博物馆门前,正巧见到在北大进修的李如森同志在喊“集合、立正”,心里好着急,到纪南城见到俞伟超同志,立即火起来,说送李如森到北大,是跟你学习的,不是为你集合学生的。为了这事,我和这位如同兄弟般的同窗、师兄吵了起来,红了脸。
为了留好教师,我们堵塞了一切后门,包括来自工、军宣传队以及个别教师的一时感情关系。选择、培养和晋级,是把好教师质量的几道关卡,教师的质量,又是专业的命根子,我们不能不慎之又慎。
五
田野考古,是揭示、整理、研读埋藏在地下的一本书,是考古学的源泉。人们正是通过一次次田野考古工作,才可能从考古学中日益增进对人类以往历史的认识。正确地深入揭示、整理、研读这本书的学者,需具备较高的田野工作技能、较深的层位学及类型学的修养,和广博的知识。至今,田野考古仍是主导考古学滚动发展的重要科研领域。
田野考古实习,是学生在教师带领和指导下,揭示、整理、研读被埋藏在地下的书,并以此为教材,使学生学会田野工作的基本技能,掌握层位学和类型学要领,深入理解和扩充课堂所学的有关实习对象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
从一开始办考古专业,就认为田野考古实习,是培养学生的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同时,又是造就优秀青年教师必经的科研之路,所以认真地抓了这件事。
1974年上半年,和吉林省博物馆合作,组织73级学生在大安汉书遗址实习。确认了被命名为汉书文化的两期遗存,及以渔场墓地为代表的、晚于汉书文化的遗存。
1975年上半年,组织73级学生参加哲盟普查,负责突泉及科右前旗两县工作。两地均为考古学的处女地,故有一系列的新发现。
1975年下半年,因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及湖北省为建设“大寨县”的需要,组织73级学生到楚纪南城进行发掘,在北京大学等校上半年工作的基础上,新识别出纪南城30号建筑遗址上的废弃时的堆积,将这建筑遗址整个地揭示出来,搞清了它的结构及层位关系。并在凤凰山发掘了167号汉墓,在填土中发现了该墓的成捆的遣册,经仔细清理,搞清了遣册的顺序,证实汉初还使用奴隶生产,和在当时财产观念中,农业生产奴隶的价值似乎高于从事杂务的奴隶。
1976年上半年,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委托,配合农业生产,组织75级学生和部分73级学生,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共同发掘了燕下都,搞清了此地自商至汉代的堆积和燕下都本身的文化分期。
1977年上半年,和黑龙江省博物馆合作,在东宁团结遗址发掘,确认了团结文化及其分期,确定其族属为沃沮,并对同地发现的靺鞨遗存进行了考古学文化分期,从而首次获得了靺鞨遗存分期的认识。
在这些实习工作中,都以学生为中心,对他们认真地进行了田野工作技能和层位学的训练,并使他们初步掌握了类型学。之所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除了当时形势外,主要是想努力扩大初建考古专业的影响。
回想起来,获得这些成绩,真是来之不易!1975年,长春发出地震警报,和当时大多数人们一样,我妻子马淑琴烙了一口袋烧饼,做了随时跑的准备。那时,李木庚、姚孝遂、李如森、魏存成、史学谦和我,都在纪南城考古工地。这些人都有个家在长春,尽管地震警报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工地,大伙儿却一心一意工作在工地,战斗在工地,似乎都没感到长春还有个家!
在“不断革命论”的指导下,“文革”这一大运动期间,运动一个接一个,与这些运动及教学进程相关的“路线分析”接踵而来,都是以处于第一线的我为对象。那时,我从来没有感到像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被审查时所遇到的那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时,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教师与教师之间,尽管有时,甚至经常存在不少分歧,争论有时也是相当尖锐的,我却从来没有被整的感觉。这除了大家都是以教学工作为出发点外,最重要却是李木庚同志的人格和能力,使工作上的是非之论没变成个人得失之争。
我持“无私无畏”“坚持真理”“让历史作证”的态度,和同志们一起,以战斗的精神,历尽艰险,走着曲折、迂回之路,到1976年,看着首届毕业生走出校门的时候,喜悦夹着悲壮的心情中暗暗地流淌着对学生的恋情。
六
1978年春季,面临着两类学生。一是被保送入校的工农兵学生,二是恢复大学考试招生进来的学生。当时的环境,使前者产生了将要遭到遗弃之感。形势使我们有可能,同时又要求我们对考古专业今后的道路,以及教学、科研、学习进行新的思考,作出新的决策。
我们这些教师,尽管遭到历次运动的践踏,却始终保持着育才的使命感,和一颗爱学生之心。因此,我们及时地对两类学生作出应一视同仁的决策。为了保证工农兵学生的质量,一是补课,加强了一些课堂教学;二是安排他们撰写毕业论文。
通过教研室一系列会议的讨论,对考古专业今后的方向与道路这一复杂的问题,才形成了主流认识,并陆续落实了一些措施,使考古专业踏进上新的历程:
1.对课程设置及安排作了必要的调整。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重点是增设田野考古课程及毕业论文,和包括考古科技在内的一些专题课程。在当时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相继请了一些知名学者来校讲学;
2.规划好学生需参加的两次实习。头一次以学田野考古技能和层位学为主,第二次主要是学类型学。自77级以后的好几届学生,在野外的时间,均为三学期。他们的最后一学期,或利用工地资料进行专题整理及研究,或搞专题考古调查、试掘,并对所得资料进行研究,产生毕业论文。
3.为保证实习的质量,和实现专业的基本的长远的科研方向,需建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实习基地。在苏秉琦教授倡议下,认为张家口地区位于长城地带,具备陆地口岸的地理位置特点,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以此为实习基地,拟从搞清其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入手,探索该地同其周邻地区的古代文化关系。随后,因张家口工作提出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仍需在其西、南地区作一些探索,以解决它和黄河流域腹地之间的古代文化关系,加之,迫于安排学生实习的需要,故于1980年秋,又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新增晋中地区作为科研与实习的基地。
4.通过张家口及晋中地区考古教学实践,形成以层位学及类型学为核心、能结合实习进程讲授的、较成体系的考古学方法论课程,以及田野考古规程和考核的标准、方法。
落实旨在强化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和成批地搞出系列性的科研成果的措施,单靠学校自身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实在是难以实现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战线拉得过长,以致到处存在隐藏着危机的薄弱环节。
1979-1980年整整两年,在蔚县的筛子绫罗、庄窠及三关,共计发掘了约5000平方米,但由于这里遗存堆积的特点,基本上是广种薄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工作处在进退维谷之中。继续在张家口拼搏是否值得的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1981年春,我只得领着张文军,到张家口督战,组织77级部分同学进入张家口,在蔚县对壶流河流域的18个公社进行卷地毯式的调查,发现遗址47处,相当已知遗址8倍。当时选择琵琶嘴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又一次发掘了三关及庄窠遗址,开创了张家口考古的新局面,加上以往两年的工作,搞清了西周以前古代遗存的编年、序列和文化谱系。
当时考古实习的指导力量十分薄弱,调査工作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那时,农民连高粱面都吃不饱,下乡吃不到派饭,即使派到了饭,也无法吃,参加调查的学生,只好带着些挂面、油盐及咸菜,饥一顿、饱一顿地工作着。为指导学生,张文军一天要跑好几个地点。他靠着实习及科研工作的进展带来的欢欣支撑着日渐削弱的身体,努力向前。几年工作下来,张文军累出了好几种病,孔哲生也瘦弱下来。
晋中考古的日常工作,基本上由许伟负责。
1982年和1983年春季,由卜工、陈冰白带领学生在汾河中游及吕梁山地进行的调查及试掘,尤其是在吕梁山地,也是在类似张家口的艰苦条件下,发扬了张家口考古精神,按照张家口所创造的模式进行工作。
由于紧张的工作,许伟病倒了。1981年的夏天,我只好动员李伊萍去工地。她毫不迟疑地跟着我走进工地,挑起了后勤、库房管理及会计重担。我和老同学王克林指导30多名学生实习。我俩都是近50的年龄,既要上工地,又要在室内指导学生整理及编写报告,深感疲劳和孤单。后期,先是孔哲生带领张文军、陈雍,不久,患病初愈的许伟和王丹都来到了工地。看到他们,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在考古工地所结成的友谊,是何等的珍贵!
这些年来,除秉琦师指点外,我从黄景略那里得到的帮助最大。正是在黄景略全力参与、筹划、支持下,依靠这种友谊、团结和艰苦奋战,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支持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下,才看到一批批合格的学生走出了工地,一批年青教师成长起来,同时,迎来了成批的系列性科研成果,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七
50年代,接受了苏联的大学模式,综合大学成了国家科学的标志,技术学科,尤其是应用学科的教育被忽视了。
中等教育没有得到改造,仍然是旧中国那一套。职业教育也没有被重视起来。
这种教育体制自然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
面对着那些考不上大学又缺乏职业训练的在业或待业的高中生,只好以大专文凭吸引他们接受职业教育。大专和中专、大专和大学划不清界限,大专在冲击着大学。国家增拨的教育经费,赶不上物价增涨的比例,学校只好靠搞成人教育以增加收入,填补教育经费的缺口,先是大专,后是大学,现在又打开了学位研究生的大门,基本上是单位花钱,个人得学位,大搞权—钱—文凭的转化,质量在降低!
在市场经济中,基础学科难以直接显示价值,功能被忽视,基础学科教育遭到社会的冷遇。基础学科的科研及教学发展不上去,将使技术及应用学科的科研及教学失去后劲。而且,人文基础学科的科研及教学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对现在与未来作出重大决策的能力。
分配不公,冲击着教育。
教育要改革。我希望改革中少出偏差。现在,我们应把能做或创造条件可作的事做好。
我们已坐在一条船上,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将这条船划到彼岸。因此,只有团结,只有坚守岗位,才能为未来的发展站稳脚跟。未来总是有希望的。
学生的质量,是专业的生命线。专业仍应以学生为中心,全心全意地搞好教学。
不提高科研,教学得不到滚动式的发展。要教好课,教师在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教学的前题下,必须努力提高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
对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看到它的弱点、缺点,又要看到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进入80年代以来,对什么是考古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什么功能,层位学与类型学为何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吸引有关学科参与考古学遗存的研究,和扩充、改善考古学的测试手段等问题,我们都提出了一些意见,并做了不少工作。和以前相比,是前进了。现在看来,考古学仍需向前走。但前进的方向,不是艺术考古学,不是新考古学,更不是超新考古学。前进的方式,不能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搬来,也不能照抄国外现在的东西。科学发展的形式,是通过量变的积累进入质变。因此,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办法,是从现状出发,吸收国外优秀的东西,沿着已形成的轨迹,继续向前。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往的科研成果不少,但品种单调。从大多数教师来看,主要善于作谱系文章。我们的步子,基本上未赶上“古文化-古城-古国”、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研究。我们已开始研究外国考古,结合并使用邻国有关资料,开展了边疆考古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在国内虽是凤毛麟角,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因为尚在萌芽之中,尚未能引起同行的广泛注意。
考古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揭示、分析和解释遗存、时、空关系所存在的矛盾,搞清楚一定历史时期中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解决这些关系所使用的技能、方式、手段、思想及法则,起到温故知新、启迪新智的作用。考古学研究凭藉的资料,是人们活动和与其相关的自然遗存,以及这类遗存展示的现象,且只是留存下来的一部分。它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成员。我们只能在这自然局限范围内,发挥它的功能。然而,这局限内的空间仍然是广阔的,需要和可能做到的事是很多很多的。
加之,现在我们不仅面临国内的竞争,同时,也面临国际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仅靠保持优势已不行了,重要的是在发挥优势的同时,努力创造条件,提高自身能力,制订出规划,认真地做事。
我们已走过了冠礼之年,而立之年就在前面。有一首歌唱道:“托出一个太阳,托出一个明天”,我把这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的身上。
(该文写于1993年3月2日,曾刊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来源 | “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复审 | 郭晓蓉
监制 | 李 让
- 0001
- 0007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