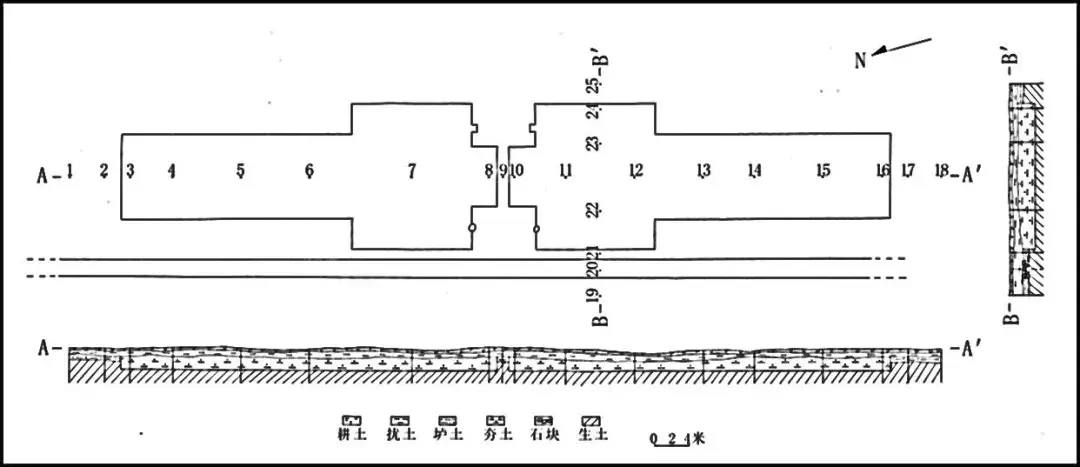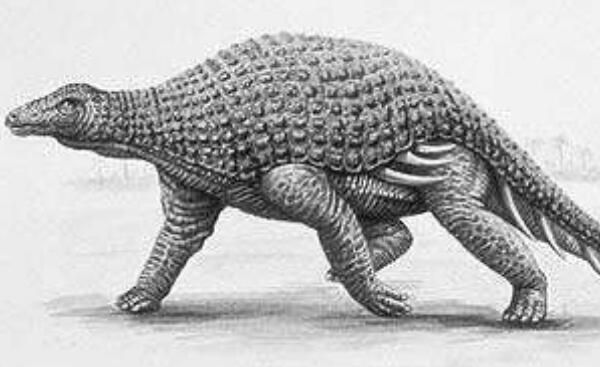查洪德: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总序

《全辽金元笔记》是辽金元笔记文献之汇集整理,汇编、点校全部现存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所谓笔记,是指那些没有严格体例、信笔记录摘录而成的著述,是古代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含有大量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研究者重视。辽金元三代笔记,特别是其中的元代笔记,又因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而具有独特价值。
对古代笔记文献的整理,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唐宋笔记,除《全唐五代笔记》《全宋笔记》已整理出版外,单行本的点校,数量也已可观。与此形成明显差异的,是辽金元笔记文献的整理情况很不理想。兹将有关情况述论于后。
一、辽金元笔记的存世与整理情况
辽金两代笔记,几乎不为人关注,元代笔记情况略好些,但被关注度也不高。这里举人们熟知的两大笔记文献丛书为例,对比宋元明三代笔记收录情况,可以说明问题。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其中《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收宋代笔记八十六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收明代笔记三十一种、元代笔记三种,按目前掌握的宋、元、明三代笔记存世情况(《全宋笔记》收宋代笔记四百七十七种,《全明笔记》课题组统计的明代笔记总数为一千零四十五种,我们统计的元代笔记总数为二百七十二种),分别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宋)、百分之三(明)、百分之一点一(元)。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收宋代笔记六十三种,明代笔记十六种,金元两代笔记五种。为什么人们的关注度如此不平衡呢?是辽金元笔记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是。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就元代笔记说,最早收录元代笔记的,是元人别集与元人所编元代总集,比如王恽的《乌台笔补》《承华事略》《玉堂嘉话》《中堂事记》,收在其别集《秋涧集》中,这类情况在元代比较多见。还有一些笔记被作为文章,收录在元代总集如《元文类》中,如杨奂的《汴故宫记》。最早大量收录元代笔记的是元末陶宗仪的《说郛》,收录元代笔记数十种,但多是摘录。明清两代,大部分元代笔记保存在丛书丛刻中,如《津逮秘书》《宝颜堂秘笈》《稗海》《古今说海》《知不足斋丛书》《读画斋丛书》以及《历代诗话》等。在古代书目中,《四库全书总目》已有“笔记”之名,该书杂家类杂说之属后有按语:“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尽管在《四库全书》中,笔记被收在子部的小说家类、杂家类、艺术类,史部的载记类、杂史类、地理类、史钞类,以及集部的诗文评类中,但杂家类还是最为集中,特别是其中的杂说之属,这部分收宋代笔记最多,达四十九种;元代笔记也相当多,收十二种,与明代笔记数量相当。《四库全书》各部收元代笔记四十多种。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这部分文献得以面世,比较重要的如《困学斋杂录》《隐居通议》《湛渊静语》《敬斋古今黈》《日闻录》《勤有堂随录》《玉堂嘉话》《庶斋老学丛谈》《研北杂志》《北轩笔记》《闲居录》《雪履斋笔记》等。后出的四库系列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了一些元代笔记,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珍贵的版本。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石印的《笔记小说大观》,收元代笔记如元好问《续夷坚志》、刘祁《归潜志》、陆友仁《研北杂志》、陈世隆《北轩笔记》、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杨瑀《山居新话》、郭畀《客杭日记》、陶宗仪《古刻丛钞》、郑元祐《遂昌杂录》,还收录了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其中多数成为二十世纪整理比较多、流传比较广的元代笔记。迄今为止,收录元代笔记数量最多的,还是民国时的《丛书集成初编》,收录元代笔记六十九种。加上其后《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一九九四年出版)收录十二种。这基本上是目前一般研究所能利用的元代笔记文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出版了多种大型笔记小说、野史文献丛书。首先是台北新兴书局一九七八年影印出版《笔记小说大观》,收元代笔记五十一种,但由于对笔记概念理解的不同,在我们看来,大约四分之一不属笔记,而实际属于我们理解之元代笔记者不到四十种。巴蜀书社一九九三年影印出版《中国野史集成》,收元代笔记十二种(二〇〇〇年出版的《中国野史集成续编》未见收元代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影印出版《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收元代笔记二十九种。黄山书社《元代史料丛刊》史书类与子书类收了若干种元人笔记,但为其收书宗旨所限,收元代笔记不是太多,反倒收后代记元代事的笔记文献不少。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出版《金元日记丛编》,收元代笔记十多部。这些可为元代笔记整理提供寻找版本的便利。另外,泰山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收元代笔记四十六种。类似的丛书还有一些,但既非影印,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属一般读物性质。
整理元代笔记较早的,可上溯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王国维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李志常原著)、《圣武亲征录校注》(佚名原著),以及《古行记校录》所收《北使记》(刘祁原著)、《西使记》(刘郁原著)。类似文献整理,有后来向达校注的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出版)。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以来陆续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其中《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所收元代笔记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杨瑀《山居新语》和王恽《玉堂嘉话》,以及署为金人的刘祁《归潜志》,署为明人的叶子奇《草木子》。《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收录署为宋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随隐漫录》《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澄怀录》七种,都成书于元代,在我们看来,也属元代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所收元代笔记有杨瑀《山居新语》、姚桐寿《乐郊私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蒋子正《山房随笔》、孔齐《至正直记》。该社有《宋元笔记丛刊》,所收基本上是宋代笔记,元代笔记只收《至正直记》一种。中华书局分别于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标点整理出版了《历代诗话》和《历代诗话续编》,收入了一些可归入笔记的元人著作。《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收入元人著述七种,也属笔记类。北京师范大学《元代古籍集成》(第二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出版)整理本有元代艺术类笔记十种。还有一些笔记被作为著名文言小说整理出版,如《郁离子》等,一些被作为地方文献由地方出版社整理出版,这类有相当数量。一些专业性的笔记被作为专业文献整理出版,如《真腊风土记》等。所有这些,目前掌握有比较好的整理本的,有四五十种。以上所述,是元代笔记整理的基本状况。
大致说,目前研究者一般可作为文献使用的辽金元笔记,总数有七十多种。而我们所做文献调查的结果是,辽金元三代存世笔记至少有二百九十种九百零七卷,其中辽金两代笔记十八种五十八卷,元代笔记二百七十二种八百四十九卷。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掌握的辽金元笔记文献数量,差不多是一般研究者可利用数的四倍。辽金元笔记这一巨大的资料库,应该发掘整理出来,提供给文史研究者。相信本丛编的出版,会助推当前的辽金元文史研究。
二、辽金元笔记价值例说
辽金元笔记整理的欠缺,使得相关的研究难以得出客观全面的认识。目前关于笔记的研究论著有不少,但研究辽金元笔记的却少见。在通代的笔记小说史或笔记文史论著中,辽金元笔记不占什么位置。在这类著作中,很难找到有关辽金笔记的内容,元代笔记也被忽视。著者首先将元代前期一批记载宋代史事的笔记归宋,然后对元代笔记成就,作出有限肯定甚至委婉否定的评价。其肯定部分,也显示出对元代笔记缺乏具体全面的了解。如认为元代笔记比较多的是琐记随笔,或轶事小说,这显然不符合元代笔记的实际。有学者肯定元代学术性笔记的价值,这很对,但举作例证的,是《隐居通议》与《南村辍耕录》,却不举李治的《敬斋古今黈》和方回的《续古今考》(尽管刘叶秋先生在其《历代笔记概述》中早就说过:“《敬斋古今黈》的内容,并不逊于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今按,《困学纪闻》也成书于元代,在我们看来,它是元代笔记)。目前唯一研究元明笔记的专著,是姚继荣《元明历史笔记论丛》(民族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出版),该书属历史学的研究,却深受笔记小说之论的影响,认为元代历史笔记“无大的成就”(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又认为“元朝笔记的主体,是杂著性的笔记和志人、记事的笔记小说。这是历经宋代之后笔记发展的必然”(第十一页),并引萧相恺《宋元小说史》之论,支持其观点。陈尚君《宋元笔记述要》(中华书局二〇一九年出版)收有十五种元代笔记的叙录。以辽金元笔记为研究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单篇学术论文,可以说没有。有一篇硕士论文《元代笔记中的小说史料研究》(赵立艳,山东大学二〇一〇年),从题目就可看出不是研究元代笔记,而是以元代笔记的内容为史料研究小说。作者认为:“除去独放异彩的杂剧和散曲外,元代的其他文学样式似乎处于衰惫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元代笔记的创作而言,数量和质量虽不及唐宋,但依然有可观之处,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对全部元代笔记有所了解,这样的论断应该会修正。要对辽金元笔记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只有建立在对辽金元笔记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而辽金元笔记文献的全面整理,又是其前提。在很长的时期中,辽金元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辽金元笔记的成就也同样被低估。多数人并不了解辽金元笔记的成就,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元代笔记(辽金不在视野中)成就无法与唐宋相比。《全辽金元笔记》的整理出版,将这些文献呈现在研究者面前,自然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对辽金元笔记成就作出客观的评价。
金作为与南宋并立的政权,金代的笔记有其特点与成就。元代笔记承宋之后继续发展,凡宋代笔记有的内容与种类,诸如读书摘记、生活杂录、文人趣事、艺术品鉴、朝政轶事、林下闲谈、诗话文话等,元代笔记无所不有。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航运、灾异、出使、世风、士风、掌故、风土、物产、演艺等,举凡士人生活涉及的领域,都在笔记中有所反映。元代笔记还有诸多不同于宋代笔记之处,如宋代笔记多文人闲暇随兴之作,明人有言:“(宋笔记)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故一语一笑,想见前辈风流。”(桃源居士《五朝小说大观·宋人小说序》)在研究者看来,宋后笔记大致也是如此。其实不然。元代笔记多为文人着意撰著,早期北方刘祁的《归潜志》,南方刘壎的《隐居通议》,后期南方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莫不如此,学术性笔记如《续古今考》等,更是着力撰著之作。就比较发达的史事记录类(刘叶秋名之为“历史琐闻类”)来说,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烈的存史意识,二是直书无隐。存史意识,如刘祁《归潜志序》所言:“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元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存史意识,当然也体现在笔记中。直书无隐,典型的如孔齐《至正直记》,书名既已可见。孔子有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齐却不如此,既不为父隐,也不为君隐。这在古人是不能接受的,四库馆臣批评说:“中一条记元文宗皇后事,已伤国体。至其称‘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晩年亦坐此患’,则并播家丑矣。”“播家丑”的是卷一《年老多蓄婢妾》条(内容即上文所引),“伤国体”的是同卷《周王妃》条,说:“文后性淫,帝崩后,亦数堕胎,恶丑贻耻天下。后贬死于西土,宜矣。”尽管如此极端的例子在元代笔记中很少,但直书无隐,可称元代笔记的普遍特点。如刘佶《北巡私记》记元中书右丞脱火赤战败被擒,直书“脱公嗜酒,醉而踣于阵,士卒尽没”。直书无隐,大约只有元人能做到。
因其时代特征,辽金元笔记又具有独特价值。读金代笔记,如读《大金吊伐录》等,会改变我们对宋金关系的看法;读《辽东行部志》等,会让我们惊奇于当时东北地区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更具独特价值的当然还是元代笔记。元代疆域广大,中外交通发达,商旅与使者往来频繁,于是域外行纪、域外地志等,成为元代笔记中引人注目的一类。西北行纪如上举王国维校注的多种,其他还有张德辉《塞北纪行》等。南方与海上,则有汪大渊《岛夷志》、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徐明善《安南行纪》、黎崱《安南志略》、周致中《异域志》等多种。元人游前人不曾游之地,入前人不曾入之境,见前人不曾见之物,感前人不曾感之情,记录了前代笔记所不曾有的内容。比如,元代有一部《和林广记》,其书已佚,但有一些佚文保留在其他文献中。在宋濂的《萝山集》中有一则:“《和林广记》所载:极西北之国曰押剌者,土地卑吉湿,近海,日不没,无昏夜,日唯向北转过便曙。”这应该是关于北极白夜很珍贵的记录。这则文献还将此地的天象与其他地区相比,说:“比之铁勒煮羊胛熟而天明者,又益异矣。”类似的,则有周致中《异域志》所载骨利国:“其国一年天旋到此,天光返照一遍,国人谓之天门开,非也。”元代笔记中具有独特价值的还有不少,如人类第一次探黄河源的记录《河源记》(潘昂霄撰),记载元代海运的揭傒斯等《大元海运记》和危素《元海运志》等,都是有特色的文献。元代笔记文献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天文的、交通的、域外的、海洋的、草原的,无所不有。这些无疑都是很珍贵的。元人日常生活是丰富多样的,记录其生活的笔记内容也丰富多彩。辽金元笔记的全面整理,将会对多学科的研究起到助推作用。
辽金元三代,特别是元代,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形成时期。在元代文人观念中,大元朝的建立,是中原疆域向四外的极大拓展,“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徒单公履撰《建国号诏》),“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许有壬《大一统志序》)。由此,王化大行,无远弗届。千百年的胡汉对立终于消除,“蒙恬剑下血,化作川上花”(陈孚诗),庆幸于“华夷一统太平秋”(耶律楚材诗),真正实现了“天下车书共一家”(杨维桢诗)。元代笔记文献,也包含有丰富的西北地域与多民族文化内容,广为人知的《圣武亲征录》,不为人知的《和林广记》等,都是这方面的珍贵文献。其他如《南村辍耕录》《至正直记》《归潜志》等,都记载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资料。辽金元笔记文献的系统整理,将为多民族一体性研究提供大量以前未发现、未使用的文献,从而推进这一研究的进展。
三、“笔记”概念之界定与收书边界问题
编纂一部大型丛刊,收书范围的划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全辽金元笔记》的编纂来说,参考学术界对“笔记”概念的理解,充分考虑辽金元笔记的具体情况,对“笔记”作出既符合学术界一般认识,又适用于辽金元笔记文献整理工作实际需要的界定,划出“辽金元笔记”相对清晰的边界,编制出尽可能完善的《辽金元笔记目录》,既是工作重点,也是难点。
对于什么是“笔记”,目前一般地作出界定,已经不难。其基本含义,学术界已大致形成共识,但落实下来,对于哪些书是笔记,哪些书不是,某一部书是不是笔记,分歧却相当大。查阅已经出版的有关笔记丛书,就可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理论层面的表述,目前分歧不大,但操作层面,掌握很不一致,具体认识,多有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辽金元笔记”划出边界,收录的书为研究界普遍认可,依然不易。
最早界定笔记含义的,应该是《四库全书总目》,其所谓“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今人的表述或与此不同,但基本含义无大差别。研究者的表述不少,二十世纪流行“笔记小说”概念,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行世,“笔记小说”概念被广泛采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显然不同于“笔记小说”对笔记的理解。史学家多使用“野史笔记”的概念,谢国桢在《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说:“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称作稗乘杂家。”(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第八十九页)这应该代表了史学家对笔记的理解。一九八〇年,刘叶秋先生出版《历代笔记概述》,由此“笔记”作为独立概念被使用。但正如刘叶秋所说:“什么叫作笔记,笔记有什么特点,哪些作品可以算是笔记等等,恐怕是见仁见智,看法各有不同,未必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他给笔记的界定是:“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出版,第四、五页)此后关于何谓笔记的讨论不少,我们没必要一一引述。对我们有直接借鉴意义的是《全宋笔记》的界定与选书实践。其基本界定是:“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古人随笔记录,意到即书,常常‘每闻一说,旋即笔记’,具有叙事纷杂的特性。从写作体例来看,宋代笔记随事札录,不拘一格,作品名称与‘笔’相关的有笔记、笔录、笔说、试笔、笔谈、随笔、漫笔、余笔、笔志、笔衡等,这些名称无不体现了宋人笔记随笔记事的特性,有别于正史的严肃划一,亦别于志怪传奇的天马行空;从内容看,涉及典制、历史、文学、民俗、宗教、科技、文化等,芜杂和包罗万象乃是其最大特色。”这是正面界定,还有反面排除:“凡题材专一,体系结构紧密的专集,虽亦有逐条叙事者,则已非随笔之属,如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以及“纯粹的传奇志怪小说作品”等,认为这些不符合笔记属性,不予收录(戴建国:《补正史之亡 裨掌故之阙——全宋笔记编纂札记》,《中国社会科学报》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我们借鉴《全宋笔记》的界定,根据辽金元笔记的情况,做适当调整:第一,辽金元笔记多“刻意著作之文”(宋代笔记也有“刻意著作”者),是否“刻意著作之文”应该不是笔记的本质属性,我们不以此作为选择与排除的必要条件。第二,题材是否专一,也难作为区分的标准。只要是随见随录,随手记录或摘录,不具备严格体例,非系统性,非有严密体系的著作,同时,它是见闻记录,或阅读摘录,而非想象虚构的,我们即行收录。我们的认定,不以内容分,只以体裁形式论。故诗话、画记等类,凡属笔记形式者,我们即予收录。第三,“纯粹的传奇志怪小说作品”,在宋元时代不多,应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全宋笔记》收录了《夷坚志》。类似之作,我们也予收录。
依据以上界定,利用各种古籍书目及叙录、图书馆藏书目录,各种大型丛刊,各种网络资源,搜求辽金元笔记书目,编制《全辽金元笔记目录》。具体收书目录,遵循本丛编《凡例》,参考各大型笔记丛刊收书目录,依据所涉书籍具体情况,斟酌去取。既名为“全”,我们尽力求全。当然,所谓的“全”永远是相对的,特别是笔记之“全”,由于不同人对收书标准有不同理解与把握,我们追求的“全”,只能是在我们收书标准下的“全”。学术史的所有“大全”项目都有遗漏,“竭泽而渔”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实现,我们的追求是尽最大努力,少遗漏,少留遗憾,做到最大限度的“全”。
四、编纂点校工作的若干问题
编纂点校《全辽金元笔记》,是为辽金元文史研究提供全面可靠的笔记文献,也为一般读者提供良好的辽金元笔记读本。为此,要认真解决一系列问题。大致说,有版本(底本)之选择、已有整理成果之借鉴、辑佚与辨伪、附录材料之搜求等。
其一,版本之选择。全面利用各种古代文献,重点大型丛刻,二十世纪以来影印出版的相关丛书,尽可能完整掌握各笔记的版本信息,梳理版本源流,确定精良适用的校勘底本,以及校本、参校本,尽可能搜集可资参考的其他文献,把校勘工作建立在准确的文献基础之上,这是做好编校工作的前提。
笔记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笔记,不同版本的差异很大,有时不仅仅是异文问题,卷数不同,条目互异。甲本有的条目乙本漏落,乙本有的条目甲本缺失。文字的出入也很大。又有不少未经整理的钞本,凌乱与残缺情况比较常见,一些文字辨读困难。基于这种情况,我们选择底本的依据,首先是全,以漏落缺失相对较少者为底本,以清晰完整者为底本。
辽金元笔记底本选择还有若干特殊情况。一是部分笔记有单行本系统与别集本系统,两者相较,多数情况是别集本系统保存较好,自然应选择别集本。二是有些笔记卷帙不大,内容比较独特,近代曾有人(如王国维等)做过学术价值极高的校注,凡此类我们即以其校注本为底本,保留其校注,参考其他版本做校勘。其他如《归潜志》,《知不足斋丛书》本有清人鲍廷博校正与疏解,也如此处理。三是《四库全书》及四库系列版本的使用。一般认为《四库全书》版本价值不高,但其所收辽金元笔记有很多版本价值较高。我们对多种有四库本的笔记做了不同版本的详细比对。比如《诗林广记》,今存主要版本有明弘治刊本与四库本,四库本乃纪昀家藏本,诸本相较,四库本为佳,少脱漏讹误,故以四库本为底本,但需将四库本以“违碍”改易之处,一律据明刊本改回。王恽的《承华事略》《中堂事记》《乌台笔补》《玉堂嘉话》,我们选择《秋涧集》本,而《秋涧集》又有多种版本,重要者如元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覆元本、《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本。一九八五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收《秋涧集》元刻本配补明覆元本,一时为研究者重视。但细加比较,《四库全书荟要》本远优于《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我们选用《四库全书荟要》本为底本。总之,以求全、完整、清晰、差错较少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在认真比对各本后,依据实际情况作出选择,而不受其他因素过多影响。
其二,已有整理成果之借鉴。《全辽金元笔记》整体规模较大,整理难度极大。要做好,除整理者全力投入、精审校勘外,最大限度地吸收已有整理成果很有必要。有今人整理本者,利用《全国总书目》、各出版社书目与其他出版资讯,全面掌握二十世纪以来辽金元笔记点校整理本的出版情况,搜求全部点校整理本,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整理成果。但借鉴只是借鉴,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校勘,必须先做校勘,而后借鉴他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些笔记已有多种整理本,但有些错误却一直沿袭。对这类笔记,须下功夫重点纠正相沿之误。如何发现相沿之误?只有多查。既不盲目自信,也不轻信他人,包括权威。要加大投入,在遵循大象出版社历代笔记文献丛刊统一体例的前提下,力争后出转精。对于无今人整理本者,也尽力寻找相关成果,以为校勘中的借鉴。笔记作品,多有辑录、摘录、转引前人内容者,而古人往往并不言其出处,我们在整理中都尽力查其出处,查找原书,以为校勘参考。尤其是学术性笔记,所讨论辨析的问题,涉及经史为多,内容多源自经史著作(当然也有子集)。古今学者相关的整理与研究成果,都可作为我们整理的参考。典型的如方回所撰《续古今考》,不参考古今经史整理成果,我们的整理可以说寸步难行,我们在整理中几乎句句查,多方查。其他问题,如元代特有的语言、人名、地名等,也必须尽可能参考借鉴已有成果,尽力减少整理中可能出现的错误。
其三,辑佚与辨伪。近些年古籍数字化的成果,为文献检索提供了极大方便。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充分查找相关材料,辑录笔记佚文,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完整的笔记文献,是我们尽力做的一个方面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辑录了一些佚文,尽管数量不是很多,但也是一种收获。在流传的辽金元笔记中,确有一定数量的伪书。前人已认定者,有署名伊世珍的《琅嬛记》,署名龙辅的《女红余志》,佚名的《赵氏家法笔记》等。前人疑伪者,有署名张师颜的《南迁录》,署名张道宗的《记古滇说》等。对于这些,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在整理中,也有新发现的伪书,如署名徐大焯的《烬余录》,从书前李模序及书之内容,可初步判定其为伪书。我们把辑佚与辨伪,作为编纂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四,附录材料之搜求。这类大型丛刊,多数不做附录。我们觉得,本丛刊所收的很多种笔记,今后再整理的机会并不多,有必要利用本次整理机会,尽力搜求古近代学者的序跋、题记、叙录,以及一切评价资料,作为附录,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奉献给研究者。经过我们的努力,附录的搜集,成效明显。即便是一些有深度整理单行本的笔记,前人已经辑录了丰富的附录资料,我们依然有新的收获。这些附录材料,增加了本丛刊的学术含量。
总之,我们全部的努力,都是要保证编纂点校质量,尽力为辽金元文史研究者和其他读者奉献出完整可靠的辽金元笔记文献,让读者信赖,让研究者放心使用。
笔记文献的整理是一项复杂烦难的工作,困难与挑战,随处而有。我们将竭尽全力,希望把工作做到最好,但问题甚至错误总是难以避免的,真诚希望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教。
查洪德
二〇二〇年十月
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贴专家。兼任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所著《元代诗学通论》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