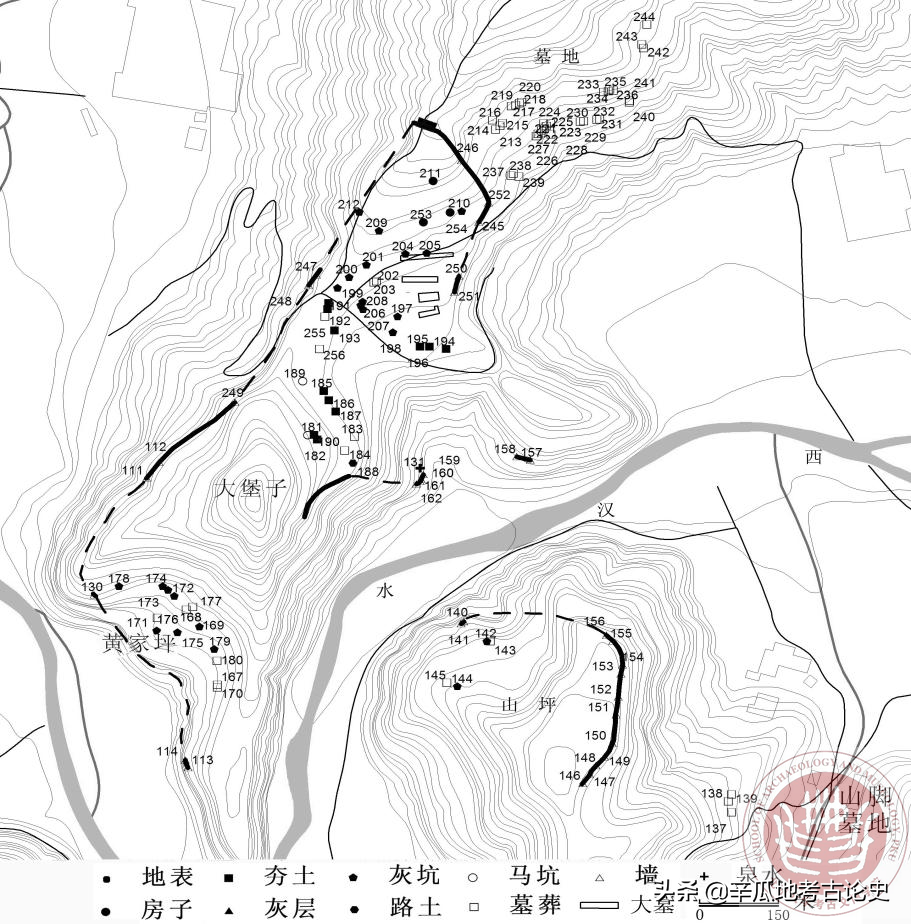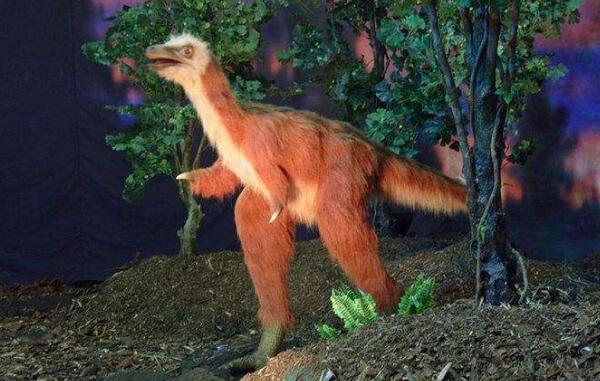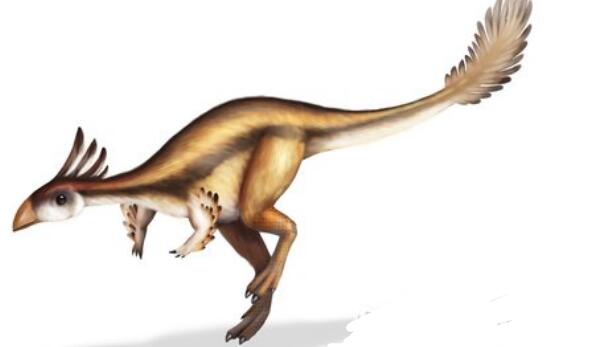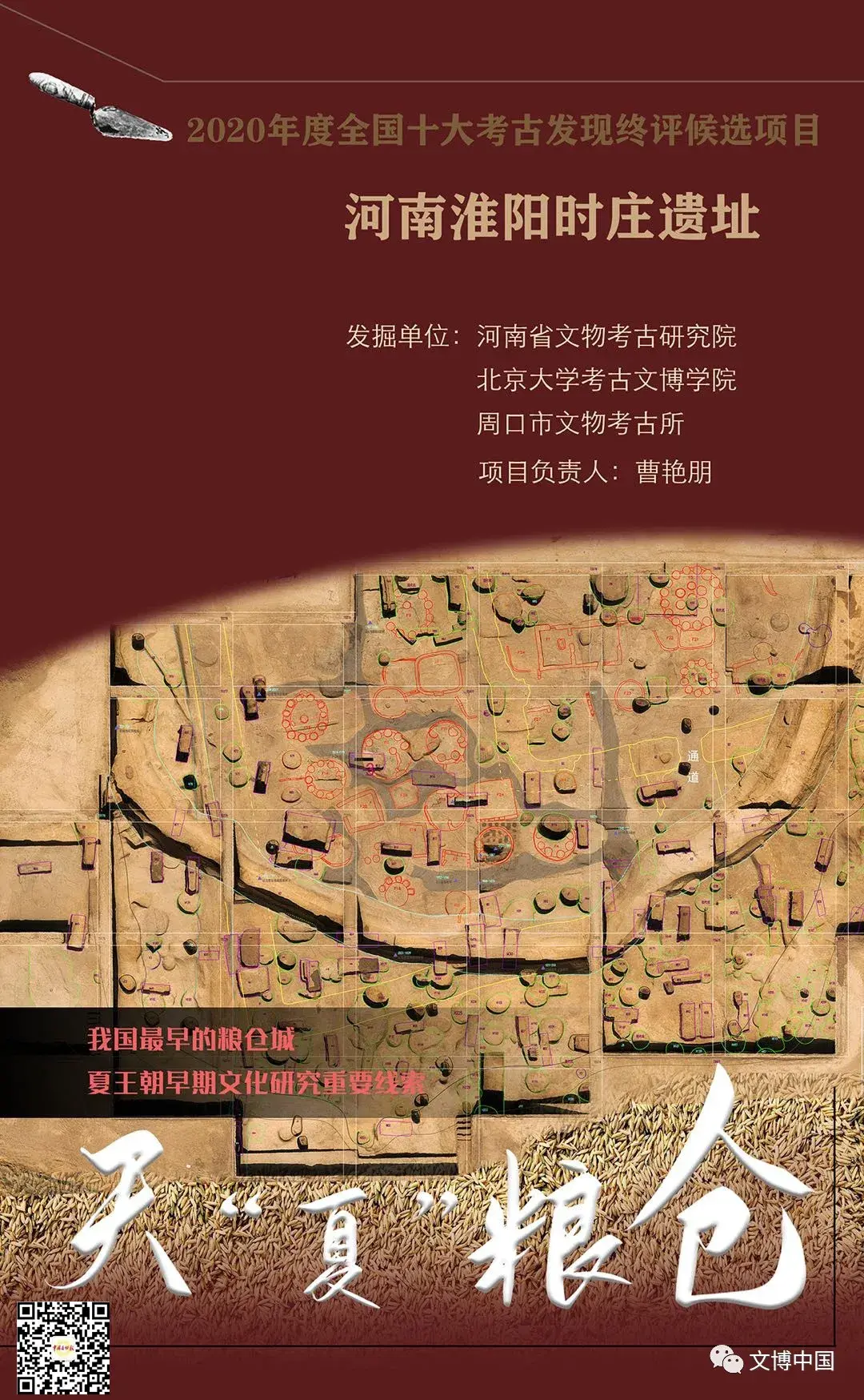中国考古百年 | 回访:暗流与低音
徐峰
2012年,徐坚先生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以下简称《暗流》)出版,在此之前,考古学界似乎习惯了考古学史著作以民国时代史语所的考古发掘、人物和研究为讨论对象。《暗流》一出,考古学史上某些被遮蔽的角落有了些许光亮,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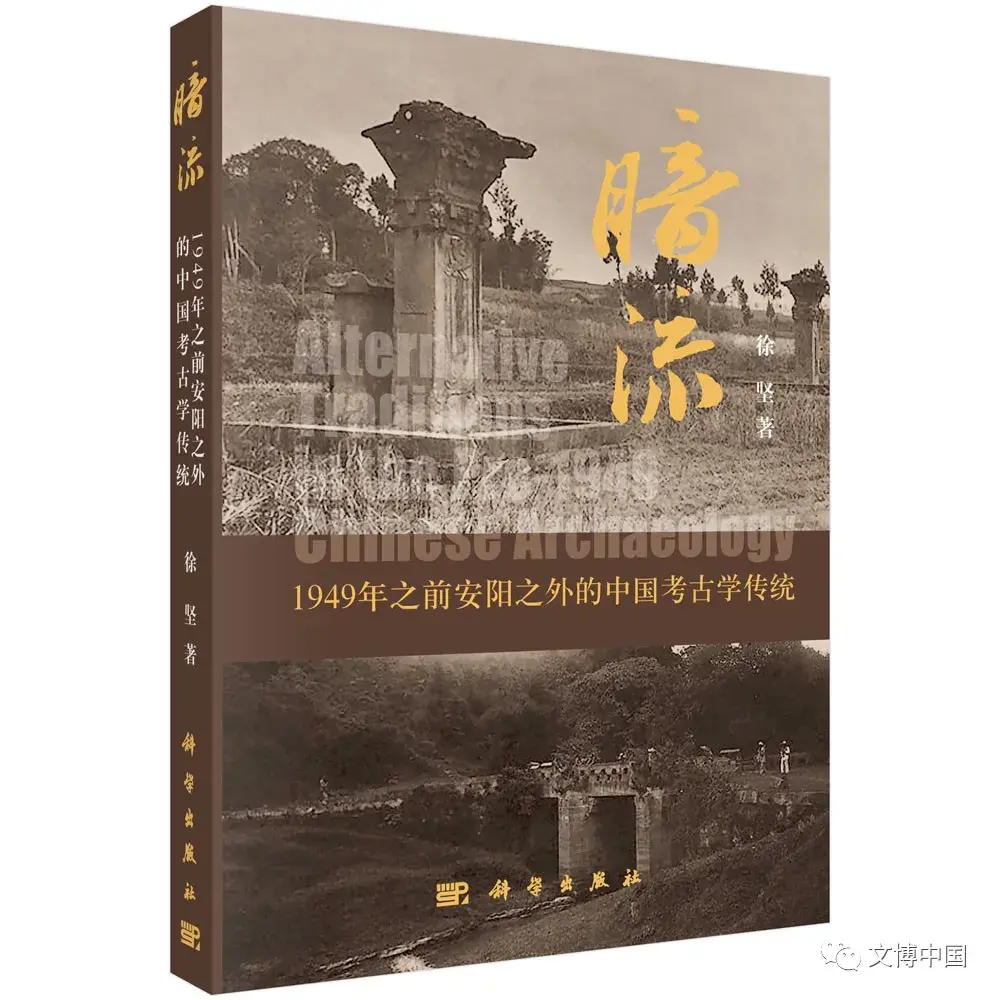
欲知暗流,自当先明晰主流。民国初年,科学思维开始向各个研究领域渗透。历史语言研究所便是学术机构层面受科学思维影响的重要产物。胡适和傅斯年都主张按照“科学”的要求来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谈及,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此科学之范畴,不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更是延伸到借助自然科学的工具解决历史的问题。考古学正在这科学的范畴之内。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尚在筹备中,傅斯年即派董作宾前往安阳调查。之后便在安阳展开了国家性的大规模的发掘,前后达15次,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当时无出其右。与金石学家从事的挖宝式考古不同,安阳发掘被视为“科学的考古”。当时有两个能反映科学的史料观和研究取向的例子。
其一,董作宾在殷墟第一次试掘13天后,只发现一小部分甲骨,且得甲骨文字者,不过六七处,董作宾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不无抱怨。傅斯年对此则不以为然,于是便有他给董作宾复信中的经典论见:应该多注意地层等问题,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傅斯年曾言“古史无待于后来的考古”,这是因为考古中那些能够促进考古学和历史学整合的像文字一类的自证性材料是非常少的。
其二,史语所于1930年对山东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一文中表扬了《城子崖》报告的编写者,认为按照文籍遗传来看,城子崖遗址十成有九成会被当作谭国故墟,然而编写者知道只是经籍遗传之说,所发掘者,并无一物确证其为谭邑,与殷墟之为殷墟有多量实物证明者不同,并且见到此地之地层有上下,不便混为一名,所以作者“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就明显体现了与“考古学是证经补史的工具”不一样的取向。
《暗流》另辟蹊径,将视野转向安阳以外的另一种中国考古学传统。作者称之为“暗流传统”,对个中被历史遮盖或隐匿了的材料进行再阐释。该书探讨了若干个案,涉及多种类型的“暗流”,有被忽视和估计不足的人物及相关发掘,如郭宝钧、吴金鼎、张希鲁、新郑李家楼的发掘、西南考古等;也有不彰显的学术机构,如云南博物馆、黄花考古学院等。
换种表述,暗流传统也可谓边缘传统。
《暗流》的篇章结构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数篇个案研究;一是绪论和和余论部分关于“暗流”的理论阐释。对于该书的成功,这两部分不可偏废。徐坚一方面整体性地界定出了“暗流”,为之设定不同的界定标准,确认暗流传统的存在,这就占据了表述考古学史中另类传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又为暗流设置了一个开放体系,指出暗流无法形成自上而下、边界分明的树状结构或者体系。这样的处理,颇见高明。其隐含之意是说不论主流还是暗流,都是变动不居的。一旦落入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就会形成不同的历史遭遇,从而不断更新历史的叙述。由此,我们便可理解该书将曾任职于史语所的郭宝钧、吴金鼎置于“暗流”体系。主流的史语所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主流中潜伏着暗流。1949年鼎革之后,民国时代居于主流的史料学派从中心滑向边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遮蔽,沦为暗流。傅斯年、李济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影响与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隐匿。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夏鼐1979年发表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连李济的名字也未提到。
《暗流》的绪论和余论中有关暗流传统理论思考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存在和其他学者类似的历史思考产生对话与呼应的可能。当年初读《暗流》,我即刻想到王汎森先生《执拗的低音》,于我有种知识考古学“二重奏”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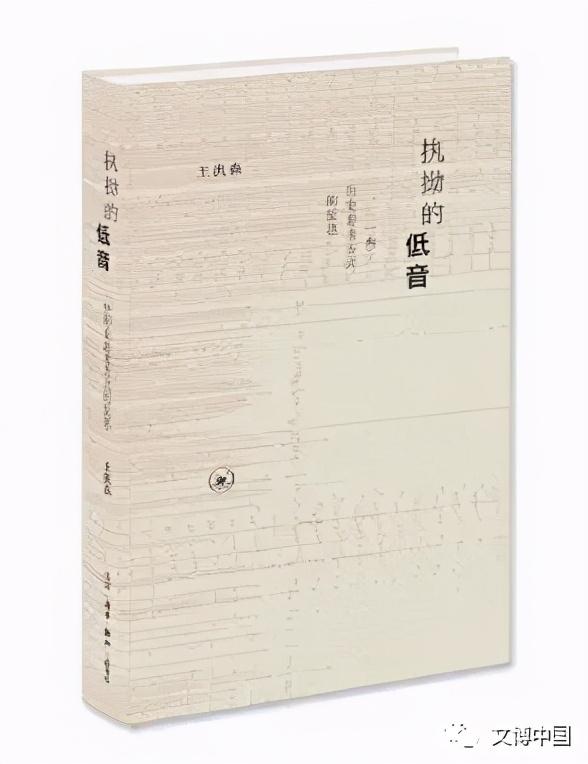
2011年,王汎森先生受邀在复旦大学做了四场演讲。第一讲名为《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后来演讲以书的形式出版,书名即以第一讲为名。《低音》的主旨是要重访近百年来被新派论述所压抑下去的声音。重审、重访低音,不是说这些低音都是正确的,但也不是复古和回归,而是为了查询这些边缘或低音是否仍有可观的思想价值。《暗流》有着几乎相同的表述。徐坚指出:“发现和阐释暗流传统却不是正本清源,重新确认一度被扭曲或者被忽视的主流传统,而是揭示研究传统的多元化本质。在谈到回归“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时,徐坚再次提醒这种回归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变天而重新回到文化-历史主义考古学的怀抱。
不论《低音》还是《暗流》,“回访”都是关键的作业方式。王汎森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回访。例如,在“事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部分,他说不管新派或旧派,往往在“价值”扬抑的同时,把“事实”的部分也贬入历史的边缘,或从此不再出现在人们眼界之内。他谈及“创造性转化”,说“原来人们以为很多传统学问在转化成现代学科的过程中功能会得到继承或改善,其实并不一定如此。有很多东西在转化的过程中被人们遗忘。尽管学问转换得更科学、更现代,但也有些复杂细微的成分被摒去了。”
《暗流》借鉴文化人类学中的“回访”,试图建立考古学史的回访方法。考古学史的确是资源丰富的回访对象。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属于近代“学科化”运动之一。照王汎森的认识,在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在将古代学问转换成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把价值、生活、带有现实意涵的部分打散开来。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也存在这个问题。徐坚发掘暗流也可谓在“创造性转换”中找寻有价值的资源。比如新郑李家楼发掘中独特的组织、沟通和执行方式对于考古学而言,并非全然无补;就发掘和刊布过程的效率、记录的详备程度、发现的完整程度和散佚器物的追索上,新郑李家楼大墓远优于中国考古学成形之后,甚至直到晚近发现的众多个案;新郑李家楼的发掘经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随后十余年发掘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墓葬的认识基础;更为重要但几乎从未被人提及的是,新郑李家楼器群的刊布不是这一发现的终点,李家楼器群的“后发现过程”——即保存和展示权之争在中国考古学上尤其具有范例意义。再如西南考古,徐坚认为对其回访不仅仅是资料层面上的补充和校正,更为重要的是准确厘定吴金鼎在方法和理论上有别于安阳传统的贡献。
何以回访能够发现有价值的资源?姑且不论爬梳、翻检历史资源,或多或少会有些新发现,进而产生新的解释。这就好比考古发掘中的筛子过土,一般总会发现数量不一被遗漏的小型物件。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和知识情境都将影响他发现、选择、强调和阐释特定的人物、事件和脉络。情境的变异转换不仅使得回访成为可能,也是必须。两部书中都格外强调情境,王汎森希望历史研究能做到陈寅恪所说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后见之明要明察,即是对情境的重视。徐坚则强调,每一个被纳入暗流传统的个案都需要在其独特的情境之中独立研究。考古学史的回访方法必须设身处地地观察历史上的研究者所面临的资料,同情性地理解他们的预设观念和推理过程。
《暗流》与《低音》的写作均属两位作者借用概念而从事的历史个案阐发,意境相通、表述相似、名称对仗。暗流是一种涌动着低音的潜流。王汎森曾用“潜流”作喻:“如果只看到当时的主流论述,而没有注意到各个层次并存互相竞逐的方式,没有看到当时的低音、潜流,很多事情会变得没有办法理解。”
两部著作都重视回访以发现有价值的历史资源或另一种学术传统,又差不多同时期发表出版,颇如蒙文通所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邻”。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 0000
- 0001
- 0001
- 0004
- 0000